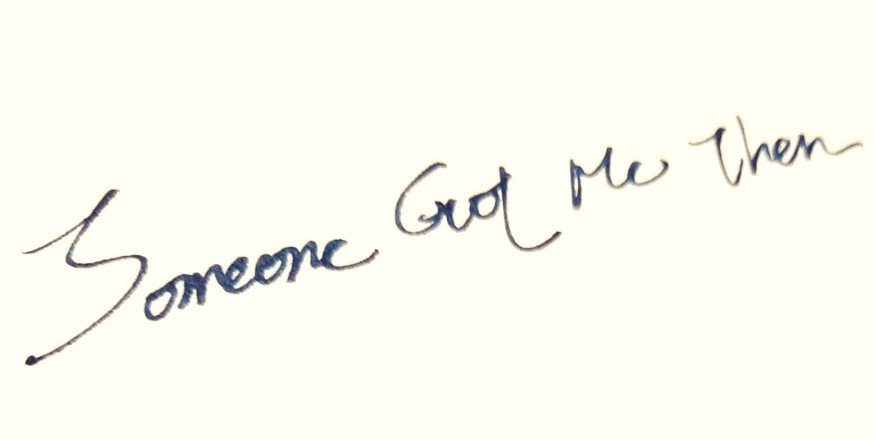|設定2016年7月,正文的伊利安側寫
27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1mGIp3xGPl
27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ucntplDbik
「她」是誰?她是「誰」?
伊利安明白的,「她」存在之必要,一如「他」對自己存在之必要。
只是在他人生有限的閱歷,還不足以辨別亞瑟的敘述中,哪些屬於真實,哪些屬於回憶的濾鏡。
他無法對此產生明確的嫉妒,說得更直接一些,他們相遇之時,伊利安甚至不存於這個世界上,無論以任何法理情的角度定義。
縱有一骨子的自由奔放,阿納托利也鮮少訴諸文藝情懷,只偶爾會用泰戈爾提點他:「如果你因錯過太陽而流淚,那麼你也將錯過群星。」[1]
對於他人的關心,伊利安就是不知該如何拒絕,他也心知對方沒有這層意思,但那仍時而讓他感覺,自己在被指責。
在遠得像是上輩子的青少年時代,他其實已經習慣了這種麻木,只是亞瑟的言詞太過柔軟,就連充滿稜角的部分也像裝上了安全防撞裝置,他忍不住想將自己的任性、脆弱、憂慮、滿目瘡痍在對方面前徹底揭露,想證明即便如此,對方也不會離他而去。
想證明這麼糟糕的他,也值得被喜歡、被愛,被渴望著愛。
就算他與「她」,完全不一樣。
相較於網際網路世代隨口一提的「女(男)神」,亞瑟口中的「她」,在伊利安認知中,更近似於神話裡富有古典美的寧芙[2]。
他不知道這看法公不公正,因為他對此的所知全來自於亞瑟──懷抱戀慕之情的男子,無論是他對「她」,或他對他──而「她」一身狀似出於自然,或者存在本質,的狂野氣質。比起不可捉摸的神性,與沾染了幾分人氣的小精靈更相仿,會在山林百川編織花冠,會嘲笑色慾薰心的醜陋妖精[3],也會因愛而不得詛咒他人[4]。
「是蘿莉塔[5]嗎?」有回,伊利安小心翼翼地提問,試著不讓語氣聽來輕佻或挑釁。
這話讓亞瑟語塞,隨後笑了起來,沒有責怪之意,只是那道目光彷彿去了一個很遠的地方。
「如果是現在的我,那可能會是,因為我向來無法摸清她的想法,而聰明的女孩從不吝於戲弄那些對她們懷有好感的人;但於當時的我,她是我與這個世界、乃至我自己的連結。親愛的,請容忍我的再次聲明:我喜歡她,但我不愛她。」
他不愛「她」嗎?伊利安感到迷糊,如果一個人能影響另一個人的人生甚鉅,那有可能不是「愛」嗎?
還是說,他不禁陷入一種暗無天日的無望,再多的「喜歡」對於亞瑟‧安斯提來說,都沒可能成為「愛」?
27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nenItQqtlL
*
27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dCPIrvr7KA
得知他每日的「小茶會」後──當然,在解釋這一連串的陰錯陽差時,他作了一定程度的保留,就作是年輕人的自尊與虛榮心作祟吧──保羅與南茜有顯而易見的驚訝,不是壞的那種,因為他們旋即不失溫暖地請他「如果可行」,不妨邀那位「關照許多的先生」來家裡喝個茶。
對此,伊利安一度輾轉難眠,名義上是沙發衝浪,但老夫妻給他特別準備了一張厚實的床,枕頭罩還有花香柔軟精與太陽的氣味,本該最是適合入夢,他卻無法成眠。
儘管來到這裡一個月不到,此前他也從未與任何英國人交旋,但感謝亞瑟(如果這是一件值得感謝的事),他知曉這個海洋民族深諳將意圖包裹於層層社交辭令之下的作風,好似若他們忠於自身慾望,那些脫口而出的就會如生日的第三個願望,隨蛋糕上的燭火一道熄滅。
因此,他能感受到他們禮貌措辭後的期待,那使他不忍讓他們失望。
然而,他生怕自己的莽撞打擾了亞瑟習以為常的、也說不定是享受著的孤獨。他說的不僅是形單影隻,將與鄰里少打交道視為敦親睦鄰、「不互相找麻煩」的物理狀態;還是被他掩飾得不夠好的雀躍、羞赧與不切實際的幻想,攪亂的一池春水。
是,即便亞瑟從未直言──無論是確認或拒絕──伊利安也隱隱感覺到,他都知道。
知道他的別有用心,知道他無法訴諸言語行動的情衷,知道他不敢將善意輕易當真、唯恐自這場仲夏夜之夢[6]甦醒時痛苦欲絕。
中學的地理課上,老師曾給他們播一部電影講解全球分工,片名原文直白明確,直譯就是「外包」之意[7]。按照美國浪漫喜劇的固有戲碼,來自資本大國的男主角與土生土長的女主角墜入愛河,苦於文化差異,最終只得成就一段被印度女性默許為「婚前的終末狂歡」的露水姻緣。
伊利安情不自禁地想,他們也會變成那樣嗎?
確實,他們什麼都沒有發生,但有沒有可能亞瑟看他,就如年少時「她」看待笨拙的他、一樣呢?而這又是一種幸,抑或是不幸呢?
幸運的是,在不觸及底線的情況下,亞瑟會寬大地容許他躋身自己的舒適圈;不幸的是,他永遠都無法踏過那道底線,成為那個堅實堡壘之中的一部分。
「如果你只把你的選擇,限制在看似可能或合理的範圍內,你就會與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脫節,剩下的就是妥協。」[8]父親的藏書中,有句話是這麼說的。
伊利安不清楚那究竟合不合理,因為倘若那是正確的,那似乎昭示他一生註定無法得到他想要的。就如孩提時代,他坐在飯廳裡窗邊的位置,目送著難得面色愉悅的父親將釣具放入後車廂、來回審視,滿意地闔上車門,最後,驅車離去。
每一次,他都無法說服自己那台車會掉頭帶上他,更甚,可能從此不回來了。也或許,早在第一次父親這麼做的時候,他的心、他的愛,他那個幼小的自我,就已經被丟在一個撿不回來的所在了。
既說不好再見,又不敢脫離常規⋯⋯若他的一生註定如此,那不是很殘酷嗎?
27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N6rz76x161
*
27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p7OtV7YwOz
沒讓伊利安的惴惴不安持續太久,亞瑟答應得爽快,當天就隨他一道造訪了老夫妻。席間相談甚歡——亞瑟應是猜著他對初識的有所隱瞞,對此隻字不提,伊利安覺得他敏銳得令人害怕——好像先前的憂慮都是霽後散盡的晨霧,來得輕巧,去得更是無聲無息。
這個夏季像是讀一本已經知道結局的書,過程曲折不失美好,他捨不得翻得太快。
後來,亞瑟帶伊利安去公園野餐、領他認識家人(包括傳聞中的羅德尼與特瑞莎),在因緣際會之下,他甚至偶遇了那段不名譽的訂婚關係的另一方——珊曼莎,讓他驚訝的是個金髮甜心,頭髮的顏色比他淺了很多、對於甜美的笑容恰恰剛好。實際上,亞瑟沒敘述過珊曼莎的樣貌,也許他向來不擅長太具體的敘述,畢竟連「她」的形貌在交談裡也像雲中窺月,唯一可知的是一頭柔順的深色長髮、幽深的烏色眼珠,以及如白蘆葦般單薄的身姿。
事後想想,說不定這麼多年他們不是未曾重逢,而是「她」少女時期身上那股能將塵世隔絕於外的靈性已被世事艱難消磨,以至於他沒能認出是「她」?
這念頭連伊利安都自覺惡毒,他已不幸如斯,怎麼卑鄙地企盼他人與他遭逢類似的風霜呢?這也難怪「她」會成為亞瑟解讀盛夏的永恆精靈,而他只是用以排遣無聊的,如海市蜃樓般的水蒸氣(water vapor)嗎?
當代有些自詡感情專家的名人聲稱,愛一個人不該太用力,因為那也會使被愛的一方產生壓力,好像自己不得不做出什麼「選擇」,將兩人逼到懸崖,以崩毀原先關係平衡為前提的、自私的愛。
或許是他太年輕,或許是他從未品嚐過愛「好的那一面」,或許是他從未體驗過「不那麼用力的愛」,因此閱讀再多,他也僅能將此視為一種立場,不具足夠的說服力付諸行動。直截了當地說,便是他想實踐,他也從未習得如此去愛的能力。
伊利安感覺,亞瑟具備這個能力,他像是⋯⋯伊利安覺得自己可能形容得不夠好,不過他的一言一行就像白沙灘上一排柔軟的、鮮明的、尚未被不解風情的風浪帶走的腳印,字裏行間都是深意,卻不著急著要這個世界理解自己。好像你明不明白、喜不喜歡、相不相信,最終有沒有其他風砂掩蓋那條路徑,留下足跡的人總會走到他意欲探索的遠方。
但是,亞瑟願意教導他嗎?為這麼庸俗的、幼稚的、欠缺考量的、就算再怎麼努力還是難掩迷糊的、碎成一片片的他。而他又學不學得來呢?會不會這種學習的渴望,也只是另外一種深層慾望的偽裝?這種爛得生瘡的骯髒欲求,會不會連亞瑟都被他拉入地獄呢?那是他最不想見到的一件事。
這想法太過消極,祖父定是會難得正色斥責他「伊留沙,神自有安排」,伊利安仍無法從無明的生活中看到一點其他可能性,只能想起《刺鳥》的控訴:「要怎麼活下去呢?這就是自己渴望的生活嗎?你從上帝那兒來,又返回上帝身邊。出於塵土而歸於塵土。生活是讓我們這些失敗的人過的。貪婪的上帝,把優秀的人聚集在身邊,把世界留給了我們這些剩下的人,我們這樣墮落的人。」[9]
萬一他任性妄為,縱然知道無果,也想親口告訴亞瑟呢?是,他永遠都不可能成為輕巧慧黠的寧芙,但就是平凡的泡沫,在美人魚幻滅之時同樣令人印象深刻吧?他是個凡人,不與日月爭光,他只祈求凡人的幸福。[10]
伊利安想成為那樣。他想在一個連塵埃都閃閃發光的時候,傾訴他的愛,接著散入風中,像個不被放在心上的魔法。
他是水蒸氣,在不需時太久的循環後——可能是繞著這個地球一週後,也可能是人生兜了個大圈後——或許某一天,能以亞瑟屆時最需要、最想要的型態相逢。即使亞瑟的生命沒有他的容身之地,紳士也會盡可能表達最大的善意,讓他能夠暫歇躲雨。
這是一種怪譎的心情,還沒道別,但他已經在期待重逢的那天了。
會不會這也是哪裡的妖精的惡作劇呢?伊利安笑著搖搖頭。
27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h3PAlmVEya
274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aDlJHdM6gB
FIN.
[1]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রবীন্দ্রনাথ ঠাকুর)《Stray Birds 漂鳥集》,一九一六年。原文全句:「If you shed tears when you miss the sun, you also miss the stars.」
[2] 寧芙(νύμφη)是希臘神話中次要的女神,有時也被翻譯成精靈和仙女,也會被視為妖精的一員,出沒於山林、原野、泉水、大海等地。
[3] 理查·華格納(Richard Wagner)《Das Rheingold 萊茵的黃金》,一八六九年。
[4] 希臘神話中納西瑟斯(Νάρκισσος)因受詛咒愛上了自己的倒影,無法從池塘邊離開,終於憔悴而死。
[5]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 Набоков)《Лолита 蘿莉塔》,一九五五年。
[6]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仲夏夜之夢》,一九五〇年代,實際年份不可考。
[7] 約翰·傑夫考特(John Jeffcoat)《Outsourced 地球是平的》,二〇〇六年。
[8] 羅伯特.弗里茨(Robert Fritz):「If you limit your choice only to what seems possible or reasonable, you disconnect yourself from what you truly want, and all that is left is a compromise.」
[9] 柯林·馬嘉露(Colleen McCullough)《The Thorn Bird 刺鳥》,一九七七年。
[10] 化用弗朗切斯科·佩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a)《Secretum 秘密》,原句:「我不想變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恆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懷抱里。屬於人的那種光榮對我就夠了。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