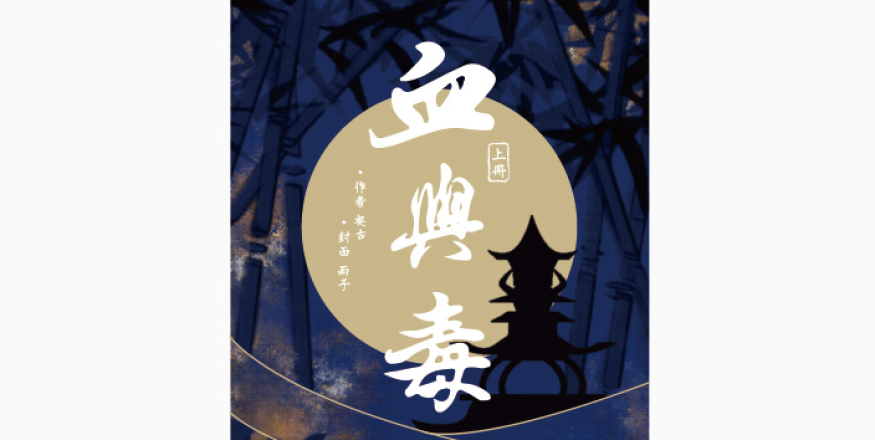貳、尋爾
準備入冬的五聖教總壇四周仍帶著翠綠氣息,溫暖彷彿春日,藥用植物混雜藤蔓珍花異草的藥蠱苑植藥區更是如此。燒炭火的爐分散園內,幾名五聖教的弟子正挪動盆栽並引導花蝶穿梭其中,至於植藥苑中心的幾張桌子上頭擺滿各式新鮮或曬乾之草藥。
此刻一位五聖女弟子面色焦急蹲在桌旁。
「阿炎!」
身著銀飾紫裳的女性不停呼喚倒地的同門弟子,卻未敢隨意搖動,如此喊幾聲後男人才悠悠轉醒,她趕緊上前攙扶,運氣替他調神並追問:「阿炎你還好嗎?」
被喊久炎的弟子抓住女子手臂嘗試讓自己清醒。撞擊地板的力道使他全身泛疼,險些無法施力,語帶困惑低喃:「嗯 ⋯⋯嗯?香卡師姐?我、我怎麼 ⋯⋯」
同門突然昏厥自是驚著香卡,連忙撐起久炎擔憂道:「你剛剛突然喊聲寨黎,話都沒說完,不知道怎麼就昏了,身體不舒服嗎?」
甩頭逼自己回神,久炎轉向同門師姐,眉首微皺。
「我昏倒很久嗎?」他滿心疑惑,按壓前額緩緩起身,神態異常凝重。
痛感來得快也消失得快,卻在其心中引起深深不安,總覺得有事即將發生。
「沒有 。」香卡搖搖頭,剛剛她轉頭拿藥草時就耳聞撞擊聲,回頭見本有說有笑的久炎已倒地,雖然很快就清醒還是讓她驚魂未定,忍不住再三確認:「真的沒事?」
「我真的沒事,抱歉讓妳擔心。」久炎連忙搖首。
出事的鐵定不是我。
男人暗忖,立即感受體內母蠱的動向,卻發現她熟睡般沒有動靜,代表子蠱目前處於安穩狀態,但這同樣可能表示存在子蠱的宿主因未知原因昏迷。而久炎自然知曉那人時常陷入危機也不願說明,使得自己常常毫不知情,幾乎成為是壓在心底的結。
危險的預感必得消除。
須親眼看見他才行,要趕去那人身邊。
久炎很快做出選擇。
「師姐,我需要離開聖教小段時間⋯⋯」
他直視師姐,語調請求,然眼中已是下定決心。
「甚麼?現在?」
香卡眉頭輕皺,對於他突然告知有些訝異與不滿,可看到久炎表情也只能深深嘆氣道:「最近天一教似乎又重新崛起,傳出有新的屍人被煉製出來,還有各類中毒事件,你確定要此時離開嗎?」
「對不起,我會把其他事交代給阿倪。」抓起手邊藥草,久炎眉間帶著歉意,將稍早製作的解藥都陳列在香卡跟前,快速同她解釋各類用途後便準備離去。
香卡見狀自也未阻攔。「好啦,瞧你這眼神,知道你有要事。」
她雖然不理解師弟怎麼突然這般憂慮,又是何等事情如此緊急,但更知道久炎並非隨意之人,八九成可推出與他那跑去唐家堡的郎君有關,因此未再多問點頭允諾:「沒關係的,去吧!記得路上照顧好身體,我再幫你向風瑤說明。」
「香卡師姐!謝謝妳!」
真誠向香卡道謝,久炎在簡單安頓完事務後直奔回藥蠱苑養蠱地,見徒弟紇倪不在此處也未遲疑,迅速整理簡單行囊後請同門轉帶自己口信,緊接前往蝶園取上追蹤蝶,在牠們身上標記體內母蠱氣息,並藉蟲笛引導其循子蠱。
「帶我去找阿湘。」他吹起笛音。
只見碧蝶在灑落樹葉間的陽光裡飛舞盤繞幾圈,緩慢朝東偏北飛去。
看來是老地方,得快些。
久炎心底即刻開始忖度如何前往目的地,可思及即使抄近程趕路,抵達唐家堡近郊也要三至五日,而他最後收到唐湘信是一月前,這之間有何等變卦都難以預料,更何況世間諸事本就無定數,沒人能算盡,更終究不會如其所願,惹他擔憂無比。
看來即使心頭存有同生共死之蠱,他們仍是天涯相隔。
男人想著,確定方位後長嘆不止,依舊運起輕功追隨碧蝶前往兩人時常相約見面之地。
其實久炎已在唐湘師傅唐芝華見證下與之結髮成郎君道侶數年,只是長久來因身份隔閡僅能分居兩處偶有見面。不過,若說唐門與五聖教暗地間多利害恩仇,若要避免疑慮,如此距離或許也是省下許多麻煩,僅需忍耐孤寂。
思及此,五聖弟子皺起眉頭,露出不悅神情。
難搞的唐門。
他暗忖,尤其那個以唐湘養父自居的唐家堡堡主。
「嘖。」
愈想愈氣。
蠱蟲感受到主人憤怒而有些焦慮,久炎立即注意到心緒影響到靈獸安穩,趕忙出聲安撫碧蝶,並加快速度前進。
無論如何,千萬不要出事。
久炎在心底低喃,雙眸透出沉重。
፠
幽暗中唐湘睜開眼,好段時間才逐漸恢復思考。
夜半寒氣使其四肢冰冷、無法動彈,僅剩下胸前的護身物發出溫暖,使之不至於在幽夜中失溫,似乎還有個熟悉嗓音輕聲喊他起床,然男人想不起來究竟是誰,頭昏沉又眼前搖晃。
他嘗試挪動手腳後緩緩起身並檢視四周,只見自己正躺在廢棄屋內的石地上,照入室內的月光撒在上頭,旁邊被蛀朽之木桌看似搖搖欲墜,染著大片黑斑,並感受身體僵硬還有外襟被夜間涼氣浸濕程度,能判斷應有昏超過至少一個時辰,然他皆無關於怎麼移動至此的記憶。
我躺了多久?
為什麼會在此?
唐湘掙扎起身後他跨出半幢坍塌房屋,拖著步伐至原先躲藏的樹,注意到兩邊陷阱都未被觸發,維持原樣,甚至只有稍早被自己掩蓋去的痕跡,別無其他。
這究竟?
難道真是自己失去意識中從樹上移動到屋內?
無論是甚麼,都未免過於匪夷所思。
皺起眉頭,唐湘習慣掛在臉上的笑不復存。
自從發病以來,這類詭異感覺時刻相隨,男人總會於回神後注意到出現未有印象之事。尤其身在唐家堡時甚至會暈沉到失去意識,醒來後卻發現已完成某些修理機械的工作。且他隱約察覺到自幾年前與久炎共享蠱後便愈來愈頻繁,連徒弟莊臻都說看過自己半夜起來點燈趕工,差點讓少女以為師傅熬夜操勞,想直接住進內房監督其起居。
儘管唐門郎中云此乃長期接觸暗器毒物後遺症,但唐湘心底明白是過去更多其它事才造就今日身體病痛,甚至久難痊癒。且即使近期潛心修行補天訣心法的久炎知曉知其身體狀況後親自配藥予他,卻終究僅能緩解前額刺痛與胸口悶痛之癥,多年來看醫仍然無人知曉此症究竟為何,彷彿唐門弟子正被某種不可視之物掌控。
靠著樹坐下,唐湘仰頭看向逐漸西沉之月,感受離開唐家堡後天地間流動氣息,空曠林野讓人感受到些許舒坦,不再窒息,彷彿久炎就在身畔。
思及此,其手撫不禁上胸口心臟旁蠱痕。
先感受子蠱安定,性命尚無受威脅,隨後透過未被面具遮住的眸子仰望漆黑天穹,男人心底浮現數載來破碎片段,伴隨暈眩刺痛。
這些日子來他與久炎聚少離多,許多時候僅能於心底念想彼此,畢竟他們間仍存阻隔,不管是身分、門派、責任或者更多沒能說出口的難解之題。
唐門弟子左手握緊胸口暗袋中護身物,腦海裡霎時閃過諸多模糊人影,其中最清晰的便是久炎,但也有看不清面容的人們,不知是死去或被遺忘,皆都使唐湘感到溫暖與悲傷。而他暗忖或許正這般想念時常使之出現幻覺,陷入迷離境界。
就在這刻,唐湘瞧見遠方有銀白色的蝴蝶繞著月飄搖而下,緩慢地朝他飛來,帶來熟悉草藥香。
「久炎⋯⋯」
他以苗語喃喃低吟,情不自禁伸出手想接觸。
而下刻其指尖竟碰到溫暖,緊接出現一雙手與其緊緊交扣,亮白鱗粉在他面前化為紫服銀飾,帶來思念呼喚。
「找到你了,阿湘。」
唐湘不確定是真是假,又或自己思念所生幻象。
只是他忽然湧出強烈睡意,讓雙眸不受控制逐漸闔上,墜入溫暖中。
如夢似幻。
፠
晨曦甫現,唐湘躺在久炎腿上陷入久未有的安眠。
他們在昨晚唐湘躲藏的巨樹上稍作歇息,久炎扯起披風蓋住彼此,取下郎君的唐門面具,動作輕柔將其劉海撥至額旁,以掌心替他擋掉逐漸明亮的天色,再喚出雙生蛇巡守四周後同樣有些疲憊靠上樹幹閉目養神。
這是隱密的地點,幾無人煙讓其安心休整到日上三竿。
清醒後久炎注意到青蛇已咬來鼠兔、白蛇叼來鴣鷓,他輕撫靈蛇身軀以示鼓勵,接著來到附近溪流,以唐湘行囊中的小鍋取水。唐湘則先撿柴生火,再從蛇口中接過獵物取小刀進行簡單處理,剝去毛羽後將內臟和部分肉餵給雙蛇當獎賞。
「你倒是收買他們收買得不錯啊!」久炎凝視繞在唐湘身邊的小青小白,訝異這幾隻挑嘴蛇難得願意食用已死去物,不禁失笑讚賞:「這麼多年,他們總算也親你了。」
「這樣算親?」唐湘邊問邊將切得工整的肉塊丟入鍋中,隨後於河邊洗去手上血水,方摸著兩隻靈蛇的頭道謝,只見牠們立即歡騰地盤起扭動。
將撿柴時看到的補身藥草清裡後丟入鍋中烹煮,久炎在唐湘身邊坐下笑道:「當然,信不信別人來做會被咬到下不了床?」
「⋯⋯信。」
唐湘完全不懷疑久炎的雙生蛇有多兇。
兩人享受山林鮮味後,飯飽起身收拾走回廢棄小房處。
途中唐湘伸手牽住久炎,久炎回握,兩人漫步在陽光斑駁林中,耳聞四周蟲鳴鳥叫,後方則是靈蛇滑行摩擦地上樹葉聲響。雙方都未開口,既無訴說久離別,也不互道見面狂喜,直到看見破舊屋瓦久炎才拉住唐湘問:「阿湘,你啊是不是又頭痛?」
郎君問話讓唐湘一愣,先想到體內的蠱,手下意識撫上胸口與胸前的護身物,突然明白為何久炎竟能在收到信前就出現於此,表情流露尷尬,彷彿做錯事被抓正著的小孩。而見他未直接回覆,久炎心中也理解七八分,表情肅穆直視唐湘雙眸,看得他只能從實招來:「近期又開始常痛,不知為何。」
「唉,我就擔心這個,等等幫你檢查個。」深嘆口氣,久炎眉頭難以舒坦,低聲抱怨:「只是你身體狀況不好,那些人怎麼還派你出來出任務?」
「他們不知我身體實情,自然派我來,倒是 ⋯⋯」
唐湘撇頭看久炎幾眼,那神態熟悉到五聖弟子立即能讀出對方欲言之語,終於重新露出笑意。
「是想問我為什麼在這?」伸手輕捏對方湘下頷,久炎直白解釋道:「當然是怕你身體出了甚麼狀況,要跟我說說發生什麼事情嗎?」
面對此問話,唐湘簡單講述唐門遭逢事端還有自身被賦予的任務,不過對於昏倒與無意識則多少語帶保留,就怕對方過於憂思。而剛聽完郎君講述,久炎眉間毫無掩飾厭惡,如同每次聽見唐湘提及唐門主唐傲天時皆為這般表情。
其實,久炎和許多排斥外族的五聖教弟子相左,對外族人沒甚麼意見,但特別討厭蜀中唐氏門人,並在唐湘師傅離世後對唐門好感全無,且次次覺得那些唐門門人間內各種試探著實不可思議,尤其他比誰都知曉,即使自己不斷勸說唐湘離開唐家堡,眼前男人也從未有貳心。
「你都做到這樣,你們那死 ——咳咳,幾位老前輩還在懷疑你的忠誠?」他不甘願問道,語氣滿是無法置信,畢竟那些唐氏門人對唐湘所做之事都令其感到憤怒。
當年久炎與唐湘關係在唐門傳開後,唐門門主勃然大怒將唐湘下藥囚禁於密室中,視為不孝之懲處,不允任何人擅自將其放出。
而許是出自殺手世家裡被恐懼培養出的疏離與自保,平常看似和唐湘友好、會求助其千機匣修繕的同門 ——無論本家人與外家,都無視唐湘所受之對待,要非唐湘徒弟莊臻奔來五聖和久炎求助,男人究竟遭遇何等對待恐怕永遠都成謎。
甚至事後久炎得知不少唐湘師兄姐就算同情唐湘遭遇,也皆認為前途可量的唐湘竟和他這苗番男人廝混胡鬧,一點小懲罰是理所當然,沒送至斬逆堂已是上頭開恩,更別提有本就不滿唐湘的同門於背地裡盡是嘲弄羞辱。
無論何者,唐湘都從未替自己辯護,只是任由他人閒語。
我久炎的男人為唐家堡盡心盡力,憑什麼受莫名其妙的委屈?
我又為何要受莫須有的羞辱?
面對這些話,沒甚麼耐性的久炎自是讓這些人體會惡蠱纏身、萬毒噬心痛不欲生,直到跪著來和唐湘求情才罷手。想當然爾之後無人再敢明目張膽戲謔唐湘,也造成久炎在唐家堡名聲的極為凶煞。
「這無可奈何。」唐湘回道,放開久炎的手轉而輕摸對方以示安撫:「畢竟是 ⋯⋯唐門。」說至此,他目光落在被久炎取走繫在腰間的半張面具上。
面具是唐門的象徵,代表除死者外無人能看到唐門弟子真正面容。
可能唐氏注定只能這般活下去。
生是唐家人,死為唐家鬼。
「算了,他們自是難以改變,我也無法理解。」對此久炎不再多談,心想唯一能做的是無論唐湘想繼續留在唐門或離開,自己都須站在他身邊,接著將話題轉回對方任務上:「喔對,你剛剛說唐懷義老前輩認為是我門弟子去⋯⋯竊取這個他們趁亂擁有的毒藥?」
他聳肩眉間透露厭煩,語氣毫不修飾。
「先說,聖教對於已流傳到他教手中的毒會直接視為廢毒,不可能主動去收回,更何況那些被唐家堡拿走的都還不是核心之毒,也不是屍典等級聖物,自然不會有人去追,他們太看得起自己了。」
對唐家堡久炎向來沒在客氣,見郎君那從未改變的神態,唐湘不禁揚起嘴角。
「他們總如此。」
他輕聲回應,並趁閒聊之際掃視四周,隨後跨過傾頹屋角蹲下檢查昨晚躺平處的痕跡。
看唐湘認真搜尋,久炎也不打攪,僅是攀上斷牆坐好讓出空間,凝視唐門弟子很快從地上找到其他毒藥罐碎片,並將其收入小囊。於這般搜索下,唐湘接續注意到旁邊桌面上污漬乃乾涸血跡,桌腳上則有黑色奇特文字,與沿著桌角下流的暗褐交融成團、難以辨識。
當其正困惑於此為何,久炎突然繼續啟唇詢問。
「是說,你剛剛說的那些中毒者都是什麼樣的人?有甚麼症狀?」
觀察那些奇特圖騰的同時,唐湘整理所知後應道:「皆為普通居民,先被封住全身脈穴,再以細針刺入腦中,使人對自己的身體失去控制。頭痛、身體無力,嚴重者會失去心神。」
聞言,久炎陷入沉默,撐下巴思索。
失去控制、失去心神 ⋯⋯
難道 ⋯⋯
在離開總壇前五聖教的確好幾起類似的中毒與失蹤事件,前些時日久炎跟香卡配製的就是解藥,此刻男人神情凝重訴說:「其實,貌似天一之徒最近又在聖壇一帶活躍起來,這邊也有普通居民被抓去試藥試蠱,其症狀與你所描述的非常相似。」
天一二字出來,唐湘未多思索就應允:「這幾個點搜完我同你回聖教。」
「這自然好啊!」郎君反應使久炎笑得眼睛瞇成線,他自然喜歡與唐湘共同回聖域,語調不禁浮現愉悅表示:「那我們路上順便繞去幫師傅帶上她喜歡的東西吧。」
可異於久炎的好心情,唐湘面對眼前的符文陷入苦思。
此圖騰怎如此眼熟?
盯緊其中某個保留最完整的符號,唐門弟子覺得莫名熟悉卻半刻毫無頭緒,下意識呼喚久炎:「久炎,這圖案你可有印象?」
「哪個 ——」
然當久炎正欲上前,唐湘臉色猛然大變,急速反手將久炎拉下牆按入懷中,順勢躲進陰影。
霎那間,數支倒針以穿岩碎石之力插在久炎原先坐處。9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9aFzTKuWlW
(下回待續)
ns3.22.79.36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