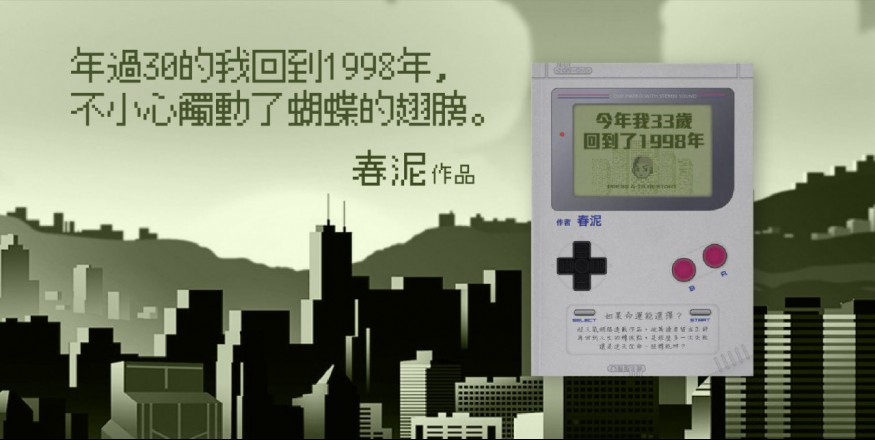別過游大輝後,我回到了葵涌村,阿婆開始準備晚飯、阿公就坐在沙發看亞洲亞洲的六點正新聞、阿興在玩GAME BOY,而我則與年紀最小的表妹阿碧玩,我比亞碧年長十二年,在二零一六年的時候,她已經長得婷婷玉立,但這時她還未夠三歲,逗她玩的時候,我有種當父親的感覺,不竟我實際年齡已經三十三歲,正常來說這個年紀已經成家立室。
亞婆喊道:「開飯喇!」
我開枱、鋪枱布、入廚房把飯菜拿到桌上,五舅父與五舅母開夜班,所以只有我們五人吃飯,四菜一湯,有阿婆最撚手的鹹菜炆豬肉、煎紅衫魚、清炒菜心、番茄炒蛋和西洋菜湯。
「阿公食飯、阿婆食飯、阿興食飯、碧碧食飯。」
我扒了一口飯,夾了舊鹹菜,那是一份久違了的熟悉味道,番茄炒蛋雖然做法簡單,但我吃過很多地方的番茄炒蛋,其他人煮的連阿婆的一半也比不上。
未幾,視線亦變得模糊起來,不斷有淚珠從眼角滑過臉上掉下來,這幾天我實在很眼淺。
阿碧指著我道:「志哥哥喊!」
阿公道:「欸!做咩食食下飯喊?」
阿婆道:「又頭痛?」
我以紙巾拭淚,道:「無事,大家食飯。」
這頓飯,我基本是以淚送飯,我和阿興自小便是被阿公阿婆一手帶大的,想不到他們仙遊多年,我還有機會和他們吃飯我焉能不感觸落淚。
吃完飯,我堅持幫阿婆洗碗,今天不知明日事,現在有機會給我盡一點孝義,是我的福氣,失去他們的時候,我想待他們好一點亦不能。
吃完飯大約八點,我和阿興別過阿婆阿公,起程回到石梨貝的家,我父母離了婚,原本我們三母子一同住在石梨貝的公屋,但不知為何變成了老豆和我、阿興一齊住,阿媽搬出去住,我對阿爸沒有好感,除了因為阿爸曾經在我面前打阿媽之外,我覺得他並沒有盡一位父親應有的責任:他好像沒有固定的工作,我和阿興的零用、開支、伙食費都由阿媽供給,他不是在家裡瞓在沙發上看電視,便是到樓下公園撚雀、去山溪捉魚毛,有時還不知跑到那裡去,幾天不回家。
我和阿興要到光輝圍搭31M巴士返石梨貝的家,由葵涌村去到光輝圍要經過一條長樓梯,這時阿興問道:「哥,你話你知道未來十八年發生嘅事,不如你去買六合彩喔!中咗會有好多錢,到時可以買間大屋。」
阿興真是…,如果我知道我跳樓會由2016年回到1998年,我當然會記熟每期攪出的六合彩號碼,但問題是我事前並不知道會回到1998年,試問那有正常人有興趣會去記熟每一期六合彩的攪出號碼。
我笑道:「依樣我就唔知,不過我就知道曼聯今屆會有好好成績,會做三冠王,奪得歐冠、英超同埋足總盃,不過最衰依家馬會無波賭,如果唔係可以贏番筆。」
阿興道:「乜馬會遲啲有得賭波咩?」
「有,仲有好多玩法添,咩總入球、讓球主客和、入球單雙,連邊個入波先都有得玩。」
阿興聽得似懂非懂,他提議道:「不如我地同媽咪舅父佢地講,可能佢地有辦法呢?」
「千祈唔好,我知道未來十八年發生嘅事,你邊個都唔講得,連阿媽同阿婆都唔可以講。」
「點解啊?」
「因為……因為傳功畀我嗰位高僧話,我本身有二百歲命,但如果我講畀一個人知就減一半壽命,依家我講咗畀你聽,我得番一百歲命,你再講畀阿媽聽,我就最多生存到五十歲;講埋畀阿婆聽我二十五歲就可以去賣鹹鴨蛋。」
阿興捂住嘴巴,重覆道:「我唔同人講,我唔同人講。」
「你都唔可以同其他人講:『我講樣野畀你聽,但你唔講得畀其他人知…』,咁樣都唔得,知唔知道?」
阿興點頭,我伸出尾指,道:「勾手指作實。」
我勾著阿興的尾指道:「依件事得你知我知,唔可以講畀其他人知,如果唔係就…」
阿興道:「如果唔係就點?溝唔到囡?」
「如果唔係你就快過我做老豆。」
現階段我還不想把我來自二零一六的事再向其他人透露,因為他們大多數的反應均會把我當成神經失常,而且還未知道歷史會否重演?畢竟我原本的命運好像生出微妙的變化。
我們行到光輝圍,我向阿興提議道:「不如我地唔好搭巴士,行路返屋企喔?」
「好啊!」
搭巴士不包括候車時間,車程差不多要二十分鐘,行路的話最多只需三十分鐘,這時候的天氣沒有2016年的香港那麼熱,加上我那副十五歲的身體並不似現在那麼容易出汗,我們由光輝圍經天橋到了另一邊青山公路,落了天橋,我看到自詡為龍蝦專家的漢寶酒家,在一六年時,這酒家經已結業多年,而現在則客似雲來,經過葵星中心,我問:「阿興,前面係咪有間小食店,啲豬扒包好好食架。」
「係啊!」
於是我們到了那間小食店,用原本搭巴士的錢買了一個豬扒包,那個豬扒包只是四元;在2016年,四元是連豬仔包都買不到的。
我和阿興一人一半,邊行邊吃,多年前的記憶都回來了,那種味道、那種價錢,我是回到了貨真價實的1998年。
我們經和宜合道,轉上大隴街,行到石籬街市時,看到了一班衣著很像電影古惑仔的少男少女,他們大都有染髮,最讓我注意的是當中一位穿著吳林紫娣校服的少女,我與她打了個照片,少女姝豔嬌麗,有七分似鄭家純(是台灣那個,不是香港新世界那位純官),亦有三分似喜劇之王裡的柳飄飄,那種鍾靈毓秀的風情帶著幾分率真爽朗,落在她身上並沒有違和感,此女身形不高,大約一米六高,黃蜂腰、且上圍在香港女生來說,算得上十分驚人,屬於「廟細燈籠大」的類型。
以現在的詞語可以標籤他們為MK仔MK妹,但當時並沒有這個TERM,應該叫街童、爛仔、飛仔、老泥妹、WET仔WET妹定古惑仔古惑女呢?
此時,一名留著藍色長髮、身形高而瘦削的WET仔,向著我罵道:「望乜撚野啊?」
如果我仍是那個十五歲的成皇志,我應該會淆底,但我是來自2016年的成皇志,我根本不怕,不是我變得好好打,而是一個人人生閱歷多了、個人變得成熟,這些事情根本不值得怕。
我站著一瞬不瞬地瞪著那個藍髮青年,他雙手握拳,裝腔作勢地道:「咩啊!包住頭扮阿差,我就驚架,過嚟隻抽喔!」
我仍然站著原地瞪著他,阿興站在我的身後,害怕道:「阿哥走啦!」
此時,那名穿著吳林紫娣校服的少女,拉著藍髮青年道:「走啦!南乳,我地去篤波喇!夠晒鐘喇!行啦!」
那名叫南乳的藍髮青年看來很聽那少女的話,跟著那群WET仔WET妹遠去,但他仍然要拿回尾彩,回頭向我罵道:「屌鳩你啊!死傻仔,下次見鑊打鑊啊!」
他們走了,阿興問:「阿哥,你頭先唔驚咩?佢地咁多人?」
「有乜好驚?你驚佢地,佢地先會恰你,阿哥講過,如果有人恰你,阿哥一定會幫你出頭。」
我們行到大LIFT,搭LIFT上去石梨巴士總站,再步行回位於五人足球場隔鄰的石逸樓。
沿途我一直在想,那少女有點面善,但一定不是4D班的同學,明天上學會不會遇到她呢?
回到家,阿爸不在家,大門旁有個大的街燈罩,被他放在鐵架上當魚缸,缸裡面飼養的不是金魚,而是他從溪澗捉回來的山溝魚,人家拿來餵魚,他則當作寵物。我打開雪櫃,與以前一樣,雪櫃沒有什麼人吃的食物,有一大包用來餵雀的草蜢及爛蘋果,和幾支入滿水的膠樽。露台有十幾個鳥籠,有相思、白頭婆、麻雀等。
「阿興,你用唔用厠所?唔用,我沖涼先。」
「你沖先。」
石梨貝這個家是沒有洗衣機的,通常我和阿興會收集了星期一至星期五的衣物,在星期六的早上帶上去阿婆家,阿婆用洗衣機幫我們洗,但內衣褲則我們每天洗澡時自己用手洗。
石梨貝的家厠所連浴室,當洗完澡後,整個厠所無論地板、牆壁,甚至馬桶亦會濕答答的。馬桶是舊式抽水馬桶,沖厠手柄是一條尼龍蠅向下拉(在大時代一劇裡,丁蟹在監倉打算用來自殺的那類用作沖厠的尼龍蠅),而厠所板內則不是鈍口的,內則那個邊緣有點利,開大時坐得久,會磨得大腿刺痛有痕,坐得非常不舒服。
洗完澡出來,看到阿興打PS的WINNING4,他問我:「阿哥,你玩唔玩啊?」
「好啊!玩陣。」
我看到那些爆格的畫面,一個又一個方塊人,難以辨認誰是碧咸、誰是傑斯,巴西隊光頭的應該是朗拿度吧?
玩了一鋪後,我實在提不起勁,以前一隻WINNING 4,我可以玩得廢寢忘食,但現在玩回這種畫質的電玩,真的沒有興趣。
「阿興,你自己玩啦!」
阿興獨個兒在客廳玩PS,我進了房準備明天上課要用的課本,打開手冊一看,明日有中文、英文、BIO、CHEM。
順帶一提我和阿興住在一間房,阿爸則住在隔壁,其實嚴格來說並非兩間房,兩間房只是隔著一塊用木板做的移門,而那移門長期是敞開的,我那邊的房間是沒有窗和冷氣的,只能打開房門作空氣對流。
準備完畢,我躺在床上,這時我沒有電腦、手機亦未能上網、而PS我亦沒有興趣,還好我在圖書館借了本書,之前等游大輝的時候,沒有認真看,於是我從頭再看。
原來杜月笙原名是杜月生,他的父母早亡,由繼母養育,後來他繼母失蹤,有傳被人擄走,流落風塵接客,總之最後飛黃騰達的杜月笙就沒有再見到繼母…
看了廿多頁,我有點睏,此時已經十一點,阿興亦準備睡覺。
關上燈,阿興睡在下格床,而我則躺在上格床上,阿興問道:「哥,你話你知道未來十八年嘅野,咁你十八年後有仔女未?」
我苦笑道:「無,未結婚,連囡都無?」
「阿哥,咁你依家要努力喇!」
「依層我有分數。」
「咁我十八年後係點?」
「唔係咁理想,所以你真係要畀心機讀書,唔好打咁多機。」
「咁阿婆、阿公呢?」
此時,我發出均勻的呼吸聲,阿興再問道:「哥。」
阿興見我沒有回應,則喃喃道:「乜話瞓就瞓。」
未幾,下床傳來阿興的呼吸聲,而我仍然睡不安穩,想了很多人和事,好像管佳莉、陳依官、成敏研等一眾舊同學,然後想到剛才遇見的那名同樣就讀吳林紫娣的女學生,那種樣貌和身材如此出眾的女同學,我沒有可能不記得她是誰,論級數就是和被譽為吳林紫娣第二最美校花的宛琳珊亦毫不遜色,身材方面就更加大勝,一想到第二最美校花,我立時聯想到第一校花,難道她就是布—正—麗。
ns3.135.192.51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