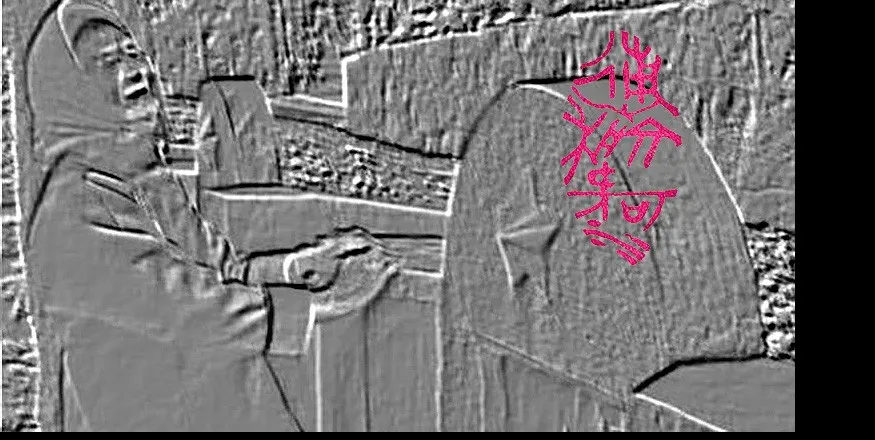導讀:河役的最後一天,梁德龍感冒了,工地上的醫生幫助打了一針,這針效果如何?
第三章(上)
雙調•湘妃怨
繈褓失爹只剩娘,分田地飽了肚腸,大食堂又饑了荒。
挖了通榆河,卻把小命喪。
婆媳兩個寡婦,日子那叫淒涼,白天閻王。
35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L6XGHlqiHb
玉米衣包澱粉,一個月下來,每個人都瘦了一大圈,連吳隊長都看上去消瘦了些。
天從昨天開始就變得陰沉下來,可能要下雨了。
吳大宏推著那輛飛鴿走回到了工地,臉上象天氣一樣的陰沉。
“開會。”吳大宏聲音很是嚴厲,看樣子在工地幹部會議上受到了批評。
“大家自己也可以看看人家,快的都要快完工收尾了,再看看我們自己的進度,今天工地幹部會議,我就被點名批評了,請假的請假,遲來的遲來,我們開挖的這一段離河床還有兩尺高呢,馬上就要下雨了,一旦下雨,水流到底部,河床又沒有弄好,到時候怎麼辦,挑水更麻煩,所以上面決定,連夜要趕在下雨之前把河床弄好。” 吳大宏才二十一歲,一直認為自己根基很淺,別人對他是陽奉陰違,幹活故意拖拉,以至成這樣。
大家心裡都憋著氣,心說你吳大宏到梁家莊才幾天,你小子真運氣,莫名其妙的就當上隊長了,你家祖墳葬在什麼寶地上,你那個當和尚的爹也會看風水麼?
隊長這個牌子還是有威信的,你再看不慣吳大宏這個人,但千萬不能看不起隊長。
再苦,再累,再饑餓,隊長發話了,今夜一定要把河床弄好。
35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x9KDp9z4wv
“兄…兄弟,我看…看這兩…兩天你沒…沒精打采的,臉色也…也不對。”德勝看著德龍這兩天像霜打的茄子――蔫了。
“三哥,這個勞什子玉米衣包澱粉吃下去我老泛酸水,胃有點難受,看到我就不想吃。”
德勝知道兄弟是餓的,但也沒有辦法。
“兄…兄弟,今…今天…你你…挑平地。”
“好的,三哥。”
工地上打著火把,遠望去一條長火龍看不到邊,看來大家都一樣,能提前完工的畢竟很少。
後半夜,淅淅瀝瀝的下起了小雨,這要人命的雨啊。
“快點挑,快點挑,等雨下大了就完蛋了,大家抓緊啊。” 吳大宏穿著一件蓑衣,戴著一個斗篷,聲音似乎要哭,當初他那和尚老爹死了也沒有看到他這樣著急過,唯一一次爭吵,是和哥哥爭是用缸還是用棺材葬父親。
雨越下越大,火把已經被人用簾子罩在上面,看樣子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挑著擔子的步伐越發沉重,腳底下很滑,一不小心就能翻滾下去。德龍臉上流下的不知道是汗水還是雨水,沿臉流下,呼吸都感到很困難。
“兄…兄弟,吃不…不消就歇…歇會兒。”
“不了,三哥,我頂得住,馬上快挑完了,不要讓吳大宏這小瞧了咱。”
35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RyRndWJoP6
天終於亮了,被弄熄的火把被雨水弄濕了,“吱吱”的冒著青煙。
河床上該挖的土終於被弄走了,吳大宏松了一口氣。
德龍甩掉身上的衣服,鑽進被子裡,蜷縮成一團。
“德龍,感覺怎樣?”德勝看到兄弟病了,一緊張,說話似乎不結巴了。
“三哥,我冷啊,把你的那條被子也給我蓋上。” 德龍連牙都打著顫。
“好的。”德勝伸手一摸德龍的額頭,好傢伙,滾燙滾燙的,“兄弟,你發燒了,我去弄點熱水給你喝喝。”
喝了點熱水,蓋了兩條被子。
“兄弟,出點汗就好了。”
德勝一眼看下去,帳篷全躺下了,不只是德龍一個人生病了,只是他們沒有德龍嚴重罷了,更多的人在打著噴嚏。
外面的雨還是一樣的下著,工地上的泥土和著雨水,一步下去就能把腳背淹下去。
一個多時辰過去了,德龍沒有出一點汗,還一個勁的喊冷。饑餓,困乏已經無法讓德龍再流出汗來了。
“吳…吳隊長,很多…人都病…病了,你看…看,德龍病…病得太…太厲害了,請個…個醫生吧。”德勝老實人,一臉憨厚。
每次聽到德生說結巴話,吳大宏都想笑,以致自己接著說話的時候都要情不自禁的結巴起來,但眼前站著的這位是自己的嫡叔丈,學著他說話是千萬不能的,這個錯誤是不能犯的。自己老丈人身體不好,以前每次他的河工任務都是自己頂著去,那時自己還沒有18歲,要不是眼前的這位叔丈幫助,就憑自己這副身子骨早被壓趴下了,沖這點,面子也要給的。
“好的,三叔,我去找醫生。”吳大宏脫下黃膠鞋,換上一雙草鞋,穿上蓑衣,戴上斗笠,出去了。
到了晌午,吳大宏走進了帳篷,後面跟著一位穿著白大褂,背著一個白色藥箱,腳上套著一副雨靴,撐著一頂黃油布傘的人,中高身材,約莫四十多歲。
“醫生來了。”
“看樣子比大隊診所的醫生高級。”
“是西醫?”
……
確實是西醫,通榆河這麼大的工程,上頭還是從縣醫院抽調了一些人作為工地醫生。
“哪位生病了?”醫生一面詢問一面向帳篷裡掃描了一遍。
“這個,這個,蓋…蓋兩條被…被子的。”德勝象看到救命稻草似的說道。
醫生走到德龍地鋪前蹲了下來,把藥箱放在草褥子上,打開箱子,取出了一個白色的兩頭半圓的鋁制的盒子,打開,取出了一支細長亮晶晶的象發簪一樣的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在場的人絕大多數都沒有見過,到大隊診所看病,都是把脈的,醫生把眼睛閉起來,半晌,才說“陰虛、陽浮、氣血兩虧、邪氣淤滯”等一些讓人聽不懂的話,再就抓點藥回去熬著喝。
醫生把那亮晶晶的東西在手上甩了甩,放到德龍夾肢窩裡,說了句“夾緊”,又從藥箱裡拿出一個軟長管一頭有兩個做在一起向內彎的鉤,一頭栓著一個象袁大頭一樣的東西,醫生把那兩個鉤鉤進了自己的兩個耳朵眼裡,把那塊袁大頭放在德龍的胸部和背部一會,然後從耳朵上取下來,繞了幾下,放回藥箱,又從德龍夾肢窩裡取出那支發簪,看了看,又用手甩了甩,放回剛才的那個鋁制的盒子裡,蓋上,放回藥箱。
“發高燒啊,很重的,現在感覺怎樣?”
“冷啊,就再加十條被子也覺得冷。”
“曉得了,打一針吧,你會好受些,最好能喝點姜湯,你真幸運,我藥箱裡還剩下最後一支青黴素,先做個皮試吧。”醫生從藥箱裡取出一個形狀和剛才一樣但大得多的鋁制盒子,說了句“弄一個大的碗盛滿開水給我,要剛開的水,碗要洗得乾淨點”。
德勝跑到燒飯的地方找一隻乾淨的碗洗了又洗,好在一鍋熱水剛開,水在翻滾著,德勝用那只碗去舀水,熱氣一下燙到了他的手,手一滑,碗掉到鍋底了,被翻滾的水拱著 “篤篤”直響,他只得用兩雙筷子把碗挑了起來,舀滿水,用衣服角托在手上,送到醫生面前。
醫生打開鋁制盒子,從裡面取出了兩支形狀一樣但粗細相差很大的有胡蘿蔔大小的玻璃管子,拆開,放進德勝端來的碗裡,又扔進了兩個形狀線棰一樣縫衣針大小的東西。又拿出一個比香煙盒大得多的白色的紙盒子,放在草褥上,打開,裡面分成好幾個單閣,放著一支一頭細一頭粗的裝著大半水一樣東西的玻璃瓶子,又從藥箱裡拿出一個大拇指大小的圓形有蓋的玻璃瓶子,放在那個白色的盒子裡面,眼精的人看見裡面有麵粉一樣的東西。
醫生又從盒子裡取出一個夾子把碗裡的那粗的玻璃管撈起來裝上,眾人這才看清縫衣針被裝在玻璃管子的最前頭,醫生把碗裡的水抽進去又打出來,如此往復幾次。只見醫生把那個紙盒裡的一頭細一頭粗的玻璃瓶子拿出來在手裡轉了一下,用兩手一扳,只聽進“叭”的一聲,細的那頭竟然被醫生扳斷了半截下來,眾人嚇了一跳,心說“乖乖,這怎麼弄的?”醫生把瓶子裡的水吸進了剛才那個玻璃管裡,又把針頭插進那個裝有白麵粉的玻璃瓶裡,把水打了進去,把玻璃管向上翹著擱置在白紙盒上,抓住瓶子在手上上下搖了兩下,交給德勝說道:“幫住搖搖。”
德勝接過來學著醫生的樣子,抓住瓶子在手上上下使勁的搖著,這會兒醫生從碗裡用夾子把那支小的玻璃管象剛才一樣裝上,同樣把碗裡的水抽進去又打出來,往復幾次。
“好了。”醫生把那個玻璃藥瓶從德勝手裡要了回來,看著德勝象做重活一樣似的搖著瓶子,笑了:“哪用得著使這麼大的勁。”用細玻璃管子從瓶中抽出了一點點藥水,又把粗玻璃管子的針頭插進了玻璃藥瓶裡,直到針頭全部進去,輕輕的放在白紙盒上。
醫生把那個細玻璃管裡的藥水朝上向外擠出了幾滴藥水,從白色的鋁制盒子裡面拿出一塊蠶豆大小的濕棉花在德龍左手腕內側稍向內的位置擦了擦,把針頭插進皮膚裡,向上挑了有米粒粗的高度,把藥水打了進去,德龍痛得“噝”的一聲,聽到這個聲音,所有人的臉上的表情都象受刑罰一樣揪了起來。
“做皮試是有點疼的。”醫生一邊安慰一邊把這個細玻璃管放進了原來的盒子裡,拉開左手袖口看了看,大家看見那是一塊手錶,都吃了一驚,我的天啦,這東西多貴啊,吳隊長都沒有耶,大家用比敬畏幹部一百倍眼神看著這個醫生。
這當兒醫生又看了看其他人,都是一般輕微的感冒,囑咐大家多喝點水,適當休息,不要著涼。
約莫半柱香不到的工夫,醫生又拉開左手袖口看了看,說了句“時間到了”,拉著德龍的左手腕看了看, “可以打針了,幫助把他的屁股露出來”。
醫生又拿了一塊蠶豆大小的濕棉花是德龍屁股上擦了擦,輕輕的把針頭插了進去,慢慢把藥水打了進去,拔出來時用一塊蠶豆大小的幹棉花按住打針的地方,跟德勝說:“幫助按一會兒,不要揉。”
醫生把自己的東西收了起來,約莫又過了兩袋煙的工夫,進來一個氣喘吁吁的人:“醫生,醫生,我找你很久了,我們那,有個人暈過去有一個時辰了。”
醫生連忙轉身看了看德龍,又看看了看表,說了句“不礙事了,要注意休息。”就跟著來人走了。
35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fJUggsz5vW
還是西藥好啊,見效真快,到了晚上,德龍淌了一身大汗,德勝弄了點吃的給他,德龍也就安穩地睡下了。
德龍一直睡到天亮才醒,真舒服呵,比昨天好得多得多了,自己也感到奇怪,這西藥打針真是神啊。
雨變小了,但還是淅淅瀝瀝下著。大家都苦了幾個月了,天放晴了就可以回家了,難得有個休息的時間,有人帶了紙牌,玩起了葉子牌,玩牌的只有四個人,圍觀的一大堆,叫聲、爭執聲,敲旱煙袋的“篤篤”聲,連成一片。
反正下雨,也回不了家,睡覺是個不錯的選擇,上了年紀的都是這麼想。
德龍早飯後繼續躺在被窩裡,不停地左右換著抓著掌心,早上開始他就感到掌心發癢,臉上也感覺到有點不舒服,用手一摸,起了幾個疙瘩,喉嚨感覺有點痛,躺著不舒服,坐了起來,一樣不舒服,再躺下還是一樣,索性穿了衣服,起來去看人家打葉子牌。
走起來,才感覺到有點心慌,喉嚨咽吐沫都感到卡人。
“德龍,怎麼眉頭都皺起來了,早上還看到你說笑呢。”
“生病哪有這麼快就好的,你以為真的是仙丹妙藥呵。”
“要是在莊子上也有這麼好的醫生多好呵,乖乖,那些東西我見都沒有見過,德龍,你真的運氣好耶,昨天醫生不是說了嗎,這叫什麼來的藥最後一支了,要不你現在還不知咋樣呢?”
“我們以前都是這樣的,傷風一次,喝點草藥都得躺個四五天的。”
“德龍,你還是躺著吧,醫生不是叫你多休息的嗎。”
……
“三哥,三哥。”德龍感覺喉嚨越發疼痛,臉上的疙瘩已經擴到胸口上了。
“我…我在呢,兄…兄弟。”德勝看到兄弟呼吸有點急促。
“三哥,我喉嚨卡得厲害。”
德勝看到德龍臉色開始發紫,嚇得不輕,旁邊有人連忙喊到:“吳隊長,吳隊長,快過來看看,德龍臉色有點不對。”
“叫什麼?這昨天不是剛剛打過針嗎,這麼快又犯了?”吳大宏正看著報紙,在這幫半目不識丁的土包子面前,他喜歡這樣表現出他識字斷文的斯文相。
吳大宏將報紙對折好放到口袋裡,走了過來,一看德龍臉上,脖子上,胸口上全部是紅色的小疙瘩,臉色發紫,呼吸急促。伸手摸了一下德龍的手,好涼,指甲顏色發紫。
“這出痧子也不至於這樣呵。” 吳大宏自言自語,看到德龍像豬肝似的臉,他感到事態很嚴重,這要是死了人可不得了。
“好的,你們看著,我去請醫生。” 吳大宏跨上那輛飛鴿,飛似的去了。
很快,吳大宏載著一個五十多歲,穿白大褂,背著藥箱的醫生來了。
“讓開,讓開。”醫生分開人群,走到德龍的地鋪前。
德龍躺著一動不動,臉色象成熟了的紫茄子,醫生拿出昨天一樣的東西鉤進耳朵裡,把那快袁大頭在德龍胸口放了放,又拿出一個比蘿蔔大點的一頭射出光的東西撥開德龍的眼皮照了照。
“唉!”醫生歎了口氣,“什麼時間發的病,看過醫生了嗎?”
“昨天發燒,醫生打過針的。”有人連忙把昨天倒在外面的藥瓶拿了過來。
35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W4xFSXMSBI
35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ksUp2o9p6a
導讀:梁德龍打青黴素陰形過敏,喉嚨里起了大水泡,活活的被憋死了,這讓孤兒寡母的怎麼活?
第三章(下)
醫生接過來看了看,又還給了那個人,說道:“青黴素陰性過敏,沒得救了,料理後事吧。”
醫生聲音不大,卻讓所有的人都靜了下來。
德勝一下子就跪了下來:“醫生,求…求你救救他啊。”
“醫生,救救他吧,他才二十歲啊,上有老人,下有孩子,你行行好吧…”
“醫生救救他吧…”隨德勝後面跪下了一大堆,吳大宏嚇得不知所措,站在那裡一點也動不了。
“各位鄉親,晚了,如果早一點也許能救過來,喉嚨裡起了大血泡,不透氣,憋死了,青黴素過敏,來得很急的,我以前碰到過一次的,也是這樣,唉,料理後事吧,我也無能為力了。”
醫生收起東西,走到吳大宏面前,搖了搖頭,歎了口氣,走了。
35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nph0i5k7TD
“兄弟啊,”德勝撲到德龍身上放聲大哭。
“吳隊長,這這咋辦啊。”
吳大宏一下子愣過神來,這怎麼辦?遇上這麼大的事,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辦才好,要是我那老丈人在就好了,可惜他那個大肚子病不能來河工呵。
“隊長,要不告訴大隊聽一下吧。”
一語驚醒夢中人,吳大宏心反而一下子穩定了下來,趕緊將臉上的慌張掩飾過去,恢復了隊長的口吻:“大家靜一靜,我去河工大隊處彙報一下。”
吳大宏推起那輛飛鴿,逃命似地走了。
35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mOpZrynLKE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三十裡的距離,消息象風一樣已經刮到了梁家莊。
梁家莊三面環水,德龍家坐落在莊子的最裡面,靠河邊轉彎處,河畔上長滿了芒柴、蘆竹和野薔薇(白殘花),屋子後面有一道三尺寬的泥臺階直通水邊,是家裡取水,洗菜和洗衣服的通道,還有幾天才立夏,還沒有到芒柴、蘆竹和野薔薇開花、飛絮、飄香的時候。
四兄弟中粱德凱最精明,最善於處理棘手和複雜的事件,而且多少識幾個字,碰上這個事,也只有他出面才能處理好一切。
梁德凱把為自己準備的那副棺材拿了出來,他知道自己有大肚子病,說不定哪天就去了,所以早給自己做了一副,前後刷了幾遍油漆,黑得埕亮。自己只有一個女兒,老婆生了女兒後就沒有再生育過,為這事他也不知煩惱過多少次,所以才招了吳大宏這個上門女婿。梁德凱把棺材捐出來有兩個目的,一是三嬸家現在除了承闊一個三歲的男孩外就是兩個寡婦,這個喪事說什麼都沒有能力辦下去的,家族裡的人或多或少都要捐出點錢,不如就把棺材捐出來,這份大禮足以讓自己在家族裡把頭抬起來,沒有兒子又怎麼了,自己照樣是家族裡的頭;二是德龍是自己女婿帶出去服河役才死的,雖然死於醫療事故,但多少有點責任,把棺材捐出來有點補償的意思。
德龍的屍體被平放在反架在兩個一前一後的長凳子上的棺材蓋上,頭前點這長明燈,停在正堂的西邊,農村習俗是有嫡孫輩的停在正堂東邊,沒有的停在正堂的西邊。滿屋子漂浮著燒了的黃表紙的灰,德龍媽哭暈過去好幾次,躺在大堂侄媳婦的懷裡,二堂侄媳婦不斷地給她撫摸著胸口,桂花腆著大肚子坐在地上,已經五個多月了,摟著承闊,斜躺在三堂嫂的懷裡,臉上掛著淚水,她已經哭不出聲音來了,任何語言也不足以來形容她的悲痛。承闊頭上戴著麻帽身披麻布,被媽媽摟著,他不明白為什麼爹爹躺在板子上一動不動,看著媽媽奶奶哭成這樣,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嚇得驚恐萬狀,哇哇大哭。
承字輩及往下輩份的人都戴著孝,農村習俗中長輩平輩不用戴孝的,門裡門外都是莊子上的男男女女,有流淚的、有輕聲哭泣的、有歎息的、更多的都是以一種惋惜的表情看著。
正堂的東邊,方桌前,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年輕和尚敲著木魚,嘴裡念著誰也聽不懂的經。
“有這麼年輕的和尚,我見過的都是一些老得鬍子老長的。”
“這年月,那些老和尚誰請得起,估計小和尚價錢便宜些。”
“什麼和尚,現在哪有什麼真和尚?都是些懂得念經做法事,出來賺錢的,你去三昧寺看看,裡面都是一些老得掉了牙走不動路看不清東西的和尚,年紀輕點的早還俗了,娶老婆的娶老婆,生孩子的生孩子,咱隊……”
“你們看,這和尚和咱們吳隊長長得很像吔,尤其那眼睛和鼻子。”
“咦,你別說,你眼睛真精吔,還真有點像。”
“不要瞎說,被隊長聽到了,還不抽你個耳刮子。”
……
人死了,入土為安,德龍的墳是在莊子後面河那邊的土地上,圓形,頂上是兩個錐形放置成沙漏壺形的墳帽,墳邊插上了一根柳條,那裡是梁家的祖塋。
頭七到斷七,桂花就這樣恍恍惚惚的過來了,所有的事件都是三位堂兄幫助做的,直到現在,在她心裡仍然不相信德龍已經死了,雖然站在河邊遠望去就能看見那黃色圓土墩,在她心中,德龍只是暫時離開了,他只不過是在外面河工上幹活,他還會回來的。人們經常看到這樣的場景,夕陽下,一個大肚子的孕婦一手牽著一個小孩一手叉在後腰間,像雕塑一樣看著河的那邊入神。
也許是經歷過人的生死離別,也許是覺得這個家還需要過下去,有三歲的孫子,還有兒媳和兒媳肚裡沒有出世的孩子,自己再不把悲痛壓縮到心靈的最深處,埋藏起來,這個家可真的要完了,桂花的婆婆拿出了當初沒了德龍爹時活下來的勇氣。
35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26Dp2WeqhZ
“呱…呱…”一陣嬰兒的哭聲從桂花家的房子裡傳來,接生婆嫺熟地稱了一下,把嬰兒光著身子趴在桂花的懷裡,轉過頭對桂花婆婆說:
“三太奶奶,恭喜啊,6斤的小子,雖說不是那種胖乎乎的,但在現在這個日子下,能生出這麼好的孩子真不容易呵。”
桂花的婆婆和桂花的三位堂嫂,每個人的臉上都飄溢著喜色。
桂花微抬起頭,眼珠吃力地向下轉著看著這個剛出生的兒子,黑黑的胎毛,一雙濃眉橫臥,大眼睛,完全不是自己的柳葉眉、杏核眼,桂花喜極而泣,活脫是一個小德龍,我的二娃呀,你可真的像你爹呵。
都說女兒像爹,兒子像媽,可二娃是個例外。
這天農曆七月初七,傳說中牛郎織女相會的日子。
35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BQ2dbYe7WG
“七弟啊,你眼睛不好,幹嗎自己親自過來送這月子禮,叫小月同你過來也好呀。”
看這剛剛坐下的弟弟,桂花的婆婆心疼地責備。
“姐,沒有事的,我走慣了,有根竹棒就行,我又不走那個木橋,從莊口轉過來的,告訴你個好消息,你侄女小月也雙身子了,五個多月了,用不了幾天,我也要做爺爺啦,這我都等了快兩年了。”七瞎子一臉高興。
“真的?那太好了,七弟呵,你也曉得,今年發生的事太多了,我也沒有去看看你。”
桂花的婆婆眼淚都快掉下來了:“女婿對你咋樣?”
“你說文山啊,挺老實的孩子,能幹活,莊戶人家,要的就是這個,滿足了。姐呀,過去的已經過去了,你呀多從桂花和兩孫子上想想,香火都接下來兩支了,要高興才對。”
“哎,兄弟,我聽你的,這兩天正打算要去找你呢,這孩子還沒有取大名呢。”
“噢,哈哈。這孩子七月初七生的……己亥、壬申、甲子……”
瞎子翻著無光的眸子,頭腦裡默默地排著盤,心中暗道可惜、可惜,將星、亡神不在同一柱中,如同在日柱,國家棟樑呵……不過還好有天乙、月德、文昌、太極四大貴人……
半晌,瞎子開口說道:“六姐,這孩子命中帶學堂、詞館,是塊讀書的好料,要好好調教,書讀成了,不愁不能光宗耀祖。”
“是嗎,七舅爺,這可太好了,咱梁家祖祖輩輩也沒有出一個讀書人呵。”桂花的聲音從房中傳來,聽得出,桂花心中充滿喜悅。
多少天了,桂花的婆婆從來沒有這麼舒心過。
“七舅爺,親戚中就你讀過書,你幫這孩子取個名吧。”
“好的,當初給承闊這孩子取名時,取天闊地廣之意,既然哥哥叫承闊,弟弟就叫承廣吧。”
“梁承廣。”
“好名字吔,還是七舅爺墨水多啊。”
356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euS7XcB6Du
桂花的心情好多了,孩子出生後,自己的注意力都轉移到二娃身上了,加之二娃和德龍長得幾乎一模一樣,看到二娃就好像看到德龍,日子雖然苦得要命,有三位堂嫂幫助,也不至於餓死,只是婆婆更辛苦了,四十多歲的人已經是滿頭白髮。她真佩服婆婆,一個喪夫喪子的女人還能夠活下來,這需要多大的勇氣。現在桂花明白了,死去的人一去不返,活下來的人只有好好活著,才對得起死去的人,自己不但要好好活著,而且要把兩個孩子養大,要看到她們娶妻生子,讓他們的孩子也叫自己一聲“奶奶”。
在某些時候,能讓人能活下來的不全是物質,而是生活下去的勇氣和希望,只要有希望,傳承才不會熄滅。
八月初的陽光,還是那麼的狠毒,桂花抱著孩子在屋後的刺槐下乘涼,不知什麼原因,今年的花期比往年向後推遲了一個多月才開始謝,也許是花神看到人間的饑餓,不忍心結束花期,再沒有東西吃,畢竟刺槐花還是可以充饑的。地上落滿了刺槐花,刺槐花是蝶形的,微風吹過,引得千朵萬朵刺槐花飄落,象千萬隻白色的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
桂花看著在懷中酣睡的二娃,臉上露出的是一種無與倫比的憐愛。
桂花看到河邊的芒柴、蘆竹和白殘花還是象去年一樣開花、飛絮、飄香。
德龍,你知道嗎?今年的芒柴開著和去年一樣的黃花,像一串串的小珍珠綴立在枝頭。你還記得嗎?你和我一塊把花枝剪下來,收集起來給媽媽做成掃地的撣子。你還記得嗎?我的手不小心被芒柴細長有鋸齒的葉子劃破,你心疼得用衣服幫我包著流血的指頭,看著我欲流淚的眼睛,你把芒柴叢中柴雀廢棄的鳥窩拿出來逗我,說我們變成一對柴雀到這個窩中生兒育女。你知道嗎?那天夜裡我真的夢見我們變成一對柴雀,生了好多個藍色的象珍珠一樣的蛋,孵出了好多小寶寶;
德龍,你知道嗎?今年的蘆竹還是像去年一樣的高大挺直,竹頂上花,被風刮起漫天飛舞。你還記得嗎?你把蘆竹砍下來,插在門口的地上,做成了兩排架子,說可以在上面曬東西。你還記得嗎?你說我們再生幾個娃娃,這個架子可以用來曬娃娃的尿布。你知道嗎?今年真的曬上尿布了,你曾經叫在我肚裡不要調皮的二娃已經出生了,他長得和你一模一樣,你高興嗎?
德龍,你知道嗎?今年的白殘花還是像去年一樣開滿了整個河畔,五個潔白的花瓣烘托著無數個向上的花柱頂著那些渴望著的黃色的蕊,它發出的香氣還是像去年一樣的令人陶醉。你還記得嗎?你叫我把這些潔白的花瓣收集起來,曬乾,塞在枕頭裡,每天夜裡都聞著那些誘人的香氣。你還記得嗎?在採花的時候,你跟我說注意不要讓它的堅硬的刺紮傷。采完了花,你問我有沒有紮傷手指,我說沒有。你知道嗎?其實我的手被紮了好多個眼,流出了血,把我采的那些花都染紅了,可是我沒有告訴你,一想到夜間我們共同枕在一隻散發出香氣的枕頭上,你知道我有多幸福嗎?
ns3.144.87.230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