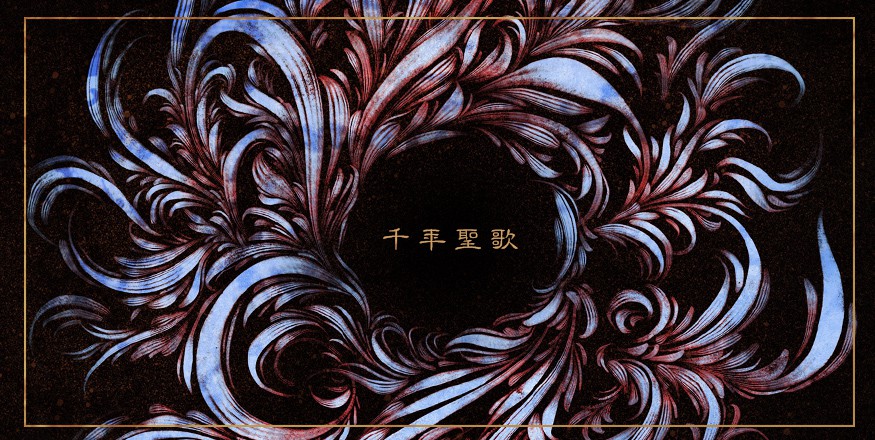-name-night.jpg) x
x
攝 by Wanda46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tTUJAzBdQJ
拉斐爾多希望自己夠了解安潔莉娜,才不會對安潔莉娜是受到詛咒而跳樓的謠言感到心神不寧。
這不是很明智的思考方式。他檢討著。
至少,他不該對區區一具自動人偶感到不適。那不過是紀念亡人的雕像,具有齒輪、會移動罷了。一種流行藝術。
流雲石為肌膚的材料,再疊上豐富的色彩,產生了一種奇異的錯覺。名為安潔莉娜自動人偶的那張臉在光芒下,不時搖曳一層淡淡礦物的光輝,宛如紅蝴蝶輕拍鱗翅,透出了微小的生命感。但當那襲精緻的黑色喪服,被達契亞粗暴地撕裂,雪白的身體被揉捏……
拉斐爾被嚇著了。那畫面太過猥褻,卻也充滿誘惑,尤其對像他這般從未見過此種場面的年輕男孩子而言。他尷尬地尋找可以安置視線的地方,一抬起眼眸,便對上自動人偶的雙眼。
從自動人偶無機的玻璃眼珠中,拉斐爾彷彿見到安潔莉娜從高塔墜地,但毫髮無傷地爬起,化為一具沒有靈魂的自動人偶。
詛咒、詛咒、詛咒……這個詞繚繞耳邊。安潔莉娜雙唇輕啟,也重述了這兩字。
拉斐爾從頭皮麻到腳。片段記憶閃現,他感受到惡魔再次把他抓到半空中,然後將他失去靈魂的身體摔到地上,讓他的靈魂面對倒在血泊中的自身軀體。
別恐慌!思考,用邏輯思考!拉斐爾在心裡吶喊。
一個人喜愛的作品會顯露他的本質。如果說達契亞極度欣賞安潔莉娜身上的某個美妙,然後他與安潔莉娜爭吵(拉斐爾有聽聞這幾天公爵和安潔莉娜小姐之間的關係變得冷淡),為了保護那個美妙不被徹底破壞,索性派人殺了她。把謀殺偽裝成自殺,好逃避罪刑。這種殘忍手段之於黑石公爵,不會令人感到絲毫意外。也或許,達契亞根本不愛安潔莉娜。他愛上的是一個幻覺。當那幻覺大於真實之際,他便毫不猶豫地摧毀真實。擁有安潔莉娜外表的自動人偶便是為這一刻準備。
達契亞快樂地大笑。現在這對達契亞是個遊戲吧,也或許是個檢驗,檢驗安潔莉娜人偶是否運作正常,保留著永恆美妙,成為專屬於達契亞的完美女人。沒有詛咒。這裡沒有詛咒。
可是那杯奶酒下肚後,拉斐爾的理智就鬆動了。這奶酒定然比他偶爾小酌的酒濃度還高,身子有點熱烘烘的。他感覺面前的紅髮人偶迸出不明黑暗氣息。他趕緊遠離現場,沒想到一回神便發現自己朝特洛伊走去。
每一次遇見特洛伊,拉斐爾心裡就升起一股難以言喻的感受,好似兩人之間有股玄祕的吸引力,能在對方身上找到彼此相似之處,縱然他不知道兩人之間有什麼共通點。但如果他靠近特洛伊,那股親近感便會消失不見,猶如一首和諧的交響曲被突如其來的尖銳鳴聲中斷,尤其特洛伊略帶沙啞的嗓音,宛若是樂曲中混合了沙子的沖刷聲,將整首曲子充斥著異樣感。
這個男人很危險。一個聲音警告道。
走到距離特洛伊五步之遙,拉斐爾聽到一陣耳語。他警覺起來,一時以為宴會裡混入了刺客,而有人在警告他。原本他想去找白隼。
「殿下,請坐。」一個男僕搬了張椅子過來。
拉斐爾謹慎瞥向對方。除了對上他的視線有些惶恐,男僕沒有顯現任何異狀。最主要的是,嗓音完全不一樣。剛剛是誰在和他說話?
「不用麻煩了。」拉斐爾揮手示意男僕退下。
這個人類被惡魔汙染了!帶走他的生命!
當拉斐爾的視線一回到特洛伊身上時,那孩童般澄淨的聲音再次響起,如水波般迴盪空間,同時直擊心底。眾人嘻笑飲酒如常,沒人聽到。拉斐爾渾身一震,明白那不是來自人類的聲音。
被……惡魔汙染?猶豫思忖間,拉斐爾與特洛伊之間再次產生了某種相斥,如同柔和的樂曲演奏被中止,不只如此,此刻就像是樂團中的提琴被大力砸碎,暴力的聲音刺著耳膜。
拉斐爾幾乎要摀住耳朵,轉身離去,卻一步也邁不開。他的身體與入侵腦海中的聲音共鳴,彷彿是他本人感到必須要──殺了特洛伊.布萊克伍德!
不可以!他對抗著莫名的想法,試圖專注在與特洛伊的對話上。
在這個人類打破伊絲女神的律法前,帶走他的生命。
那悠然的聲音愠怒起來。
紊亂的情緒流竄,拉斐爾藏在身後的左手緊緊握住右手,阻止自己拔出腰間的劍,刺入特洛伊的胸膛。他的手越握越緊,痛到可以感受到指骨在彼此摩擦,彷彿要碎裂。
我身為王子,可不能輕易就被煽動。忍耐。這不屬於我的感覺,定是又受到某生物的影響。控制情緒。拉斐爾告訴自己。他看向舞池,想轉移注意力,忽然可以在每個人心臟上看到一團光。他自然而然地理解那些是生命的光芒。他平時就能感受到周遭生命的能量,只是畫面變得具體。跳舞的人輕快踏步轉圈,人們心頭上的那團光芒,像極了不時拍翅的發光小鳥,隨著心跳閃爍。拉斐爾身上有一股力量越奔越急,幾乎要駕馭他。他有股強烈衝動,想呼喚那些光芒過來。他看向特洛伊,特洛伊心口上也有一團光,至少──
拉斐爾深呼吸一口氣。
我恨特洛伊嗎?拉斐爾問著自己,恨到想帶走他的生命嗎?
他打量著特洛伊漆黑的頭髮、細長的雙眼,或許具有東方人血統,不過他更覺得眼前只是一個富有野心的男子,而他身邊最不乏這種人。特洛伊或多或少展現著無禮高傲,但拉斐爾深知自己性格上的弱點,無論對方有多壞,他恐怕必須很努力才能憎恨一個人。從小到大,拉斐爾從未真正討厭過誰。心裡那股殺意過於鮮明,以致顯得荒謬突兀。
他終於築起心靈防禦,將所有聲音從腦海中趕了出去,奇異光點的畫面跟著消失。拉斐爾鬆一口氣,他的秘密能力連結上情緒激動的生物時,有時候會讓他覺得自己要不是自己了。
拉斐爾得以冷靜了一分鐘,繼續與特洛伊對談,同時難過地想特洛伊到底是對什麼生物做出了傷天害理的事情,讓那個生物非得置特洛伊於死地不可?可是「惡魔」、「伊絲女神的律法」?這幾個不合乎常理的關鍵字令他納悶,心裡又有一種說不上的感覺,使得脖子冒冷汗。他不禁盯著特洛伊。特洛伊正談論起和黑石公爵的合約云云,避重就輕的回答仍讓他覺得頗可疑……
──拉斐爾。
拉斐爾心中一凜,從沒有聲音能夠在他封閉心牆後,還能滲透進來。那孩子似的聲音輕輕柔柔,彷彿吹過牆縫的風,貼在耳畔嬌嗔。
你是誰?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拉斐爾驚訝回應道。
萬物不重視名字。從沒有生物叫過他的名,連跟他朝夕相處,最像人類的彗星也只稱呼他為拉,如悠揚啼鳴。他可以感受到那生物絕對不是個孩子。它非常強大,知曉無數事物,度過的歲月難以用人類壽命估量。
拉斐爾,來,來我們這兒,我們告訴你一切。
你要告訴我什麼?拉斐爾疑道,我又要如何找到你?
你只要答應就好。
好……本來拉斐爾並不想即刻回答,卻不由自主地回應了。
往後拉斐爾回想今晚,才領悟到不能隨興答應精靈的任何請求。許多傳說故事裡都有類似的警告。不過他實在不可能在第一時間點聯想到與他對話的對象會是誰。畢竟他正處在人工雕築的繁華城堡裡面,四周人聲鼎沸,燈火通明。
那聲「好」所代表的允諾,讓拉斐爾感覺自己的意識敞開了大門。風暴般的力量急速席捲進來。除了那句答應,其餘念頭在須臾間瓦解,消失不見了。
你是,精靈木?拉斐爾的問句猶如狂風中薄弱的鳥鳴聲,連自己都幾乎聽不見。他的心靈被提了起來,好似乘上了羽翼,那是一種很驚嘆的感覺,讓他忘了抗拒和恐懼。
接下來拉斐爾唯一的想法就是他必須前往里斯塔山。
「殿下,您要去哪?」
一個大聲呼喚讓拉斐爾回過神。他發現白隼攔在眼前,而自己不知何時已經走出宴會廳,來到城堡花園。
「我……」拉斐爾望著白隼。明明大可以編個外出藉口,可是他連稍加掩飾的精神都沒有剩下,於是赤裸裸地將心中想法說出來。「我要去里斯塔山。」
白隼皺起眉頭,「殿下,您是說現在嗎?」
拉斐爾的注意力像一片被風吹起的葉子,從白隼身上飄離,無意識地繼續往前走。
「王子殿下!」
拉斐爾再次停下腳步,剛剛好像有人在叫他?他轉過身。「白隼?」
「殿下,你還好嗎?」白隼犀利的目光掃視著他。
「我是有些困惑。」拉斐爾承認。
「已經要午夜,您應該是累了。請殿下先回房休息。」
拉斐爾點點頭,就要隨白隼前往客房時,高亢的鷹啼吸引了他的注意。
拉,來。
彗星這麼說道。
來。
花園裡的花草樹木也都在這麼說,四周所有的生命都在這麼說,數百萬生物的聲音交織成一首盛大的共鳴曲。於是拉斐爾只跟著白隼走幾步,便轉身走向城堡出口。
拉斐爾發覺去路再次被阻擋。白隼跑到他前面,輕拍他。
「殿下,你還好嗎?」白隼面孔離他很近,緊盯著他。「您的寢室不是這個方向。」
「不好意思,白隼,我必須去里斯塔山一趟。」拉斐爾訥訥地說。
「殿下,恕我冒昧詢問,為什麼您想去里斯塔山呢?」
「因為我必須去里斯塔山。」
白隼面色凝重。「殿下,您喝醉了嗎?」
「我不知道……我……得去里斯塔山。」
「殿下,您在胡言亂語了。失禮了。」白隼半舉著雙手,防止他再往前踏出一步。「請您往回走。我帶您回房。」
冷不防,天空上一道黑影急速落下,發出撕裂空氣的聲響。
白隼立刻做出反應。看向攻擊者是誰時,白隼已經退了兩步,將配劍出鞘。
劍刃發出一聲尖嘯,在空中劃出一道弧線,巨鷹歛起爪子,傾身閃過。
「畜牲!」白隼怒道。
拉斐爾無意傷害白隼,他的心思純粹只為前往里斯塔山,嚇唬擋路的人。他抬起手,呼喚彗星回來。彗星落到他的手上,手腕傳來刺痛時,拉斐爾才想起他沒有穿戴護套,無論彗星如何小心翼翼地不希望傷到他,利爪還是穿透了絲綢禮服外套,鉗入他的肌膚裡。
接下來,如同上次貓頭鷹利爪鉗住他,拉斐爾的感知突然擴張,那股痛,比親吻更加親密,比刀刺更加深刻。不過這次與他肌膚和鮮血接觸的不是陌生的動物,而是彗星。他不再只是與彗星共享著感覺,而是他們彼此的感官彷彿已被烈焰燒熔、結合。他可以清楚感受到吹拂過一根根羽毛的微風,並微妙地察覺到自己的氣息就在一旁吐納;他能從鷹的眼中看到自己,甚至比自己攬鏡自照時更為清晰。而彗星所聽到的──
來。
拉斐爾迷惑地睜大雙眼。那聲音既像是來自內心深處,也像是來自遙遠彼方,如同寂靜夜裡的鈴鐺輕響,聲音穿梭在兩個世界之間。
我們走吧。拉斐爾半闔上迷濛的雙眼,點點頭。他已經無法分辨是他正這麼想,還是彗星在和他說話,還是誰在他腦中說話。他不再是個人,也不是鷹,他們的思緒結合,變為一體。
「殿下,請您先讓彗星離開吧,您的手已經被鷹爪抓得流血了。」白隼冰域口音浮現,透出他的焦慮。他僅將劍刃朝下,沒收回刀鞘。「若殿下一定要前往里斯塔山,里斯塔山是危險之地,請給在下時間安排安全的上山路線。」
拉斐爾聽而不聞,他眼前的畫面早已失焦,白隼和一株巨樹的虛影疊加在一起,他似乎只要伸出手,就能搆到遙遠的彼方。
所以他便伸出了手。彗星揮起翅膀,朝白隼發出警告的尖銳鳴叫。
「彗星,離開!妳的主人需要休息。」隨著威嚇的聲音,森然利光映入拉斐爾的眼中,只見幽暗的樹影被白隼手中的劍劃開。
彗星飛了出去。拉斐爾記得這種感覺,鳥兒們是他的劍。
彗星飛到空中後一個迴旋便朝白隼直直俯衝,一雙利爪在黑石城堡的通霄燈火下顯得鮮明,極快極狠,就要朝白隼的臉欺下來。
白隼一劍揮向空中的黑色幻影。彗星掠過刀尖,迅猛地颳起一陣風壓並在空中轉向。這時大門突然被推開,一對嘻嘻哈哈的賓客從中走出,刺眼的光線從門後射來,這瞬間的變化驚嚇到了彗星。
雖然背對著敞開的大門,拉斐爾居然也能感受到白針般刺入彗星眼中的光線。他抬手遮眼,耳邊只聽見彗星狂亂地往白隼身上攻擊拍打。
當他睜開雙眼時,驚見半截鳥翼落到了地上。
彗星發出淒厲的叫聲,紛飛的黑羽在斜長的光芒照耀下宛若羽毛形狀的黑曜石,閃閃發光,而白隼手上的劍,滑落細小的紅色血珠。
拉斐爾同時出聲慘叫,右手臂一陣火燙。
彗星!但他被彗星排拒在外,像是心靈赫然被剝離出去,塞回原本狹窄的肉身中。拉斐爾瞬間清醒了,他就只是他,他不再是彗星,或者其他什麼。
不要感受我的痛苦。彗星鳴叫不已。拉,停止與我連結。
拉斐爾的右臂外套上迅速暈開一道深長血紅,被刀刃切到骨髓般的疼痛讓他下意識地按住傷口。
「殿下,趴下!」白隼朝他跑來。
轉眼間,他朝後倒下,白隼已經把他按到地上,身子完全被壓在白隼的身下。「……怎麼了?」突如其來的衝擊讓拉斐爾既震驚又困惑。
「恐怕有人暗中偷襲殿下。」白隼指著拉斐爾紅透的右手袖子。拉斐爾恍然地看著白隼已經拋掉配劍,轉而掏出手槍,掃描四周,大吼:「是誰?出來!」
四下只有越來越淒厲的鳥叫聲,如同鋒利的刀子劃過冰面,刺得他的心像被刀尖劃過般疼痛。
「白隼,放開我,彗星她……」拉斐爾焦急地要推開白隼,眼角隱隱泛出淚光,然而白隼輕易地壓制住他,只專注在任何出現在四周的動靜。「白隼.霍爾札特,我命令你放手!」
「王子受傷了,誰快去叫醫生!」忽然有人高喊,蓋過了拉斐爾嗚咽的怒吼。
騷動的聲響吸引了好奇的人們,大批人們從敞開的大門中湧出,如禿鷹般將他們圍成一圈。
「通通退下!」白隼對空鳴槍。「否則視為襲擊王子的嫌疑犯!」
槍聲讓人群驚慌地移動他們的腳步,但有兩三人一邊快步走,一邊竊竊私語,似乎認為白隼是在做一個挽救眼前醜態的演出。
熱燙的羞恥爬上拉斐爾的臉頰,他不敢想像在大庭廣眾之下,任何有損尊嚴的狼狽樣子傳到父親的耳中,父親會做何感想。就算他的地位能使人們在他面前不敢隨意造次,卻無法阻止人們在背後散播著他們對廣場發生事情的想像。
其他模糊的想法逐漸消退在腦海的角落,彗星的叫聲扯動著他的心。
大概是確認沒有問題了,白隼終於放開拉斐爾。
「抱歉,殿下,攻擊者恐怕藉機混在人群中離開了。請您先……」白隼擔憂地說。
拉斐爾沒有心思聽白隼的說詞。他翻身躍起,奔向彗星的所在地。
「不,彗星,彗星!」拉斐爾抱起在地上悲鳴的鷹。失去右翼的彗星痛苦地掙扎,胸前還有一道可怕的長傷口。彗星亂踢的利爪再次割破了他的華裳,又在他身上添上了幾道新傷,但他睜大的雙眼充滿著不可置信,對不停增加的割傷渾然未覺。
「殿下,」沒想到白隼居然抓住他,還強硬地將他拖起。「有人要對你不利,此地不宜久留。」
「你把彗星的翅膀砍斷了!」白隼的碰觸有如把拉斐爾電了一下。拉斐爾猛地抬頭望向白隼,大聲指責,「除了你,還有誰會傷害我們?」
「我能體諒殿下現在的心情。」白隼冷硬地說,像把他當作胡亂發脾氣的任性小孩。「但您身上的傷口並不是我造成的,刺客恐怕還在暗處伺機行動。請您先快去安全的地方吧。」
拉斐爾短促地吸了口氣,那口氣卻像是有根刺梗在喉嚨裡,他掙扎著控制自己的心情,於是又吸了一口氣,將先前那股氣嚥了下去。他眼睛泛起水霧,不過他眨了眨眼睛,不讓淚水流下。
「我自己會走。」拉斐爾的雙唇顫抖。「白隼將軍,前往里斯塔山是我與彗星共同的希望,不管你說什麼,明天一早我都會帶著彗星出發,請你用所剩無幾的時間作好上山的準備。」
白隼一時無言,面無表情地站了好一會,然後生硬地鞠躬:「遵命,殿下。」
「彗星,我在這裡,我會一直陪著妳。」拉斐爾摟著奄奄一息的鷹,竭力用自己鎮定的心安慰彗星。「我知道妳很痛,因為我也很痛。拜託,再撐一會,我們明天早上就去看精靈木。」他垂下了頭,用細如蚊呐的聲音低語。「我們一定會一起回到精靈木上的。」
拉斐爾閉上眼睛,他在彗星的心中看到一個畫面,是他變成鳥兒,與彗星在精靈木上磨擦依偎的畫面。彗星已經開始將所有的痛苦推開,只將心中充滿著他。
ns18.223.172.149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