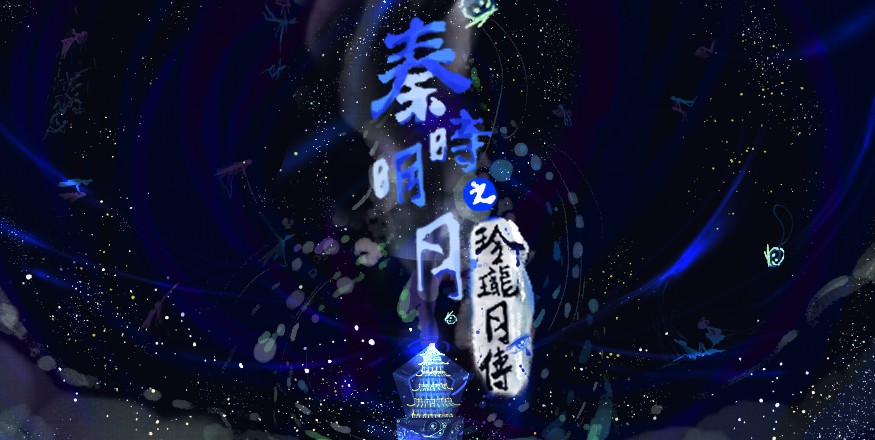水部樓堂下,弟子們寂靜無聲,專注在娥皇宣布的試煉結果上。面對眼前難以置信的結果,思緒猶如濁水爛泥難以攪開,娥皇嚴中帶柔的指示,到了耳邊也模糊不已難知其意。
半晌過去,我依然呆愣在角落,眼下有太多的不明白全都攪在了一起,細細數來,一為失去,二為失敗,三為失意。
“失去了前往咸陽宮的機會,失敗於簡單不已的試煉,失意在阿鈴的生死未明。”
「丟臉至極!」一聲尖銳的罵聲刺進了心坎,抬頭一看,那咧著嘴,眼帶嘲諷的綠衣女子,滿是不屑的斜眼瞪了過來。
「白…娦?」我呆愣道,目光依然出神的望著不遠處的沫泣。
「看看你的夥伴,看看那愛哭的女娃,在看看你,嘖!嘖!嘖!別人在幻境裡可是闖了七關,過了九難,而你?以你的實力,竟連區區一道驗心之試都能輕易落敗?!著實可笑!可笑至極!!!」
白娦的惡語再次不做修飾的凶狠襲來,突然間,她的罵聲停止,使得游離的思緒猛然回神。
只見白娦臉上露出陰暗的笑容,看著她細眼彎彎,嘴角上揚,一股不祥的預感油然而生,她回頭望向沫泣,當長老宣達完畢,她便速速上前將沫泣給拉了過來,娥皇看著白娦的舉動竟也不制止,一臉等著好戲的從容漫步,優雅地回到了堂中主坐上倚躺靜待。
「瓏弟子,你看我這不好心將沫泣妹妹給帶來了。」
「你心裡頭定當是有許多話想對她說吧!」白娦放開了沫泣,站到了我們二人的正前方,一臉蔑視的勾起了嘴角。
眼前的沫泣一身青衣染上了點點嫣紅,肌膚之上殘有著來不及清理的血污,看見她這模樣,方才盤據心裡的不甘瞬間消弭,我小心地伸出了手,輕握住了她的掌心。
「要是我能在快些進那黑門,你就不必受此苦難,不只如此,明明…明明是如此簡單的試煉,我卻始終未能下的了手,明明你在試煉中奮鬥拼命,而我卻失敗了。」我不敢直視眼前模樣虛弱的少女,一想到在幻境之中我屢屢失敗的同時,她卻是拚死闖過了一關又一關,對此心中開始譴責起了自己的無能,開始愧疚於渾身是傷的沫泣。
「哈?!…哈哈哈哈!」白娦尖銳的笑聲,打破了糾結的心牆,抬頭望去,她捧腹大笑不能自已。
「你…難怪!難怪你沒能通過試煉,沒想到陰陽家之中真出了個這麼個蠢笨的廢物!!!!」
「本以為能夠有幸目睹姊妹鬩牆的好戲,但…你這愚蠢的廢物…哈哈哈!你竟然從頭到尾都沒看清?你還真傻傻的以為,以為她是為了你?!」
「你…你說什麼?」
「沫泣女娃,你難道要我這局外之人來替你解釋解釋?」白娦戲謔的話語,沫泣陰沉的神情,無時無刻都在助長著內心蔓延的不安。
「前輩,方才我通過試煉後身子依感不適,因此我已稟報長老讓我先行離開,如此,沫泣告退。」
沫泣說罷,向娥皇行了禮後便頭也不回地往正門走去,望著離開的沫泣,腦中盤旋著白娦方才的惡語,心中焦急下便大喊道:「難不成你早就做好奮死拼搏的覺悟?你口中的試煉有成,長老青眼,竟比你自己的命還重要?!」急語出口後,肺腑立馬涼了半截,腦中閃過了陰陽家森嚴的規矩。
“陰陽家弟子,嚴禁擅傳未經宣達的指示。”
「瓏,你說什麼?」白娦率先出口質問,她收起諷笑的語氣,一臉嚴肅的冷眼看我。
「你的意思是這些都是沫泣告訴你的?」
「不是!」我強力否認,欲讓白娦的矛頭指向自己。
「你敢說出這話,代表你們兩個都有問題。」
「不!是我。」
「是你道聽胡說,又或者,你才是散佈這事的主謀?」白娦陰冷的目光變得更加犀利,她這是想讓我擔上更重的罪名?!可惡,好一個白娦!!!
「夠了。」突地,娥皇沉聲一喝,周遭交頭接耳的弟子,以及目露兇光的白娦皆安靜了下來。
「我是打算提拔通過幻境的弟子,順道帶其前往咸陽宮執行密令沒錯,但這些計畫都詳記於長老密卷之中,你非密令要員,竟私自散布未經宣達之事。」
「此罪可大可小,大則上達護法,小則幻刑嚴懲,這全權取決於你的目的,你是偷窺密卷呢?抑或憑空捏造呢?」
我沉默不語,握緊雙拳,兩拳依然止不住的顫抖,這是數月來我犯過的最大失誤,沒想到小心再小心,最後卻被自己心焦似火的急語給焚灼上了。
「不說話? 」
「罷了。」娥皇語氣一轉,細長的指尖居高臨下的直指著我,她一改柔和,肅穆的冷聲下令。
「瓏弟子聽令!」
「服下閉鎖丹,親自將罪卷送達辰極宮,等左護法大人歸來親自裁決。」
娥皇右手一揮,堂下弟子整齊劃一的讓出了一條狹窄的小路,眼下娥皇的意思便是讓我即刻前往,不得耽誤。
走在弟子讓出的窄道,四周無情的細語,鄙視的目光,一點一滴的蠶食著身心。小心觀望,沫泣不知何時離開了樓堂中,長老身旁的白娦無聲嗤笑。
沒想到頭一次讓弟子為我開路,竟就是親自領罰,而且還是在大庭廣眾之下,親送罪卷。
陰陽家的每位弟子都十分明白“罪卷”的意義,罪卷意同其名,本質就是帶有罪狀的卷文,而陰陽家的卷文與街邊文卷最大的差異,便是上頭施與的咒法,與尋常咒法不同,罪卷術法無形無質,不損肉體,卻傷心神。
舉一個最好的例子,不久前金部某位弟子因不明原因,被扣下盜賣婉人蠱的罪名,雲中君那噁心老怪因此大發雷霆,讓弟子提著三斤重的罪卷,跪罰於蘭荏堂前一個時辰,他為防弟子搗鬼,還用了割人利麻編成的粗線,將罪卷與弟子死死地捆在了一塊。
從那次以後,再也無人見過那名弟子,數日後,末閣之中也悄悄流開一段簡潔的口令。
“罪卷之下,生皆同死,罪卷之上,不死亦死。”
當初聽見這段流言,心頭悶了半天,一番細想,那弟子八成在罪卷脫手那刻就已失了神魂,非人非鬼。而他的下場不外乎就是被雲中君給抓去煉藥,亦或做成藥人也未可知,總之,那就是一個”死”字,肉身完好,心神潰散,真真是個非死亦死。
普通罪卷上頭無特別施法,一般由入門弟子遞送,如若某天哪位大人親自指示”親送罪卷”那此人定是離死期不遠了。
“至少現在的我就是如此。”
不同於雲中君那噁心老怪,半顆丹藥皆捨不得給弟子花用,娥皇倒是為了殺雞儆猴,把閉鎖丹這等封閉內功的奇丹給拿出來了。
眼下真不知是該哭還該笑,也許在未入幻境之前,娥皇早已藉著善上若水,稍微探著我的實力也不一定,否則何故還要特意鎖住我的內功,不就是為了防止我暗自抗衡她所下的術法。
眾目睽睽之下,我服下了閉鎖丹,頓時體內氣息窒礙難疏,還未反應過來,娥皇早已命人將顯眼的罪卷捧到了我的面前,伸手接過罪卷的那刻,意識彷如沉到海底,五感逐漸喪失,最後心頭一念閃過了沫泣的身影,星魂的話語。
“末閣裡頭的明爭暗鬥遠比你想得還要更加危險。”這麼一句不明就裡的話語,放到如今一語成讖,我依舊是蹚入了末閣之中最汙濁的爛泥,那深不見底的算計。
不知過了多久,意識有如漂泊在刺骨凍人的冰淵,一時的刺骨時不時便轉為炙熱的焚燒,就這樣來回往復,緩緩折磨著心神的每個角落。
縱使如此,這一路上我最不缺的便是”苦痛”二字,不論是當初刺心之痛,分離之苦,幻境之噬,哪個不是鑽心刻骨,如今只不過是腦子被凍了幾下,烤過幾回,又能奈我何?!
一番張揚壯膽後,內心開始奮力抵抗咒法,過了許久,受盡折磨的意識終於逐漸回復,視線緩緩清晰,忽地,眼前一道孰悉的身影無聲地映入了眼簾,她青色的衣擺在冷風之下隨意擺盪,身上乾涸的暗血也早已清理乾淨。
“沫泣?!”
張口叫喊,嘴角紋絲未動,此刻我才發現,雖然意識稍有恢復,但身子卻是不聽使喚,徑直往天極圜的方向緩步行去。
看來在意識全無的狀況之下,娥皇施於卷上的咒法早將身體給控制了,也難怪身旁毫無監管之人,有了咒法控制壓根兒還需要什麼人呢?
「瓏。」一聲淺薄的叫喚,語中盡是說不明白的情緒,她走到了我身旁,隨我慢步在空無一人的子屬樓廊中。
「為何你聽了白娦之語,卻依然將罪名攬在了自己身上?」
「傻,真傻……打從相遇開始你便是如此,直到現在落得這番田地你依舊不改。」
眼角餘光裡,沫泣堅強的目光退去,空留一段隱匿不解的失意,她低頭垂眸似在思量著什麼,片刻,她抬起了我的手臂,撥開上頭的衣料輕輕撫摸。
「她們果然沒那麼輕易放過你,你看看你這無瑕的肌膚上頭,添了多少黑紅的瘀傷,想來是他們趁著無人之時,暗自施術擊傷你的,畢竟現在的你毫無意識,無法反抗。」
「…………」一陣沉默過去,兩人的腳步聲迴盪在這空蕩的走廊,不遠處一道星夜似的紗幔垂落於地,看著此物便知,在沒走幾步就到天極圜了。
頓時,內心對沫泣的不言不語感到一陣酸楚,難道她在怨我試煉之中的無用?口無遮攔地差點連累她受罰?
一陣思慮糾結下,沫泣似笑似悲的話語打破了沉默。
「事到如今,我還在這做什麼呢?」沫泣眼角泛出了淚光,她語帶顫抖,輕輕地放開了我的手,我努力想眨眨眼睛回應她的話語,但眼皮卻如凍結般毫無反應。
「呵,沫泣啊沫泣,你自己竟開始動搖了?」沫泣喃喃自語,語中充滿了諷刺與悲笑。
「也是,若連失去意識的你都不敢坦白,那我又何故一直在此躊躇不前。」沫泣頓了一瞬,手中醞釀術法,不到片刻,一道淺淺幽芒不偏不倚的擊入了心頭,頓時緩慢的步伐驟然停下,焦惱的心緒也隨著停滯的步伐一併鎮定下來。
“是什麼事讓她不惜施術,也要將我攔在此處?不只如此,她還替我緩解了磨人的術法,但…但這要是被人發現,豈不就會與我一起背上罪名?!”
心中頓時為身旁的少女的行動胡惱了一番,一番氣惱後又轉為無底的擔憂,這樣不上不下毫無平息的心緒,可比什麼凍人術法,灼人咒訣,還要來的更加吃力。
「瓏,你知道我膽子小,這幾月下來的相處, 我本欲帶進墳頭,至死都不在憶起,這些事實,這些算計,我著實沒有臉面在跟你坦露半句。」沫泣突然加快腳步,略微走到了前頭,她孤身處在前方背對著我,即便不見面容,她那滿帶悲戚的語句,早已如夏夜驟雨般席捲而來。
「你知道嗎?你…你真的是位奇怪的女子,即便過往我孤身越過了無數黑暗,卻依然選擇在你身旁停了下來,不論是出自利益也好,算計也罷,有那麼剎那,我總會不自覺地被你的笑顏給影響,彷彿我們本就是如此,本就能一起互相相助走出末閣。」
「我甚至不解,為何當你出現後,心頭籠罩的陰霾會時不時透出點點微光,就好像…現在這般,我本就不會跟你說這些的,但我卻還是說了,為何?為何呢?」
頓時,沫泣自語自答,緩緩傾訴,每個字句間的感情皆一滴不露的流淌於心。
「當我們初見之時,你僅用半個時辰,便盡數破解了所有弟子耗費一月才能勉強完成的密卷事務。」
「從那刻開始,便是一切謊言的起點。」沫泣深吸了一口氣,壓著聲,冷道:「我騙了你替我分擔工作,你笑著接下;我騙了你替陰陽家弟子出頭,你哭著向我尋求安慰;我騙了你…我騙了你許多,許多,直到此次試煉,我依舊是負了你。」
「過往數不清的謊言慢慢累積,直到我真正了解了你,直到我能利用這份了解達到我的目的。」
「你定是到接下罪卷的最後一刻,還在自責自己的無力,還在為我著想,但那些...那些悲痛的背後,我卻依然冷漠地踩過過往被糟蹋的一切,踩著你那捨己為人的決心。」
「打從檢核開始,我便利用你的術法避過了長老的善上若水,接下來的水門試煉也同樣,那裡頭的危險我心知肚明,還有你的實力,你的心性,我亦瞭如指掌。」
「你的實力無疑是五靈玄同之首,其勢有如過往被抹去存在的五靈玄同”芙蓉”般,都是那麼強大耀眼,正因如此,我才會選擇九死一生的黑境,即便知曉這是一個危險的賭注,但我依舊是撐過來了。」
「我深知黑境之裡的敵人對你而言是遊刃有餘,而清氣逸散的照心之景就不同了,你從始至終不斷惋惜每道生命的逝去,即便你動了殺心,你的內心深處,依舊還深藏著相信他人的善意。」
「這也代表,你不可能通過試煉,你的失敗早在踏入大堂的那刻便已注定。」
「……」沫泣停頓一會,淡然說:「木已成舟,原本此事到此為止也就完了,但我卻還是小瞧了白娦,小瞧了你。」
「我沒料到她能看破我的意圖,試圖借你之手讓我深陷絕境,我更沒料到,你聽了白娦之語急語飛出的同時,卻依然袒護著我。」
「瓏,罪卷之上,不死亦死,即便無罪卷,長老將此罰送與左護法裁決的決定,早已斷了任何可能。」
「你知道陰陽家內從不允許妄談任何大人,但你不知在這妄論的背後,有一句短短的七字言,卻罕有的留了下來。」
「凜刃一祭無生情,動魂攝心左護法。」
「這許是我們彼此的最後一面,我…。」沫泣原本清冷的字句擱在了口中,片刻,她低落的話語陡然一轉,仿若冰雪消融,語中堅毅的決心破冰而出,展露無疑。
「我對不住你,但—我從未有過半分後悔,即使時光倒轉,我同樣會做出相同的選擇。」
「明日長老便會前往咸陽宮,到那時…期盼多年的心願終將實現。」
「最後,謝謝你,瓏,謝謝你在這末情之閣,末光之地,所帶來的一切不凡。」
「縱使無期,依然再會。」
周身術法隨著離去的身影一併消去,眼前倩影再也不是當初溫婉可憐的少女,一句再會,別了過往,別了故人,別了心底熟稔的那位泣容少女。
短短幾句隻言片語,道盡數月來的矯情作戲,剎那,心窩裂了一道縫,縫中逐漸流失的是強撐死扛的理智,心頭混亂無止,意識再次迷失。
恍惚間,夜風刺骨的刮過了肌膚,天極圜外廊之側,一望無際的星辰,一輪孤寂的望月,伴著沉重緩慢的腳步聲,一步,兩步,終是回到了星海之頭,沉寂之星,陰陽之極。
剎那,膝蓋唰地落地,一聲沉悶的撞擊伴隨著裂骨的疼痛刺進了腦門,粗魯地喚醒了不知所措的自己,一剎的呆愣,一瞬的清醒,體內不斷壓抑的內力,終於隨著失控的情感發狂迸出,須臾,手中高捧的罪卷頓時化作青煙消弭而去。
「為何,為何不告訴我實情,為何…?」朱淚奔騰,無所停止,顫抖地啜泣,抽疼的身軀,絞痛的五臟,為了三月以來的虛假,為了三月以來的信任。
“原來試煉之前,水門之別,你那一反常態的神情舉動就源自於此,為了…為了你那長久期盼的心願?。”
如果…如果你實情相告,我們是否就能併肩到最後,直到現在,我依然無法相信那個黑眸含淚的沫泣,從始至終都只是作戲。
淚水模糊了視線,模糊了聲音,辰極宮模糊不已的青銅大門映入眼簾,隨著那無言的傀儡孤立於此。
半個時辰過去,我依然跪立在此,明明罪卷早已被暴走的內力盡數破壞,身體卻依然不聽使喚,一步也未能挪移。
背叛之情夾帶著太多道不出秘密,當沫泣坦白的那刻,一瞬的憤怒掃過心海,隨之而來的便是無盡的悲鳴,比起怒火與怨懟,悲傷才是永遠存留心底的印記。
不知出神了多久,心頭的風雨隨著逐漸遞減的溫度回歸平靜,一時思量,一時淚雨,腦中捋過了三月以來的回憶細絲。
是啊,我又何嘗不知呢?三月過去,能夠通得心神的自己,心底比誰都明白陰陽家的規矩處世,但…為何我總是不願承認,不願面對那些美好的背後,是用多少磨難換來的。
“徹骨絕情,心無凡思,究竟非同戲語,縱使心中有數,我依然相信當初在大堂之上,她那聲顫抖的”對不住”,那瞬間黯淡的黑眸,便是她內心深藏的真心,即便…即便,信了會傷痕累累,我依然不能放棄,那怕一絲渺茫,我也不能放棄!”
霎時,心中暗想一一串連,一陣奇光照亮腦海,恍然大悟。
“期盼…已久的心願?沫泣口中的心願,使得她捨棄了太多東西,不管那心願值不值得,對她來說已是無上瑰寶,無法放手。”
暗自思量,世上諸多背叛,諸多苦難,哪個不是為了心中最深切,最無法割捨的執念而生?不管是內門弟子,娥皇,沫泣,一輪數過,眾人皆有自己的苦楚,皆有自己手染黑血的理由。
“人心…似水,變化無常,人心似水,澄澈通透,黑如玄墨。”
一陣感悟,內息忽地攪動,就如同知曉了某種天地至理,心中暗自浮出了通心控意的驅使之道,就如同直覺般,輕輕抬手,掌中一道又一道翻湧的清氣恣意游離。
「……」沉澱了半刻,心中的平靜並未持續太久,不到一會,心緒再次低迷,盪到了心情的谷底。
「道理我都懂…但,但一身情根怎可能說斷就斷。」於戲大嘆,身子直接倒在了辰極宮門口,伸手開展,兩腳大開,一副猖狂無禮的躺再了辰極宮門外。
「沫泣…你才傻…傻子,你個大傻子!!!!」語氣再次發顫,我將雙臂擋在眼前,放肆的在刺骨的琉璃地上哀號大喊。
「你要是一開始告訴我,我定會竭盡全力助你的!還說了解我?!放妳個狗屁啦!!你要是了解我,你便不會欺瞞我到現在,你要是了解我,你便會選擇相信,而不是把我蒙在鼓裡!!!到了最後你也不會把自己搞得傷痕累累!!!!」
「你這傻瓜!傻子!!大傻人!!!大蠢貨!!!!」
「蠢貨。」一聲孰悉的沉穩迸出,腦袋未做他想便一語接下。
「對!!!!蠢貨!!!!她就是個大蠢貨,傻子,大傻子!!!!」
「沒錯,就是蠢……….。」剎那,方才邪魅陰柔的聲音,終於貫穿了腦門,直直地戳入了心坎。
「啊啊啊啊 ?!!!!!!!」身子飛地彈起,雙目瞪大,映入眼簾的是空無一人的走廊,見此情景,我緊按胸口,帶著些微的驚詫與失落低下了頭,呼了一口大氣。
「幻,幻聽?難不成是方才罪卷術法的影響,害我…我還以為那冰塊…星….。」
話未止,一個白皙纖長的指頭趁我未注意之時,輕輕彈落在了額間,隨之而來的便是我的驚聲一喊,向後倒退。
「怎…怎麼…?!」一個往後彈飛,背部死死的貼在了辰極宮冰冷又堅硬的青銅大門上。
「星……星…星魂?!!!!」
驚詫一喊,眼前少年眉眼間露出了些許疲憊,他纖長的睫毛掃去了沾染其上的塵埃,臉上邪魅攝人的紫焰,被他額前稍有凌亂的秀髮輕輕遮擋,這般不同以往略沾風塵的模樣,頓時為他俊美的容顏,在添上了幾分不同凡響的魅意。
只見他身披靛色斗篷,布料上那繡工精細的天斗圖樣栩栩如生,一縷細長繡金的暗色掛帶,在他的胸口繞了個完美又優雅的小結,他輕輕抬手,從容不迫的拍去了肩上的沙塵。
三月未見,他一邊愜意打理衣容,一邊用他那深沉的藍眸緊緊的凝視著我,彷彿要將我的心頭看穿一般,使得心跳驟然加快。
我貼在門前一語不發,誰都沒能料想到他竟會在此時回來,腦中無不是方才放肆的大字形躺在地的模樣,這樣羞恥丟臉的情感轟地攪亂了思路,以至於眼下的我目瞪口呆,模樣矬矬的擋在門前。
「傻子。」突然間,一聲沉穩的”傻子”,伴隨著敞開的大門,使得身子就要往後摔跌在地。
剎那,眼前少年右手輕抬,食指微勾,一股孰悉的雄厚內力包覆身軀,眨眼間,他用內力輕輕一拉,我便一聲不吭地跌進了他溫熱的懷中。
眼下一尺不到的距離,足夠讓許多細微之事竄入心底,他身上若有若無的夜風涼息,伴著高雅清淡的香氣沒入鼻息。
“ 嗯?這舒鼻的清香,這香草味道….。”一寸思量,過去醫庄學得的百種草藥掠過腦海。
“芍藥?!芍藥之香!”
正當思緒沉浸在他身上散出的芍藥清香,星魂輕哼一聲,壓聲道:「看來這三月以來,不變的只有你那呆傻地樣子,我都提醒三聲”門” ”開” “了“。」聽見這話,我趕緊掙脫他的懷中立正站好。
眼下我略微皺眉,雙脣緊抿,吞了吞口水,有些不敢置信地望著他,這番瞎搞下,心中開始不解這般窘境。
“怎麼每次見著星魂都這般丟臉?怎麼每次到了他跟前,我都像個傻子似的?還有他之前身無藥草清香,怎麼如今突然染有香氣了?”
當我還在門旁糾結苦思,星魂早已繞過了我,默默的踏入了辰極宮,回過神來,望著他有些嬌小的背影,背影中那挺拔又不失優雅的淡然,無聲地攪動了心海。
“他…真的是他,他真的回來了?”心神忽地放空,我狠狠掐了自己的臉頰,臉上炙熱發疼的觸感,默默地證明了這令人又驚又喜的事實。
也就是此刻,心中恍然領悟,明明方才心頭悶的跟塊石頭似的,如今一見著他,內心無盡無頭的陰霾竟一掃而空,就好像…好像只要看著他,世界便會再次灑上華光,綴上星點,一切不安將盡數消埋在他熟稔的氣息,靜謐的藍眸之中。
此刻我心懷忐忑的踏步而入,數月過去,終於再次踏進這寬敞華貴的辰極宮中,漫步走去,膝蓋忽地刺痛,腳步不自覺慢了些,我輕拉淡色長裙,試著掩蓋膝蓋受傷之實,整理好衣裙抬頭一望,星魂早已悄無聲息的站在了我的面前。
「誰幹的?」星魂冷聲道,眼中靛藍兌上了幾寸鋒芒。
「長裙都拖地了,這…這樣也能看的出來?難不成他偷使讀心術?」我低頭看著拖地的長裙小聲咕噥,星魂似是聽見般,抬指往我低垂的額頭稍加施力,硬是讓低垂的視線對上了他那暗藏怒意的藍眸。
「唉…這,這…說來話長。」一聲嘆息,只好把今日之事毫無遺漏的傾吐而出。
ns 15.158.61.20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