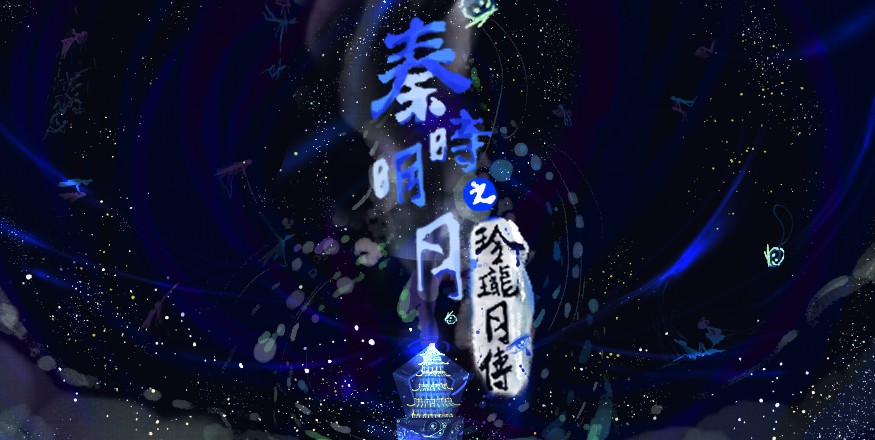偌大的廂房內,衛婀公主從頭到尾只是在一旁安靜看著,絲毫未有想從座位上起身之意。
我看著不遠處優雅端坐的衛婀,心中不免聯想到了方才的傀儡戲,身處戰國時代的各大勢力,確認彼此利益與鞏固權力的最好方式的"結親"當是不二良選。
"還真真是肥水不落外人田。"
「羅兒,如果那衛婀真的相重你,你對她又有何想法?」我不安問道,雖說結親有結親的好,但卻不知甘羅心中真正的想法為何,到底是利益為重,抑或本心為主,而甘羅她又會喜歡初見的衛婀嗎?
「若換作瓏兒,你又有何想法?」甘羅毫不猶豫地像我反問道,藍眸似乎暗了幾分。
「衛婀公主,遠看窈窕淑女,近看清雅端莊。論家世、容貌、才學,身為公主的她皆無可挑剔。若我是你,便是如天道自然,隨情而動,眼下我既未動情,自然是婉言推卻。」
「總之,我覺得彼此要郎有情妾有意才是個理。」
「呵,是啊,可在這戰國亂世,又有多少情能夠隨心,又有多少人能忽略背後夾藏的利益,唯珍惜眼前人物。」甘羅冷笑一聲,語氣藏著無奈與不滿。
「此次,呂相大人雖有意從中牽線,但衛婀公主卻是親自赴會,恐怕這位公主與呂相大人的意思有所相左。否則,結親這等大事,早就先知會爹與娘了。不管如何,不論入眼與否,以甘家的地位與權勢來看,若此次結親真有結果,那也都算是甘家高攀了。」
「撇除這些不談,你自己對衛婀就未有其他想法?」我有些意外的望著甘羅,畢竟那位端莊的公主也算是難得一見的美人,我本以為羅兒小小年紀,會傾心於公主的氣質與容貌。
「大家同為戰國亂世上的傀儡,都受執掌傀儡的利益大局操弄,既然彼此都知曉這只不過是逢場作戲,又談何傾心?」
「不是,我想說,想說人家好歹是一國公主,難得的美人,不都說世間男子愛美人,更何況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退一萬步來說,動心這種感覺只道是情不知所起,即便明裡暗裡有利益糾葛,哪時動了心還真是無人可知。」
「聽你說的頭頭是道,好似你曾動過心似的。」甘羅瞇起眼,嘴角勾起壞笑,一臉就是我毫無經驗還在那胡說的嘴臉。
「少,少轉移話題,你就老實說嘛,美人入眼,你當真都未有動心?」
「哼,你自個都說世間男子愛美人,可此時此刻,羅兒我只是位總角孩童啊!」
「更何況,公主面紗遮面,唯見雙目,你又知曉面紗之下是何等顏色。」甘羅一臉無辜的淺淺一笑,狡猾地迴避了我的問題。
「嘖,就你理多。」
半晌過去,我依舊不氣餒的與甘羅纏辯,最後卻還是敗給他凌厲的口舌,也不知是他年歲太小,又或者是只為家國而心無旁騖,談到男女之情,就如冰塊一般冷冰冰的,毫無熱情。
「美人面前像個冰塊,我看我不喚你羅兒,改喚你冰塊好啦!」
「唉,這就是阿鈴說的情竇未開,對,你就是情竇未開的傻冰塊!」忽地,當我出口打趣甘羅之際,腦中嗡鳴不止,對於過往的記憶又清晰了幾分。
「阿鈴,他是何人?」
「莫非你又想起什麼了?!」甘羅急切地朝我問道,我卻難以維持意識回答他。
此刻我雖漸漸地想起了陰陽家的一切,卻唯獨有一人,唯獨陰陽家左護法的印象,彷彿受一層迷霧蒙蓋,難以窺得真相。
忽地,甘羅突然收斂神態,朝我示意前方有人過來後,便假裝看向數十尺外的傀儡戲偶,獨自自語評論。
「敢問先生便是甘家神童,文信侯大人府下年紀最小的門客,甘羅先生?」
只見一位臉帶白紗的女子優雅地朝甘羅走來。她聲音甜美,嬌柔動聽,一眼看去身形高挑,與方才那位身著翡翠色深衣,衣上繡有蕸葉的公子無的身高相差無幾。
眼前女子雖身型高挑,整身散發的氣質卻是嬌美可憐,令人憐惜。
她一雙靈目含光的褐眸藏著笑意,令人難以從她柔媚的眉眼中挪開。這樣乍看之下,竟是比遠處的衛婀在多上了幾分顏色。
「奴婢是公主的婢女小蓉,不知今日公主安排的傀儡戲曲,能否入的了先生的眼。」
「此次戲曲蘊含深意,令甘羅受益良多,公主有心了。」
眼前名叫小蓉的女子不羞不怕,言行舉止間有禮親人,她本與甘羅閒談近日瑣事,結果甘羅只是客套幾句後便打算離開。
也不知怎地,小蓉似乎見甘羅有意離開,話鋒一轉,忽然談起了大秦,談起了諸侯列國。
如此,原本左腳剛踏出的甘羅,在不知不覺間留再了原地,半個時辰過去,小蓉與甘羅聊的熱絡,我在旁邊看了都不禁懷疑,到底是小蓉能言會道亦或是甘羅有意與其深聊。
在此期間,他們二人不是淺談大秦現況,便是聊及呂不偉近日的決策,可當我越認真聽他們談話,心裡頭越覺得奇怪的很。
細想之下,一位公主的婢女懂得大秦朝堂局勢,還對呂不偉近期的決策頗有興致,這怎麼想都不合常理。
我趁著他們聊的熱絡之際,開始偷偷地對此她上下打量起來。看她雖身著尋常的婢女服,可唯獨臉上的那抹白紗材質不凡。
在心中抱持著這個想法下,我立馬湊近觀察,不看還好,一看竟發現在白紗上頭繡有一片不顯眼的銀絲蕸葉,蕸葉繡工之精緻,華貴的不似女僕所能穿戴之物。
而且上頭紋路精緻,布線華美,竟與那位衛國王族,衛無公子衣上的繡角如出一轍。
赫然察覺此事的我,立即朝身邊的甘羅提醒道:「羅兒,此女的真實身分恐怕非是婢女。」
眨眼間,小蓉突然手腳迅急地,朝甘羅掌中塞下一方繡帕,她的身手快速到甘羅還未反應,帕子便已到了他白皙的掌中。
我擔憂的看著甘羅打開帕子,深怕帕子上有何不妥。結果當帕子打開,上頭只是繡了幾朵芍藥,並無藏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甘羅見此眉頭皺起,藍眸朝我這裡飄了一眼,便將左手負於背後,悄悄地在背後寫字。
"你也發現了?"
「這是自然,她高雅的談吐與舉止有別於尋常女子,更別說她方才同你討論的大秦局勢,也不似一般婢女能擁有的見地。」
"不錯,當真是與我想到一快去了,看來昔日的笨鬼跟了我數年還是有所長進的。"
「哼哼,你少臭美,我看到的可不只有這些。」
「你且仔細看看她那輕薄的白紗,上頭繡有的銀絲蕸葉,是否與公子無衣著上的蕸葉紋路神似。」剎那,我等到的不是甘羅回復,而是小蓉甜美笑聲。
「先生為人不只溫和有禮,人亦見多識廣,著實令小蓉敬佩萬分。不如,先生直接喚我小蓉,總比左一句姑娘,右一句姑娘來的親近些。」
小蓉褐眼瞇起,像極了兩輪美麗的灣月,看著小蓉眉眼開朗的模樣,心中不知為何又是一總難以言喻的酸楚與悶疼。
一剎的恍神,心中突然萌生冷意,若是在尋常人眼裡,她的舉動不只自然,甚至還會讓人覺得親近許多。
但是,此刻心中卻是替眼前嬌美的女子的舉動,感到一絲不安。好似下一刻,她這般親近的背後還藏著某種不懷好意。
甘羅在小蓉語畢後,眉角微抽,藍眸裡閃過了一絲焦急,下一刻,他有朝小蓉拱手,說:「姑娘,莫忘了你的帕巾。」甘羅語畢,小心的將帕子遞還給面前的婢女小蓉。
在甘羅遞出帕子的剎那,從方才到現在的不安忽然爆發,只見小蓉的褐眼在一瞬染上了冷意,從她周身散發出的氣息,詭譎的令人在熟悉不過。
"這是……讀心術?!"
陰陽家上乘控心咒,動魂攝心—讀心術。
「羅兒,快從她身旁離開!」我下意識地衝上前擋在甘羅的面前並朝他大喊,甘羅一楞,人才剛退後,便被突如其來的一聲柔語給打斷了。
「小蓉莫惱,對付利嘴小兒而驅使讀心術,未免浪費力氣。」
只看那公子無從容地從數尺外漫步而來,他朝著身前的小蓉輕聲的安撫,褐眼朝我們一掃,便如同春日染上了寒霜在無溫煦。
小蓉看了一眼身後的公子無,原本親人嬌美的氣質消失無蹤,隨之而來的冰冷貴氣展露無遺。
「也罷,淺薄的試探就到此為止,這傭人的粗衫衣履我也穿煩了。既然婢女與神童踰矩私訂的好戲落空,也就沒什麼好藏掖的。」
「甘羅,甘家末子。看你方才迴避話題,不敢直呼我小蓉的模樣,是早已猜到我的真實身分?」小蓉收起眉眼上的笑意,言談間多了一種高傲的貴氣。
「聰慧的小神童,我便開門見山地說了,我,便是你們口中的衛國公主,同時,也是今日會回絕文信侯結親提議的衛婀。」
這公主扮婢女的戲碼,當真算的上是今日的頭等大戲了,我在旁緊牽著甘羅的手,不免能察覺甘羅故作鎮定的神情下,藏著多少的緊張與急躁。
沒想到衛婀就是小蓉,更沒想到這一開口,就如同甘羅不久前猜到的結果一般。
"衛婀從頭到尾,都未有想與甘家結親之意。"
「多日前總聽文信侯提起你行事穩重細膩,滿腹經綸,是世間罕有的少年天才,可平心而論,你雖聰慧過人卻不會武,全身上下不見一絲內力,也未有修習外功的體魄。」
「你一人無以一敵十,能夠護己亦護他人之力。恐怕你不曉得,身處亂世,光憑一張巧嘴是走不長久的,即便你能言善辯,也敵不過刀子一劈,箭矢暗射,我說的可對?」
「呵,彼此都是聰明人就不繞彎子了,今日聚會結束,我會先行回絕文信侯的提議,若等日後你真有了一番功績,到時再議結親之事也不遲。」
甘羅靜默不語,兩顆藍珠子隨著衛婀犀利的評論漸漸冷了下來,我見甘羅一副不快的模樣,心裡不禁覺得萬般的不甘。
衛婀說的沒錯,縱使她言語犀利,卻喚起了過去陰陽家的末閣中,爭強鄙弱記憶。
"強者為尊,弱者為芥。"
「命也,運也,文信侯此次操之過急,樹大招風也不怕落人口舌,一盤好棋全盤具倒。」衛婀柔聲不滿地說著,抬指一勾,甘羅手頭上的帕子直接飛到了三人中間。
衛婀不屑地瞥了一眼帕巾,帕巾的周遭頓時蒙上冰霜,不到半刻,帕巾化成冰片,衛婀食指輕輕往上觸點,冰片立刻破碎成了點點冰華,漸漸的消散於四周。
甘羅見到這番奇景,臉上閃過了一絲驚詫後,依舊沉著的冷眼沉默。
「姐姐,在他面前談論此事是否……。」公子無小心問道,語氣裡的溫柔與恭敬,當真是與方才陰陽怪氣的模樣判若兩人。
「無妨,文信侯看中的人,當是有腦袋能管好自己的嘴,不過,月神大人近日對此事異常關注,也不知大人背後有何深意。」
只看那公子姐弟二人細聲私語,倒是被一旁的我與甘羅聽的一清二楚。
「羅兒,若我沒猜錯,他們二人乃陰陽家弟子,方才那衛國公主使出的陰陽術……。」話還未說完,意識又再次模糊,甘羅見我情況不對,直接與衛婀二人拱手示意,應答幾句後便打算速速離開。
忽地,衛婀一聲輕慢的淺笑,把正要離開的甘羅給叫停下來。我背對著甘羅看向衛婀,在她的褐眼中我看到了毫無保留的輕蔑。
「看來就算是博覽群書的神童,也不過是個不解風情的木腦小兒。」
木……木腦小兒?
聽了衛婀的驚人之語,我連忙看向甘羅,只見甘羅藍眸驚顫了一瞬,有些不可置信這罵人之語是出自眼前嬌美的公主之口。
沒想到除了我之外,竟還有人能當著甘羅的面前罵他,更還況還是罵他"木腦小兒"。
「天底下尋常男子受美人贈以芍藥,無非心驚悅目,而你這木腦袋不只是皺眉,還面若玄冰的將佳人的心意給退回,看在文信侯的面子上,今日我若不提點提點你,怕是小神童日後又會惹得哪位玉貌花顏笑話。」
甘羅聞言,原本冷冷地藍眸露出精光,他嘴角勾起,道:「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甘羅方才未明"刻意喬扮成婢女的公主"之意,讓公主笑話了。」甘羅說罷,又是有禮拱手匆匆離開此處,欲前去與甘櫟會合。
行走途中,我一想到衛婀最後一臉鄙夷的對著甘羅的不解風情之舉,硬是罵出個木頭腦袋後再細細開解,便使我不由得也想調侃甘羅幾分。
「嘻嘻,那衛婀公主以芍藥帕巾相贈,卻沒想到遇上了你這冰塊,想不到神童羅兒見識廣大,卻唯獨沒料到芍藥表心,心誼之情,男女之定。」
「你可無恙?」甘羅聽到我的調侃後,停了下來,卻是先關心起我的狀況。
「無事,只不過好似又想起了什麼。」我從容應答,卻不想甘羅見我無事後,竟是怒哼一聲,不滿地將我剛剛的調侃給駁斥回去。
「笑話,你方才說心誼之情?心誼之情我沒瞧見,倒是瞧見蛇蠍情意。若我再跟那衛婀談上幾句,恐怕她一句定情怕巾,再一語假意暱稱,便要憑空生出多少閒言碎語,如此一來,搭上我也就罷了,若搭上甘家名譽,到時候不就成了他們酒水相會的一個笑柄。」
「不過區區芍藥,我怎可能不曉得背後含意,既然她有意構陷於我,我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呵,難怪她方才起頭便是婢女與神童的踰矩之行,原來如此。」
「哼,走吧,這"好消息"足夠讓叔父,大—吃—一—驚了。」甘羅一聲冷哼,邁出不快的步伐向甘櫟走去。
「是,是,是。」我隨口回應,將兩手搭在甘羅的肩上,就這麼悠哉了一路。
10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OfJOBzRXPa
傍晚時刻,今日千言閭之行有驚無險地落幕,衛婀等人巧妙的避過了呂不偉特意提出的結親,也讓甘羅默默地鬆了一口氣。
回程的路上,甘櫟難得一臉沉悶,兩顆眼珠子死死的盯著面前的甘羅。
「這其中一定有詐,我們的玉奴才貌雙全,怎麼偏偏就失了公主青眼! 」
「這衛婀公主哪裡不好,怎麼就唯獨眼睛不好使! 」甘櫟忿忿道,看起來對於今日衛婀興致缺缺的有意回絕,非常不能接受。
「叔父,您別鬧了,論地位、金銀、權勢,甘家若能與其結親那才真是有詐。」
「大人做事從來是有跡可循,此次結親不只是大人對你寄予厚望,也是為了能助長甘家權勢,大人什麼不好,就是慧眼獨具,待價而沽,既然今日衛婀公主不相信大人的眼光,那便他的損失。」
「叔父的意思,莫非呂相大人除了向大王推舉我出使趙國外,還有其他打算? 」
我看著甘櫟眼睛一亮,眸中閃爍著精光,即便甘櫟不如甘羅悟性極高,少年神童,他卻也是伴隨著呂不偉數十載的老狐狸。
「玉奴,甘家上下一族的興榮就靠你了。」
甘櫟淺淺一笑後,便將話題給轉往別處去了,不論甘羅怎麼從旁敲擊竟也未能在從他口中套出半點玄機。
過沒多久,馬車回到了甘家,甘櫟又丟下一句要去千言閭尋芳,便又匆匆別了甘羅。
「難得你叔父走的如此匆忙,平常不都要跟你一笑二鬧三團抱才走的嗎? 」
「呵,你沒聽見嗎?叔父說要去千言閭尋芳,估計又是他那套老話。」甘羅望著奔向千言閭的馬車漸行漸遠,直到消失在街道的盡頭,才轉身踏入院內。
「什麼老話?」我狐疑問道,尋芳這事莫不是指紅顏知己吧?!
「夜幕下的千言閭,是男人枕上的溫情,掌中的紅印,月下的昏醒。」甘羅一臉無趣的說著,對這事是稀鬆平常的很。
「哼,不過就是與女子唱曲彈琴無趣的很,還有他小酌溫酒也能昏睡不醒,到底是叔父上了年紀。」
「我平日聽你與甘櫟閒談,怎就沒聽過這話?!」內心驚嚇間,不免想到甘羅這孩子,聰明是真聰明,但是他當真明白甘櫟字裡行間的意思嗎?
「誰讓你這隻鬼聽人說話總聽一半。」甘羅朝我這做了個鬼臉,直接晃進了臥房。
「還不都是某人平常老說些無趣的。」我埋怨的咕噥幾句,坐在了甘羅的床旁,看著他換下今日出行的華服。
甘羅褪下華服,他白皙的肌膚襯搭精瘦的身子,在月光的照射下,小小人兒宛如皎玉。
片刻,他疲憊的將華服整齊收好,換上了寢衣,身子放鬆一躺,直接躺在了床上。
「喂,羅兒。」我側身躺在甘羅的身旁,一想到今日千言閭甘羅對於男女之情的看法,心中不免也好奇,這小神童若真喜歡他人,那又是何種情景。
只見甘羅睡眼惺忪的將頭轉了過來,慵懶的沙啞道:「嗯?」
「如果,我是說如果,日後你真遇上一位心儀的女子,你會如何?」我挪了身子,在往甘羅身旁靠近了些,想從他深邃的藍眸中捕捉任何情緒。
只看他的眼眸悄悄的垂了下來,細聲呢喃:「古往今來,男女之間本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何來心動?」
「你別跟我扯世俗規章,我就只是好奇天賦異稟的小神童,眼光如星星一樣懸在天上,天底下的花呀人呀微小如蚍蜉,就沒你入的了眼的。」這次甘羅聽到我的諷刺,意外的沒有立馬回嘴,反而思慮了良久才認真回答。
「我不喜歡像你一樣怪傻的。」甘羅壓聲答,藍眼珠裡是傷人的真誠。
“......”
「真—是—謝—謝—你—的—形—容—羅! 」我悶聲回應,心中開始暗自後悔開啟這個話題,竟沒想到在他身旁跟了四年,得到的竟是他關於我傻氣的認可。
「既然結親是因利益比較所生,那人當然是優先挑選能夠助己的良配。」
「我想我們是雞同鴨講。」我尷尬微笑,知曉這些話會直接投應在甘羅的腦海,於是我努力的將尷尬二字,誠心的由口詮釋而出,讓他好好體會他到底在說些什麼。
我談一剎的情意,他說一世的互利,當真是雞同鴨講。
甘羅似乎感覺到我的不悅,他頓了頓,再說: 「我現在雖不懂何謂男女之情,但,倘若可以,我希望與我偕手之人與你同樣。」
「哈哈,真是好笑喔。與我一樣傻笨,你這是自打嘴巴? 」我不屑的冷嘲,開始做好了唇槍舌戰的準備。
「如果她能同你一樣,那笨也無妨,傻也無妨。」剎那,我蓄勢待發的等來的不是甘羅的回嘴,而是他沉穩又堅定的輕語。
他眉眼微垂地沾染了惺忪的睡意,棕黑色的髮絲輕柔的散在他的額間,如此毫無防備惹人愛的他,此刻出口的話語,卻比任何刀槍箭矢都要來鋒利,鋒利的將我所有的不滿割裂得破碎無比。
我不由自住的被他此刻平靜又澄澈的湛藍眼眸給深深吸引,好似他深遠又純粹的靈魂與我互相共鳴一般,令人陷入其中難分你我。
「你可還記得這數月以來,前來甘家細賞傀儡戲的名士貴客,儘管是和顏悅色,厚禮相待,也無非是想從我身上覓得能相助於他們的價值。人若無名,不缺蔑視輕看之人,反之,人若有名,亦不缺投機取巧之人。世人趨利乃是情理,正是因為這情理,人與人的關係便是以利而斷,以益而動。」
「在這世上會不顧名聲、才貌、權勢、利益金銀為我著想之人,恐怕也只有爹娘與叔父,除了他們,誰又會真心與我知冷知暖,掏心掏肺;除了你,誰又能真心與我相惜相知,傾心吐膽。」
「你為何是隻鬼呢? 」
甘羅有些落寞的喃喃自語,我看這樣的他,一時間竟恍惚起來,不知該說甚麼,明明他說的有理,但我卻深知,在這層"情理"之中,人與人的關係亦是存在著純粹的善意,可奈何他心思聰慧,看透成人的交際景象,又如何能想到冥冥之中,亦是有無關利益的傾心與互助。
半晌過去,甘羅眼皮子疲憊地的緩緩垂下,徒留一句模糊的呢喃,縈繞於我的心頭。
「若你與我同為人,我是否就可以......。」
「我就可以與你一起體會世間千萬百感,實軀同心相伴與你。」我輕聲接下甘羅睡前的夢語,這是我頭一次感受到如此純粹又洶湧的感情。
它無法用言語比喻,無能觸及,只有彼此能夠相通於此,如同無形的線結糾纏,融合,直到最後,它—成為了一體。
今夜過去,繁星的靜默好似為一月後的游趙一行默默祈禱,受雲海擁抱的皎月陷入了長夢,一夢過後,終歸得從浮雲殘夢中再次甦醒。
10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7ANzN4lJHT
*
10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xcEYDVpNnA
子時深夜的咸陽宮內,唯獨一處的大殿還留著淺淺燭光。
大殿中的贏政隨意地安坐於榻,他身著金縷寢衣,烏絲隨意的垂落在他菱角分明的肅顏上,儘管他披頭散髮,卻是難掩其威嚴的神態,他瞥了一眼掌中的密卷,一陣冷笑,密卷脫手,頓時被他丟飛在了案桌前方。
案桌前站著一名男子,男子醒目柔順的赤髮散落在他寬敞的臂膀,一雙比劍鋒還要鋒利的眉眼恭敬注視著眼前帝王。他一身暗紅的長袍在燭火下未顯得鮮明,反而是令人更難以看清。
他便是數年後的中車府令,趙高,而眼下,他還只是君王暗地裡的隱密部下。
案桌前的趙高見了贏政丟出的密卷,瞇起了尖細的眼掃了一眼密卷,開口朝贏政稟告道:「大王,文信侯大人的門客,甘家末子甘羅,明日便要出使趙國,而長信侯那處奴才以派人前往,既然人事已成,剩下的便只能是順從天意了。」
趙高的語調非剛非柔,少了男人的雄氣,卻也談不上女子的柔和,贏政聽聞,黑眸微抬,與趙高對上了眼。
「此刻,殿內只有你我二人,門外也有你精心培養的鬼蛛守著,如此,這顛倒陰陽的聲音,也可給寡人省了。」
「奴才,遵命。」頓時,趙高原本似男似女的嗓音陡然一轉,便如暗夜中鳴響的鐘鼓,令人感到厚重與低沉。
贏政方才看了密卷,是關於兩月前,他親自下令呂不偉與昌平君,前往雍盛調查長信侯所回傳的結果。而此密卷是昌平君等人隱瞞呂不偉,並託陰陽家,大秦右護法月神給贏政秘密帶回。
密卷中,長信侯嫪毐與其母趙太后私下偷生了兩子,此消息還流傳再雍盛內,令臣子百姓恥笑,更甚者,暗市之中還漸漸流傳出大秦大王贏政,乃國相文信侯,呂不偉之子的非議。
贏政心想,當初呂不偉暗中與趙太后藕斷絲連,他處在大秦興榮的浪尖口,為了朝廷安穩以及鞏固勢力,他便將自己母后不忠,臣子不敬之事給忍了下來。
如今呂不偉自從擔任相國,雖無再與趙太后往來,卻是在當時私下舉薦了一名男子敬獻與趙太后。
那名男子便是嫪毐,而嫪毐則是由呂不偉的心腹甘櫟所尋得,抑是甘櫟替呂不偉安排,讓嫪毐走過虛假的腐刑,也就是男子的去勢的刑法,然後再藉機以宦官的名義服侍太后。
呂不偉心計深沉,善於用人,使得這一切本該被砍頭的大罪,老實的藏在了雍盛的隱密角落數年之久。
殊不知,這一切亂象看再贏政的眼裡,卻是一場以人相賭的棋局,從頭到尾,贏政要的只有一個結果。
"大秦的霸業,也就是他自己,贏政的萬世霸業,而這霸道的盡頭,絕不容許大秦以外的任何勢力存在。"
「自從當初嫪毐平定成蟜之亂,排除朝堂內部的韓國隱患,寡人就久未有這種心血沸騰的感受了。」贏政低沉的嗓子迴盪在肅靜又空曠的殿堂中,此處唯有他與眼前赤髮臣子趙高。
「坐。」贏政從容向趙高說道,語氣中倒是少了幾分帝王之威。
趙高聽聞,俐落的整理的衣袍,自然的坐在案桌前的席榻上。他與贏政對視不懼不怕,反而露出了平靜的顏色。
「趙高,此局寡人所下的決斷,你可否覺得無情,又或者說,你,可否覺得我無情?」贏政黑眸中映射的燭光泄泄搖動,卻動搖不了他心底堅定不屈的執念。
「大王,我猶記得當初母親駑鈍,開罪了楚系親族。蒙受他們恩典,我與母親日夜在隱宮受盡凌辱。母親早逝,奴才孤苦無依,若非大王您看中了奴才微末的才學,救奴才於水深火熱,奴才今日便已是無塚亡魂,孰可憐見。」趙高冷眼與贏政平靜解釋,平放於腿上的雙拳卻是越攥越緊,直到腿上的衣料漸染了點點暗紅。
「無論喜惡,君王在上,任是枯骨遍地,鬼哭神號,奴才從始至終都認為大王有情。」趙高的銳眼與贏政相視,語中的肯定與堅信令贏政的怒眉微動。
「然,大王非只是秦國的大王,大王欲行常人無能行之,欲立常人無能想之,是以情與無情皆為一體。」
「呵,寡人記得此話出自月神法師之口,未料你竟記下了。」贏政哼笑,一臉的威怒無聲消去,只留威顏下的疲乏。
「大王與奴才都曉得,秦國如今國力強盛,是因法之大勢,集諸力加諸於身,集諸權獨攬王手,才有可勢如破竹的把握,一戰昏庸無能的六國君主。」
「趙高,當今秦國能走到此,不只是因先祖開明,新法施行,更有賢才輔佐。寡人當初為了大局,為了曾經的功臣,默許呂相之過,而他亦有心,知曉避嫌。一月前,我曾私底下召見過呂相手下的甘羅,他之才識,若再經過歲月雕琢,朝堂黑白洗禮,將來定是棟樑之材,失之可惜,棄之可恨。」贏政語畢,拿起桌上的酒盞一飲而盡。
趙高聽贏政所言,眼中掠過了即為細小的冷意。
忽地,贏政掌中的青銅酒盞重重一放,咚的一聲,差點碰壞了盞下的秀木案桌。
「如你所言,秦國要力戰六國,必須獨攬萬權,嚴刑法度,排除諸國勢力,不論明暗兩處,大秦王權萬不可受他國染指,你也算是寡人一手調教而出,你的法學造詣與我同心,朝堂上下,唯有你曉得寡人的執念。寡人一路隱忍,從當初卑賤,處處低頭的趙國質子,到如今立於大秦之巔,萬人俯首的秦國君主,多年的布局的這盤棋,從今往後只有得勝一說,不可有分毫差池!」
趙高並未被贏政的突來的激昂宣言給震攝,他眉眼鬆開,再次抬眸無懼的凝視贏政,直道:「大王,你方才問趙高你是否無情。」
「除了月神法師所說,無情與情本為一體,我真正的答案與其不約而同。」
「奴才的五臟六腑,實心的只想到一塊去,大王與我而言是有情不假,但大王亦表天,將來勢必成為天下大王,天無情,以萬物為芻狗,大王,自然也無情。」
「奴才方才所言,人事已成,剩下的是順從天意,而王意便是天意,大王定將如願以償。」
贏政聞言楞神一剎,朗聲大笑後,替趙高斟滿酒水,兩人雙眸夾帶冷意與果決,互視半晌後,彼此皆將酒中之物一飲而盡。
「談了一日政務疲乏的很,夜深人靜,我才憶起久未拜見過你的書法,聽聞你六鋒成一氣的書法運筆已有所精進,是以,六鋒玄玄,集集一體,六體從一,一化六體。」
「你,可願為我執筆?」贏政嘴角微抬,凝視著趙高,他將帝王氣勢都留在了方才的談話裡,眼下,他沉聲一問,語中溫和平靜。
趙高難得沉著的神態掠過一抹驚詫,他和顏悅色的閉起鋒利的銳眼,莞爾淺笑,應道:「趙高,願為君意。」
ns 15.158.61.41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