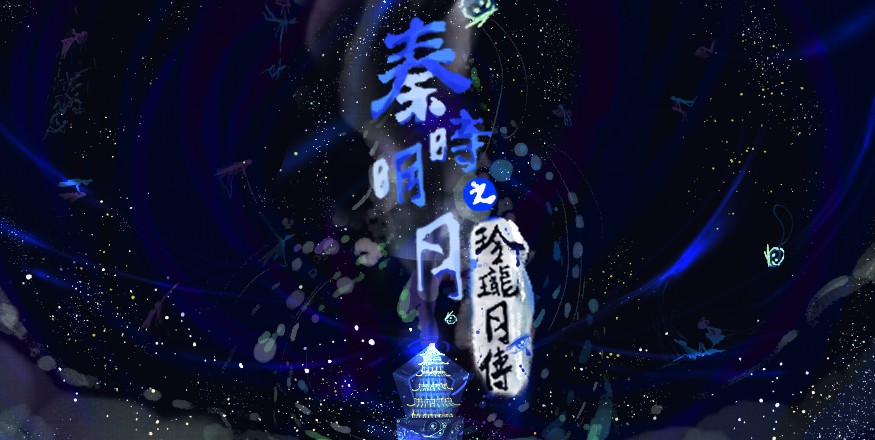不知又過了多久,腦中被朦朧的悲傷覆蓋,我感覺到周遭有人在哭泣,憤恨,害怕,惶恐,還有人......難以置信的瘋狂顫抖。
經歷過無數次快將人逼瘋的遺忘與甦醒,思緒為此延宕了好久。時間悄悄流逝,當身軀的感知逐漸從朦朧中清醒,眼前的景色方才清晰的映入眼簾。
灰濛濛的天空下,大秦的高台樓宇死寂的佇立在空曠的砂土上,四周嚴肅的兵士整齊劃一的一字排開,荒地上近百人被粗繩綑綁著,卑微如罪人的將頭扣在泥沙上。當我仔細端詳面前跪著的人群的瞬間,內心忽然湧出難以承受的恐懼。
眼前跪地低頭,哀聲低語的人群是甘氏宗族,是當初依依祝賀過,送別過甘羅前往趙國的甘家血親,而在人群最前方百尺處的兩道身影,則擊潰了恐懼的最後一道防線。
只見甘羅與甘櫟雙膝跪地,一高一矮的身影前方站著威嚴的大秦君主贏政。
「嫪毐受車裂之行已伏誅,呂不偉禍亂宮闈,失德失職,褫奪相位,公至朝堂,私至家舍,但凡朝臣,門客,僕從者與嫪毐之亂有所干係等,均已死罪論處。」
「甘氏全族上下聯通呂不偉,甘家甘櫟暗度陳倉助其進獻嫪毐,惡行惡狀,連坐處之,當誅全族!」
此時贏政厲語中的意思,如同利刃將我僅存的理智斷的一乾二淨。我終於明白當初在趙國王宮時,從玲瓏上頭感受到的恐懼是什麼,那是無法停止敲響的警鐘,是無可避免的未來。
明明上一眼甘羅才剛遊說趙王不費一兵一卒拿下五座城池,用他引以為傲的計謀,犧牲他國人民的鮮血,在權衡利弊下揮灑才智換來大秦更大的利益,甘家的榮譽,那現在,眼前的這些慘況又算什麼?
"甘氏全族當誅,那甘……甘羅該怎麼辦?他敬愛的爹娘該怎麼辦?他珍惜的叔父,守護的甘氏都該如何? "心魂震顫下,意識的每一寸都像被寒針反覆扎刺,我已經無法去理解眼前發生的一切。
頓時腦子像進了水無法思考,眼前清晰的景象開始模糊成血色,身心都在這瞬間為之顫動,我試圖驅使四肢奔向甘羅,卻發現身軀像被釘在原地般無法行動。
正當我以為此刻的情勢,已經讓人絕望地無法喘息,殊不知下一刻才是真正令人窒息的絕望。
只見甘櫟緩緩地抬起手指向他身旁的甘羅,他用孰悉的口氣,有條不紊地說著我不理解的話語。
「嫪毐的確是罪臣所尋得引薦於文信侯,而文信侯將他進獻於趙太后亦為罪臣一手打理。然,多年以來,甘氏唯有本家之人與文信侯有所來往。文信侯向來禮待門客,對待心腹之人必會贈予奇珍以表重視之情,若大王欲查證文信侯與甘氏的關係,大可從奇珍信物下手,眼下甘氏一族只有甘家有文信侯所贈與的千年丹木。」
「此木為文信侯珍藏的貴品,千金難買,世上難求,其木紋與質地只要讓木匠一觀便可分辨。過去甘羅父母收下貴木後,將貴木贈於其子甘羅。而甘羅則將其製成傀儡,如今傀儡由甘羅隨身保管,大王一搜便知。」
「是以本家之人與文信侯勾結的證據便是甘羅身帶的傀儡,文信侯贈與甘家的稀世奇珍,偃師丹木。從始至終與文信侯有所干係者,只有罪臣以及甘羅本家等,其餘甘氏分家親族對此均不知情,大王公正嚴明,還望大王信賞必罰,依功者論賞,切莫傷及無辜,殃及池魚,導致大王多年來積累的恩威受損。」
剎那,周遭的聲音變得模糊,唯獨甘櫟的話語入了耳,就像是寒針輕巧地順著耳道進入,再狠狠的扎破耳膜。
明明他從頭到尾語氣鎮定,明明他是一臉孰悉的堅持,但為何他此刻出口的話,卻是荒唐的讓人不可置信。不用誰來明說,與甘羅相伴四年之久的我,是再清楚不過甘櫟話裡的真假。
我心知肚明甘氏宗族中雖有部分成員與呂不偉有所牽連,但大部分的外房親戚從頭到尾不曉得此事。此刻就是他們被贏政下令處死,也是冤枉的無處申冤。
一句"我不曉得","我是被冤枉的"根本說服不了贏政,事已至此,贏政本可以直接處死甘櫟,卻選擇肅清整個甘氏宗族,還特別巧合的等到甘羅回來再行審判。
種種跡象,無不是表明贏政對甘羅有某種企圖,但這種企圖無論好壞,對於甘羅來說只代表著眼前滅族的慘狀,負罪的罵名。
甘氏宗族與呂不偉有所往來雖是事實,但這也成了贏政定罪的理由。如今甘櫟以丹木為證,將甘家與甘氏的關係撇得乾淨,只要犧牲甘羅一家,便得以保全整個宗族。
甘櫟當初將傀儡託人送至趙國,難道便早已料到今日的慘況?!
可不管怎樣這樣殘酷的話語任誰出口都好,但是此時此刻為何偏偏是他,為何偏偏是甘羅最信任,最敬愛的叔父?
而甘羅,從頭到尾為了甘氏的甘羅,在生死抉擇的面前又能反駁什麼?
我驚愕地看著贏政喚來趙高,半個時辰過去,數名匠人被僕人匆匆請來。這時一旁的趙高向甘羅走去,他盯著甘羅腰部隆起的衣料笑得令人心裡發寒。他動作輕蔑地在甘羅身上又搜又找,最終才將甘茂傀儡從甘羅腰間搜出。
趙高將傀儡給予匠人判斷,數名匠人一拿到傀儡無不是議論紛紛,雙目像活見寶物似的發光,他們數人細聲吵雜一會,方才向贏政稟明傀儡的丹木材質,實乃呂不偉珍藏的千年丹木無誤。且傀儡本身作工精細,若不論木質,光憑傀儡的手藝,當真算是巧奪天工。
我看贏政劍眉怒蹙,眼中的狠戾越發越張狂。他打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聽匠人講完,他此刻的眼神就像是確定了答案,便迫不及待的想要快點了結眼前敵人一般。
只見贏政瞥了一眼身旁的趙高,趙高立馬從後頭領來一位男子與一位少年。
此二人中男子身穿材質高雅的素服,另一位少年一身絹衣,衣上的繡料華貴異常。
「寡人想知道,今日若換作是你們二人,你們又會做何決斷?」贏政並未回頭看向他們,他冷肅的視線始終落在甘羅的身上。
素服男子率先恭敬站出,拱手道:「兒臣以為,有罪當罰為正法,罪人甘櫟其罪重大,應當同嫪毐一樣處以車裂之行,而甘羅此次初始趙國獲得功績,理應斟酌功過大小,不可倉促行刑,其餘甘氏及甘家等人同為甘羅親族,若徹查過後若無證據犯下罪刑,便不須施以誅族重刑。」
「是以殺一無罪,唯恐人心惶惶,無錯含冤,日日憂怕。正所謂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賞罰本當有所依憑,須功過分明,萬不可牽連無辜,百姓應當敬君,而非畏君,如此重罪濫施,恐不利君王名譽。」
素服男子話音剛落,他身旁矮他數寸的華服少年朗聲大喊就是一句應證身分的"父王"。
「賞罰分明本無錯,然賞與罰本皆出於君王之意。亥兒想,王者施行,背法去勢,亂矣。縱依法行之,勢未見長,未能嚇阻愚昧罪民。是以王者,自是威攝天下,人心好惡,從無真心敬服之說!」
「以現狀為例,甘氏甘家唯出一甘櫟,便可以小姿事,禍亂家國。今日只罰了甘櫟的罪,世人皆以為如此禍國大事,只須以一人之命抵之,那來日,十個,百個,千個一呼百應甘願赴死,又是能夠不顧全局,再次顛倒朝政,攪亂事非!」
「當今愚民頑劣,王者則應當嚴刑昭告天下,重罪當前,連坐處之,天下草芥百姓,皆有以身查察的義務,若誰犯了,九族之內無人可以倖免。甘氏甘家此刻便是要做這殺一儆百的開路石,爾後誰敢心懷異心,便是同個下場!」
「寡人知曉了,你們下去吧。」
贏政抬手一揮,他身後的兩位公子年紀稍長的公子恭敬行禮後緩緩退去,而另一位少年公子則是一句亥兒告退,便一臉輕鬆的退了下去,彷彿他眼前近百名即將被處死的人,只不過是路上不起眼的石子。
贏政瞇起他冷肅的眼盯著甘羅,他充滿威勢的口吻將我原本高懸的心勒得更緊。
「寡人說過,叛國禍亂者,寡人一個都不會放過!」贏政怒喝,沉重又響亮的聲音迴盪在偌大的刑場。
「然,寡人亦曾立誓,大秦國土,信賞必罰,此次嫪毐謀反雖與文信侯脫不了干係,但是文信侯畢竟曾輔佐先王,勞苦功高。是以大秦律法,有功者當賞,有過者必罰。大秦厚待良士,求賢若渴,若任何人可同甘羅一般不費吹灰之力得五座城池,如文信侯一般曾安邦治國,身負擁立先王之功,那寡人自然是有理可評罪等輕重。」
「寡人念在文信侯過去為大秦盡心盡力,敬心愛國,功勞之高,只褫奪相位且免去誅族罪刑,而其餘相干人等,無功不說,諂媚陷主,奸行亂國。」
「無論甘家亦或甘氏,本次與嫪毐之亂有干係者,無論關係淺重,皆一律以死罪論處!」
贏政舉起他無情的手,玄色衣袖隨著他手臂無情揮下的同時,甘羅父親的頭顱伴隨著一瞬的快刀人頭落地。
此刻鮮血染紅視線,甘氏親族的頭顱就像無人在意,任由腐敗將其扯落枝頭的果子,無人在意的重重落到地上。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我絕望哭喊,死命地在原地掙扎,口中幾千句重複不斷的否定,更加深自己心知肚明早已經無法挽回的悲劇事實。
眼前的甘羅就如同當初扶桑凋謝時的我一般,兩眼被喪失生意的絕望占滿。
我崩潰的喊著甘羅的名字,希望他能注意到我,能看著我,而非是用那種心死的黯淡星眸,眼睜睜的望著眼前飛濺的鮮血,咚咚落地的頭顱,不斷在他的眼前重複折磨他的心靈。
贏政刻意將甘羅父母分開處刑,又是一個一個慢慢地奪走了甘羅至親的性命。而無情的刀口在奪去了數十條人命後,眨眼間回到了甘羅母親的頸部上。我看著此刻贏政的眼神,那雙像是早已安排好一切,冰冷無情盯視甘羅,像是要在甘羅的臉上找到任何一絲細微的表情。
「甘羅!」
「勿忘名,莫忘本。羅心所往,星辰所向。」
「你永遠—是娘心中最棒的羅兒……。」
刀斧落下,她最後一聲溫柔的叫喊卻永遠成為過去,再也不可能回來了。
「不!!!!」
「甘羅!!!!!」吼聲出口,僅此一瞬卻在轟轟雷聲中戛然而止。
耳邊充斥震耳雷鳴,腦中被甘羅支離破碎的心給占滿。即便面臨生離死別,我卻從未聽見她的父母有任何一瞬的哭嚎與遲疑,就連甘羅娘親最後對他的叮囑都是堅毅的令人動容。
我由裡到外發瘋似的扯動四肢,直到感受到裂心之痛,宛如要將我的意識從神魂上一塊塊地給剝離下來。接著悅耳的破碎聲佔據腦海,在瞬間伴隨著蒼穹上的一聲雷鳴巨響,我的身軀終於脫離原地。
只看趙高冰冷的拿起匠人手中的甘茂傀儡重重的摔在地上,他在甘羅的面前狠狠踐踏,蹂躪腳下被沙土染髒的傀儡,而甘羅只是雙唇顫抖,面如死灰的看著。
我擦去所有淚水徑直朝甘羅奔去,穿過冷面帝王,越過荒涼黃沙,即便耳邊是一句又一句無情的君王威語;是此起彼落的甘氏親族埋怨怒吼甘羅家人與甘櫟的聲音,也無法阻擋我拼命的朝甘羅奔去。
當我奔到甘羅的面前擋住他的視線,他看著我,心死的藍眸在這瞬間恢復一絲溫度。我捧起他因絕望而冰冷的臉,將我的額頭死死貼在他的額頭上。
此刻,我們彼此的鼻尖相碰,我收拾好所有負面的感情,堅決的凝視著不發一語的他。
「甘羅,我在這!」我昂聲大喊,甘羅黯淡的藍眸泛出晶瑩淚花,他張著嘴,卻沒說出任何話。
「說好的一言為定,無論是生是死,我都陪你!」我堅定道,直接將他擁入懷中。
「你必須冷靜下來,事已至此,無畏風雨,方覓天晴。」我感受到甘羅身軀猛力地顫抖,感受到他心裡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悲傷與憤恨不甘糾纏的無休無止。
「羅兒,對不起,我上次未能對你說出口,還口是心非的拒絕你。其實我一直都明白的,明白自己的感情,我喜歡你,真的,真的好喜歡……好喜歡。」
「無論他人如何待你,我始終都會陪在你的身邊,所以你必須振作起來,你必須得活……。」話未說完,雷聲滾滾,數道厲雷兇猛劈下,清脆的碎裂聲在耳畔響起。
眨眼間,甘羅嬌小的身軀冒出陣陣紫焰,紫焰燦爛覆蓋他的身軀與容顏令我看不清他的表情,頓時我能感受到他的身軀裡頭有股未知的力量正在無聲暴走,並且牽引著紫焰的火勢從他的喉頸處暴走衝出。
「不!!!!!」
霎那的楞神,當我聽見甘羅尖聲嘶喊的同時,全身上下每寸肌膚彷彿要被撕裂成碎片,我這才意識到我的時間不多了。
我再次捧起甘羅的小臉,即便耳邊傳來身軀清晰又響亮的碎裂聲,也無法阻擋我朝甘羅暖暖淺笑,他看著我,原本因驚恐而慘白的神情,恢復了些許的溫度。
「這不是頭一次了,你會等我的,對吧? 」甘羅一楞,咬牙死撐,含著淚輕輕頷首。
「如論過去或未來,我始終喜歡著你。」
「甘羅,活下去,等我。」話音一落,轉瞬的消散快到連我都未能好好看清與聽清甘羅的任何反應,我又如往常一樣,無聲無息的就像從來未存在過一般消失在這個瞬間。
不過,即便如此我也不怕,畢竟,這又不是頭一次了。
我相信我會等到甘羅,當我再次甦醒,他也一定—會平安的等著我。
10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ACsVkMMSpp
*
10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2e5e5eizoE
暗雲之下,雷龍在天穹來回穿梭,瓏月清晰的身影伴隨著轉眼即逝的雷光,頭一次在甘羅面前消失的無痕無跡。
甘羅咬緊下唇,慘白的薄唇被朱色染紅。他聽見身後的甘氏親族有人唾罵,罵他們一家上下害慘宗族;有人痛哭,突然受冤便是家人性命不保。
誅族之罪裡頭有人知曉內幕,卻選擇痛罵;有人毫不知情,卻是心疼甘家與自己的家族。
何謂人性,是以利而動,以益而斷,這些甘羅都是明白的。但是曾經的他即使知曉,卻仍然相信自己的親族與敬愛的親人。
現在他最想守護的親族,最為敬愛的至親,卻成為親手葬送他們一家活路的人,而父母的坦然與甘櫟的冷漠,令他逐漸迷失在層層陰謀算計當中。
甘羅冷笑著,眼睜睜看著心儀的天仙佳人在他眼前消散;看著被汙泥染髒的衣袍;看著地上任由他人踩踏的甘茂傀儡;看著無能為力的自己。此刻無權,無勢,無力的他算是個什麼東西。
算是靠著與生俱來的氣運,靠著聰慧過人的頭腦,到最後為甘家,為了大秦,闖過數次鬼門關,帶著滿腔熱血,天真走進君王早先設下的死局,擔下君王冰冷的降罪。
此刻的他終於認清了一件事,人心詭變,不可信之,人性孱弱,不可試之,即便是至親的親族,人的任何關係擺在利益前頭脆弱如枝,一折兩斷。
此時此刻,他,選擇不再相信任何人,他,只看他們的心。
厚重的烏雲彷彿承受不住地面上悽慘哭喊的求救聲,頓時,雨點滴滴,在轉眼間如狂瀑傾瀉而下。
贏政身旁的趙高即刻拿出準備好的傘為贏政撐起。贏政高傲垂眼看著眼前被雨水打溼的甘羅,他緩步離開趙高撐起的傘下,趙高本想追上前,卻被贏政抬手制止。
此刻的贏政與甘羅只有一步的距離,甘羅沉默不語,低頭看著地上的被父母的鮮血染成血色的污泥。
贏政不顧雨勢的與甘羅一同淋著雨,他沉默半晌後瞇起眼,對甘羅冷道: 「寡人說過,你若要一窺大秦霸業,便要做好覺悟。」
甘羅聞言緩緩抬起頭,他很慶幸自己發紅的眼眶與止不住的淚水,順著滂沱大雨消失在沙泥裡。他冷眼注視贏政,冰冷道:「大王曾言當今急危非五國,乃旁親之人。如今甘羅已非文信侯門下之人,還望大王看在卑臣淺薄的功勞上,放甘氏剩餘的血脈一條活路。」
「聰慧如你,你應當想到今日罪行何人無辜,何人該死,即便你曉得甘氏有人恨你,恨整個甘家,即便如此你依然替他們求情?」贏政瞇起眼狐疑問道。
「甘氏畢竟為甘羅本族,無論我受何委屈與磨難,甘羅與本族終究是血濃於水,就好比…….。」甘羅停頓剎那,在一瞬間露出無情的陰冷淺笑。
贏政在察覺甘羅的笑容後,竟頭一次打從心底覺得看不清眼前這位天才少年。
「就好比,生養甘羅的大秦,大秦永遠會是甘羅的歸處,犧牲骨血,融盡所念,只為秦土。」
贏政咧嘴一笑,聽明白甘羅話中之意。於是,他大手一揮,令行刑者停下手中刀斧,留下為數不多的甘氏血脈。
贏政看著眼前目光決絕的俊容少年,他雖然覺得在這凜凜眸光的背後還藏著某種他看不清的本質,但他依舊對甘羅所做的選擇感到滿意。
而跪在君王面前的甘羅,何嘗不知自己父母以及甘氏部分成員受冤,可無奈王法之下,以一儆百是從古至今不變的死則。要說甘氏何錯,撇除甘櫟所作所為,其罪僅僅是捲入了王權勢力的鬥爭之中,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甘羅自己是再清楚不過。
正當贏政與甘羅對談之際,數百尺外的一名將士早已默默地離開刑場。他一身乾淨的漫步在泥水上,孤身向不遠處的馬車走去。雨點在落到他身上的幾寸間被他刻意散出的內力給擋下,他精準的操控內力,甚至到了一塵不染的程度。
走了沒幾步將士輕輕抬手,他粗曠的身軀與嚴厲的面容頓化輕煙消散在雨中。
頓時雨中的將士消失無蹤,唯獨剩下一名體態高挑,端莊清冷的美人。她眼眸前覆蓋的青色緞紗優雅飄動,一身淡藍色的月紋外掛與美麗的紫色髮絲在雨中醒眼異常,她是陰陽家的右護法,大秦的護國法師—月神。
月神端莊的坐入馬車內,車內的大司命早以在車裡等候許久。
她見到月神歸來,立刻朝月神恭敬點頭,認真道:「月神大人,此玉以我的力量尚可控制,此番倒是難為大人親自上陣壓制玲瓏。」
月神坐在馬車上閉目養神,她溫柔地捧著碧玉玲瓏,半晌過後才淡淡的回應大司命。
「天底下除了東皇閣下,無人可以壓制瓏玉之力。瓏玉之源就如同無邊無際的大海,我等不過是試圖干涉海流去向的細屑罷了。」
「況且此番由我親自出手方是穩妥,畢竟方才玲瓏本身承載不住瓏玉之力,若非我及時以出手護住玲瓏玉石,玲瓏碧玉恐將毀損。」
「罷了,如今玲瓏中的瓏玉本源已然消失,是時候回去稟明東皇閣下了。」
「是。」
大司命應聲過後,恭敬的退出月神的馬車裡頭,轉而搭乘另一輛馬車。月神見大司命離開,嘴角溫血溢出,又是靜心調氣數十回方才緩過去。
「想不到頭次感受瓏玉之力,竟是連半刻都無法撐住。」月神淡然自語,默默地攥緊掌中裂痕滿佈的碧玉玲瓏。
一個時辰過去,月神掀起被雨水浸濕的簾子,冷眼看向外頭的暴雨無情落下,看著車馬往九天曦和的方向行去。
10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AymGCiR3nU
*
10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sPC4g2jn4n
處刑結束後暴雨依然無情地傾倒而下,此刻甘羅跪在甘家外頭的荒地上,淋了四個時辰的雨,吹了四個時辰的冷風,只為了確保自己父母的遺體被贏政指派的僕從確實安葬。
如今贏政以文信侯曾經舉薦之名,以及甘羅身負大功,身懷負重致遠的才幹為由封他為左丞相。此舉一來堵住未能殲滅的文信侯殘黨的嘴,二來以甘羅的才智拜相上朝,收為己用本為贏政所願。
贏政心想既然已經暗地裡斬斷文信侯與甘羅的關係,險遭滅門的甘氏宗族也不敢再與其他勢力有所牽連,只能仰仗甘家末子甘羅。
七日過去,正午時分的咸陽城西市熱鬧非凡,各地的百姓頂著烈日圍繞在西市刑場的外頭,只為了目睹文信侯的心腹甘櫟受車裂之行。
此刻甘櫟身軀微懸在半空之中,他的四肢與脖頸被粗麻繩分別綁在不同的馬車上,眼下只差時辰一到馬車駕動,他便要被五馬分屍。
一會過去,眾人的情緒越發激動,他們大聲嚷嚷,向甘櫟的身軀丟去了無數顆碎石子。
即便甘櫟四肢受拘束,他依舊漫不經心的運起內功,悄無聲息的彈開欲攻擊他的石子,丟石子的人群見石子從甘櫟身邊擦過,以為是自己沒丟準,於是更加惱怒的猛力拿起石頭像甘櫟砸去。
結果一頓亂石胡砸後卻是驚動刑官,刑官隨口指示又將胡鬧的人群給驅離後,刑場上的喧鬧方才減緩些。
一個時辰過去,甘櫟終於等到行刑之期,他抬眼看著曾經結識的刑官神色黯淡,猶豫半刻才顫巍巍的丟出行刑令。
行刑令落地的瞬間, 吵雜的人群忽然安靜下來。只見眾人突然低頭緘默的互相推擠開出一條小路,甘櫟不以為意地望向獨走在小路中間的人,剎那,他的瞳孔放大,身軀僵直,直勾勾的盯著人群中有些矮小,卻又威勢凌人的少年。
那名少年是甘羅,他的姪兒,今日除了是甘櫟自己受處決的日子,亦是甘羅任職左相的好日子。
甘櫟看著甘羅不快不慢的走到最前頭,看著他藍眸裡的冷肅,一身華貴異常的官袍,在烈日下顯得格外耀眼。
如今兩兩相視,過去的千言萬語,到了最後卻甚麼都沒剩下來。而甘櫟乾裂的雙脣微顫,往常自然出口的玉奴二字,如今卻被他鎖在喉間裡頭。
片刻,馬匹被行刑者以長鞭催促,甘櫟全身上下的肌膚與骨骼開始被割人的粗麻繩撕開。
甘羅冷冷看著甘櫟,並從衣兜裡拿出一個木枝,一個陪他走過寒夜荒沙,闖過無數關隘與君王虎口的相思之物,甘家院前的櫟樹樹枝,她的娘親親手折與他的櫟枝。
甘櫟在看見櫟枝的一瞬,忽然忘記了身軀的劇痛,憶起了過去的種種。
「嘎—巴—。」
樹枝清脆的斷裂聲響起,甘羅親手在甘櫟的面前折斷了櫟枝,他舉起櫟枝朝甘櫟身軀輕蔑一砸,這一砸直直砸在了甘櫟的心窩上。
甘羅砸出樹枝後頭也不回地轉身離開,但是此時的他卻不曉得,從頭到尾能觸碰到甘櫟身軀的也只有他掌中脆弱的木枝。
甘櫟見甘羅離去,暗血一咳,大攤污血嘔在沙地上。在他氣息將盡之時,腦中憶起逐漸模糊的背影,聲聲顫抖的欣慰呢喃。
生死一瞬,他彷彿回到了過去,看見曾經在櫟樹下清朗笑著的藍眸幼童,看見了甘羅身上不凡的未來。
「玉......奴,叔父...叔父答應過你的......一言為定,便是這...樣.....就....好......。」
行刑結束後,甘櫟的屍身被曝曬在咸陽城市近七日有餘,在此期間甘羅包括殘存下來的甘氏,無人去看過他,直到官府定的七日期限一到,甘櫟腐敗的屍身才被甘羅遣人收了去,最後葬在離甘家十里外頭的一棵櫟樹下。
又過了數日,傳說中年庚十二拜相的神童卻突然傳出病恙。
贏政收到消息後,雖立刻遣人去探望甘羅的狀況,但是卻只得到甘羅身體病重,昏迷不醒的消息。爾後,贏政又讓人送去數十樣上好珍藥與名醫卻也是未見起色。
就這樣一個月過去了,望月之下,甘家的宅院裡身姿嫵媚的大司命不請自來,她輕鬆的繞過甘家的僕從,走到了甘羅的臥房外。
她推門而進,看到了身軀慘白,面容枯槁的甘羅好似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
她步伐輕緩地走向床邊伸出艷紅的手,試圖查探甘羅確切的情況,忽地她的背後遭人一碰,驚的她立馬轉身過去。
大司命回首猛瞪,發現眼前站著的人竟是甘羅,她內心驚呼著此次竟未能察覺他的半點氣息。
甘羅見大司命吃驚的樣子,放下方才點碰大司命後背的劍柄,淡然道:「跟我來。」
二人來到庭院,院中長年青綠的櫟樹葉子枯黃,伴著一張孤冷的石製桌椅沐浴在月光下。
「你房裡頭的人是怎麼回事? 」大司命有些不快的問道。
只看甘羅隨意地用衣袖撢了撢眼前乾淨的石椅,便從容地坐了上去。他望著月圓愣了半刻,方才回應大司命。
「替身罷了,要瞞過羅網與陛下讓他病成這半死不活的模樣,可費了我不少力氣。」
「陰陽家大司命,半夜擅闖他人臥房,莫非是有別的見不得人的興趣? 」甘羅挑了挑眉,嘲諷的語氣與過去相比多了幾分的陰冷。
「呵,牙尖嘴利的小子,如今你沒了至親,甘氏也只不過是一群拖油瓶,你自己又當如何?」
「我在等一個人。」甘羅抬首望著明月,語中難得的溫情令大司命聽得都有些出神。
「以此為前提,無論如何我都必須活下去。」
「哦,何人?」
甘羅聽聞大司命好奇的提問,嘴角頓時勾起玩世不恭的弧度,便是注視著大司命不發一語,大司命見甘羅認真看著自己,眉眼閃過一絲驚詫,便不再多想立刻轉移話題。
「你突然裝病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
「陛下雖將羅網的權柄交到趙高手中,卻不知羅網暗地也不安分。近來羅網的行事越發縝密,完全不留任何蛛絲馬跡,若要尋得證據對付趙高恐是不易。」
「況且最近羅網明裡暗裡時不時便來甘家光顧,若非我設圈套將他們支走,再尋來一個能夠以假亂真的替身,再過不久恐怕趙高的羅網下次送的見面禮,便是底在喉間的刀柄了。」
「不錯,你倒是有自知之明,既然你暫時構不成威脅,趙高則會先動楚國勢力的右相,昌平君。」
「但是即便你撐過這段險期活下去,你之後又打算如何? 」
甘羅一楞,淺笑著道: 「變強。」
「真是籠統的答案。」大司命勾起嬌豔的紅唇,不以為然的凝視著甘羅。
「身處朝堂,即便是手攬大權的呂相也會被人拉下高臺。這次,我不會再當局中傀儡任人操弄,如今的我只願做這控偶之人,作為觀局者洞悉世事,把握己命,恪守本心。」
「聽起來,新任的左相似乎對目前這個位子不太滿意啊?」
「易窮則變,變則通。大司命此次前來是為了向我點明此事吧?」
「呵,不愧是少年天才,既然如此明人不說暗話,尊貴的左相大人若對目前的境遇有所疑慮,可否願隨我到陰陽家拜訪一回?」
甘羅聽聞大司命誠摯地邀請嘴邊的笑意加深,他望著圓月,一聲哼笑傲然應道:「哼,正有此意。」
ns 15.158.61.12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