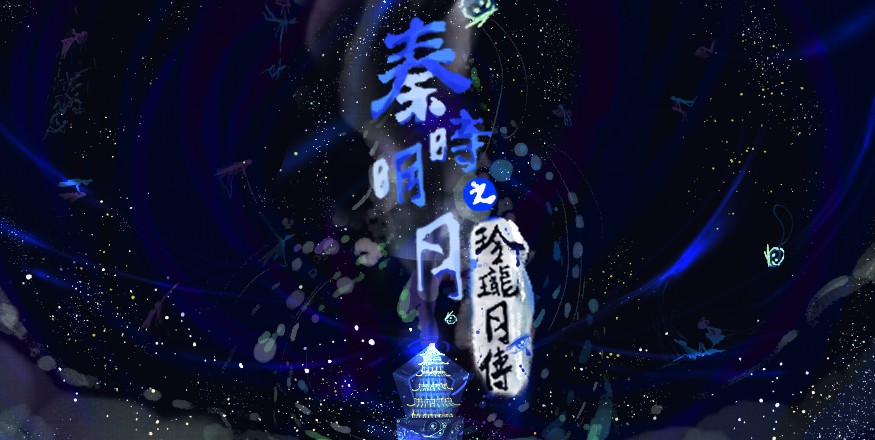秦王政九年,楚國某處郊外一名女嬰細聲泣啼,此地杳無人跡,只留下了一名棄嬰以及荒地上的斑駁血跡。過了許久,一名身著素衣的少年偶然路過,他尋著遠方細小的哭聲而去,片刻,映入少年眼簾的是被污布包裹著的女嬰,以及女嬰身上一塊看起來貴重異常的玉玦。
少年見此情景猶豫了一陣,他看著這片荒地,見了地上的血跡,猜呼著女嬰的身世,半晌過去,少年雖未得其解,卻還是將弱小無比的她抱回了家中。
「善兒?!你怎麼去個都城就撿了個女娃娃回來?!!!」
少年聽見眼前阿母的驚吒聲,既未害怕也未動怒,而是默默地將女嬰的玉玦拿起,在嗔怒的婦人面前晃了晃。
只見婦人一見此物,臉上的怒紋瞬間消去,她一改怒態嘴角默默揚起,一把麻力抓起了玉玦,裝模作樣道: 「唉,沒法子,如今總不能再將她給丟回去。」
「罷了,家裡再添個奴婢也不是什麼大問題,這女娃一個孤棄子,便喚”棄”吧!」
「是。」少年沉穩應道,他阿母的性子他是在孰悉不過了,要不是有那看起來貴重異常的玉,這女娃恐怕連踏進家門也無法。
少年望著懷中的女娃出神了一會,便用手指戳了戳她的臉頰,輕聲道: 「我名吳善,吳氏,單名一個善,而你,棄,望你能夠康健成長。」
從此刻開始,女嬰與少年的命運便緊緊的纏在一起,他們兩個誰也未曾料到,從今往後他們的人生也將隨著天下的局勢翻天覆地。
十三年過去,棄已從哭啼嬰孩轉變成體貼細緻的少女,她總是能清楚的記得吳善說過的每句喜歡,記得吳善討厭的每個事物,也只有她能夠令不苟言笑的吳善開展笑顏。
吳善本為名將之後,其吳氏家族代代相傳一把絕頂名劍,而這劍鋒利無比常人難以駕馭,唯獨吳善,吳氏之中唯一一位能夠揮劍自如,運使劍招的青年,為此他每日不曾懈怠專心習武,修習兵法之道,只為了有朝一日能夠立下戰功出人頭地。
原本這該是平淡美好的一年,但一場夜雨,伴隨著官兵的鐵甲聲,亂紛紛的踏平了吳氏的每座牆角,這年,吳家之長因謀害君王的空頭罪名被處死,吳家上下舉家逃到了楚國邊郊,過上了貧困艱難的生活,而這般大落之下,原本吳家的奴僕走的走,逃的逃,一家上下病的病,死的死,其慘狀幾乎如遭滅門般悽慘。
這樣艱險的困境,唯有她,唯有棄,堅定不移地留了下來,縱使她每日以淚洗面,為了吳家的大變心感哀戚,她依舊是留了下來。
正因如此,這樣堅定不移的信念致使吳善待她越發的好,甚至超過了原本主僕之間的界線,越過了主僕情誼,相知之情。
兩年過去,一樣的夜雨掃過了房舍的屋頂,發出振隆吵雜的轟隆聲,這次,棄不在如過往般害怕,過去只要夜間飄起雨點,她便會想起曾經的噩夢,想起那個一夜之間跌落深谷的吳家。
而今夜,眼前身姿精瘦壯實的吳善,令她忘了這一切不安,那英挺男子的容顏,露出了不同以往的羞澀,原本他沉穩的雙眸也多了七分蜜意,有如幽谷之下花開遍野。
一夜纏綿,兩人如膠似漆,互相許諾終生。
那年,棄十五歲,也是那年,她有了孩子,她與吳善的孩子。
秦王政二十五年,楚國被滅,棄在一片戰火下逃竄著,她懷中尚未滿月的孩子大聲哭啼,儘管嬰孩哭聲宏亮,卻也蓋不住難民的嘶聲叫喊,而吳善在混亂之中為了保全母子兩人,遭秦國高手重傷,這一戰下來吳善被迫與棄走散,兩人都未能知曉,這次分離將葬送他們的過往,葬送曾經的相許蜜意,曾經的同甘共苦。
子時之刻,冷風拍打在棄的背脊,她瘦骨如柴,襤褸似懸鶉,兩腳多傷痕,而她懷中緊抱不放的是性命垂危的嬰孩,她蜷縮在破敗不堪的房舍,周遭半點人影皆無,她不曉得她逃了多久,走了多久,只知道當她毫無力氣在行走之時,眼前的斷瓦殘舍成了她如今唯一的避難所。
她抬起頭,看見了今夜烏雲密布,她的腦中在此時閃過了這時數十年歲月的點滴,那是服侍吳氏的艱苦,服侍吳善的歡喜;那是往日生活的不易,往日相伴的甘飴。
她望著懷裡的孩子無聲流淚,心中不停打轉的是命懸一線的吳善,奄奄一息的孩子,還有那餓到骨子裡的慾望,痛到心坎裡的哀傷。
當她將所有念想集合梳整,一句簡單又難以接受的話語盤旋在棄的腦海。
“我不想死。”
她明白了,此刻她對於生的執念超過了懷裡的孩子,越過了思念吳善的情感,她無法接受她懷抱著這樣自私又殘忍的想法,在內心一陣糾結下,兩位看起來與她年紀相彷的少女無聲地出現了。
破屋裡一位青衣少女身披紫紗,挪動之間有如黑夜中嬌美的魅影,另一位身著綠衣身型比身旁的少女在嬌小許多。
「這都什麼爛差,竟讓你來這荒野破屋,還有這臭氣四溢的女娃,她不會是死了吧?」綠衣少女率先發話,從她口中透出的是難以親近的傲氣。
「你不想死,對吧?」青衣少女無視了身旁的綠衣少女,直白的對棄問道。
棄被這突如其來的美人一問,嚇得雙唇顫抖,眼眶驚淚,不敢多說。
「我給你一個選擇,是活,亦或—死。」青衣女子態度一轉,從原本優雅淡然的提問轉為冷冽刺骨的命令。
那天,在那寒風之中,棄選擇了死,她的心隨著親手扼殺地孩子永遠沉眠在了那個破屋,與此同時,末閣之中多了一位天資聰穎的女弟子—沫泣。
“莫留始末,泣止於此,從今日起無棄,無泣,唯留末泣,沫泣。”這便是青衣女子對她說過的最後一番話。
曾幾何時,她在末閣之中偶爾還會憶起那最無法接受的一夜,憶起那親手剝奪骨血的髒手,憶起那苟且偷生的自己,但這僅僅是在進入末閣的一個月間,一月之後,她再也不曾夢過那寒夜,夢過那奄奄一息的孩子,夢過她始終惦記的吳善。
現在孩子死了,吳善死了,他們都死在了楚國覆滅的那年,死在了沫泣的心底,原本該是這樣的,但在一場大雨滂沱的夏夜,那最熟悉的人影,最熟悉的劍芒,一聲不響的刺向了她塵封的過去。
她在某次任務中瞥見了他,瞥見那個曾經互許一生的男子—吳善。他手中握著名劍,肅穆的劍眉高高豎起,一劍揮過,劍指目標人頭落地,頓時天雷一響,一人突變六人,眨眼間的功夫,六人的身影便一同消失在了雨夜。
經此一別,沫泣慌了七日,悲了七日,她盡她全部的心力資源去打聽那名男子,只為了確認他真正的身分,數月過去,關於那名男子的背景,只得了個淺薄的消息。
他是羅網中的一名殺手,羅網,秦國最為龐大的殺手組織,其中以趙高為首領,培養了許多刺客精銳。
但,他並非普通殺手,而是羅網下的六劍奴,六劍奴之首,六劍奴是直屬於趙高的六位殺手,一人六體,六體一人,而羅網的每個殺手只有劍名,未有名字,這使得沫泣更加執著起了那名貌同吳善的男人。
從此刻開始,沫泣心中所想無非是見到那名男子,她曾以為她死了,死得透徹,連同她的心一起葬在了那間破屋,現在,那未能看清的虛影成為了她唯一的執念。她試了各種辦法,甚至勤勉出色的完成了任務,卻還是未能覓到一個能夠前往羅網,見到趙高,見到那名男子的機會。
這樣一籌莫展的日子一天天過去,兩年光陰轉瞬而過,執念未解的她卻是先等來一個驚天的消息。
水部備受關注的五靈玄同—芙蓉,其人因謀逆之罪而遭處死,而她便是當初的青衣少女。此事過後,取代芙蓉接受玄同之名的則是當初的綠衣女子,一位年近三十,身姿外貌卻如女孩般嬌小稚嫩的女子—白娦。
自從白娦接任五靈玄同,沫泣行事更加低調小心,在九天曦和的這兩年,她深刻的明白,這位看起來嬌小無害的女子才是最不該招惹的對象,只因得罪她的人,下場從來都不會好到哪去。
某次沫泣隨著白娦一同前往蘭荏堂交辦事務,她偶然間聽到了一位令長老”特別”關注的弟子。
「唉,老夫真真是放走了一個那麼好的美人,真是氣煞老夫!活了數十載,這機遇怎就那麼剛好的在唾手可得的地方給溜了,唉—唉—唉。」雲中君面容連連嘆氣,懊惱的對白娦自憤道。
「你說的那名瓏,我好似在長老的文卷上見過。」
「哦?!不妨說來聽聽!」
「呵,怎麼可能…許是我看錯了,那可是極密卷文,要不是長老傳我拿印,我也沒法瞧見,定是看錯了!看錯了!一介入門弟子怎可能會出現在密卷上,況且你這東藏西藏,對那什麼隆?還是壟?說的這般保密,難不成這其中…。」白娦眼睛瞇起像極了俏狐狸,她向雲中君略使臉色,想從她口中套出點什麼。
「嘖,白娦弟子,你何時對我如此沒個分寸,老夫問,你便答,這方為規矩!」
「雲中君大人,息怒息怒,想讓我多加留意,您還是得透點風聲給我才是個法子呀!」
「她非常人,僅此。」雲中君板著臉,半句都不願再多說,白娦見此態也是左耳進右耳出,掃興之下隨意應付後,便與沫泣離了這蘭荏堂。
數日後,沫泣得到了一個驚天消息,以及一個不可錯得的機遇。
先是娥皇將選拔優秀的弟子,一同前往位處咸陽的羅網死牢執行任務,再者,她遇見了那位特別的弟子,並且是在她得知前往咸陽宮消息後的不久。
沫泣一想到能夠確認男子的真身之時,那悲喜交雜的感情將她冰冷的心牆給融碎,她哭了,久違的再次落淚,她在剎那間終是變回了曾經的棄,那個淚啼不止的棄。
而這樣的她也被眼前容貌出塵的少女給撞見了,那次便是他們頭一次相見,也是往後這三月以來,名為友情之苗茁壯的開始。
與瓏月相處的這數月,她用了各種辦法摸清了這女孩,但,有那麼些瑣碎時光,會讓她放下各種算計心機,好好正面瓏月澄澈無比的紫眸,還有她那眸光中透出的溫柔堅定,她自己也未能料到,瓏月帶給她的影響,正悄悄的打開她心底塵封已久的某種情感。
三月過去,沫泣依舊是利用了瓏,前往了咸陽宮,而在那裡她終於得見記憶中的那抹溫影,她終於能探清,這些日子以來內心翻騰不止的不明心緒。
當任務接近尾聲之時,她見到了他,六劍奴之首—名劍真剛,那也是吳善,吳氏吳善。
那夜,那個短暫的會面,短暫到一把劍,一冷眸,便徹底讓她從過往清醒了過來,他是羅網真剛,而她是陰陽家沫泣,棄善兩字刻在他們的心中,善棄兩字成為他們的結果—他們早已捨去了過往。
這些結果對於沫泣來說並不陌生,過往數來,她的人生何嘗不是大起大落,只是這次,她沒想到一切迷霧散開後,心頭竟會如此空虛,又或者說,會如此如墜谷底一蹶不起。
曾經她懦弱的為了活下去選擇了陰陽家,而現在,她自己也不曉得了。
沫泣失神的走在陰陽家在咸陽宮的駐地裡,她曾想著若是左護法或長老對瓏月施用讀心術,那她之前對瓏月透露的那些消息也將引火自焚,但這些懲處對她來說早已變得可有可無。
此時失意的她聽見了白娦的話語聲,那陰冷又令人發毛的話意。
「明日起我們便正式回到九天曦和了,到時結果定讓大人滿意。」
「我早已安排好了,瓏她只要碰了我設計的密卷,上頭的咒法還有你的蠱毒,定會讓她變得比你的寵物還要乖巧。」
「天資優越又如何?到頭來還不是賤如相鼠,她一介凡人,早該了解這是我們之間永遠無法跨過的鴻溝。」
「呵呵呵,是,我自有辦法,鋒芒太甚的草民我是一個都不會放過的。」
沫泣聽了這番話,猶豫了一瞬,下一刻,她便稟了娥皇打算先回九天曦和。
那時的她心裡有歡喜,驚恐,感嘆,她歡喜瓏月在罪卷之刑後平安無事,驚恐白娦所做的決定,感嘆自己還能有一個機會,去守護住這些年來自己早已淡忘的東西。
一路快馬加鞭,她心急如火的趕回九天曦和,而這途中等待她的卻是一場死局。
夜風吹起,吳善手握細劍暗傷沫泣,他未殺她,而是餵她服下了某種丹藥,沫泣一技滄浪之水直接催化內力,讓掌中水珠化為冰氣打入吳善右肩。
吳善遭此一擊,驚的退了數步,沫泣也趁此時連忙遁走,一個時辰過去,沫泣回到了九天曦和找到了瓏月。
但,到了瓏月面前她才發現她的嘴已不聽使喚,她大聲一喊,殊不知,這從他嘴裡脫口而出的瓏字,竟是她最後一句道別。
在這短短數十年歲月,她犧牲了許多,跌倒了數次,而在最後她踏出的這步,踏入了再次為了某人付出的道路上,剎那間,沫泣心中早已熄滅的暖光,在她喊出瓏的名字時又重新燃起。
沫泣一生縱有遺憾,但在末路之下她依然覓見了曾經那位無愧於心的自己。
最後,她安靜的躺在了瓏的懷裡,沉沉睡去。
9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NUdXDVEC8u
*
末閣中堂下,一切聲響進了耳裡繞轉著,盤旋著,片刻,這些碎語又輕盪玄乎的飄走了。
如果,如果此刻世上同時發生了千萬種厄難,那這千萬種便如同刻在了我的心頭肉上,如果,如果眼前光陰百轉凝成了一滴珠淚,那這玲瓏淚珠便會泯沒我的一切情感。
“人生浮夢,夢醒細嚐,似是浮沫,似是霞光,回首一望,諸情流淌。”
此時心中塵封的某種力量,隨著不斷作用的情感正在慢慢被釋放,就只差那麼一點,這股躁動難安的力量便要破心而出。
「大司命大人,現在定論瓏弟子的罪刑是否言之過早?」
「哼,一向不問俗事的君房,難得出頭竟是來蹚這渾水?」
「白娦弟子,此言差矣,這般要緊大事怎可與俗事相提並論。」
「湘夫人長老得知沫泣遭難的消息後是惋惜不已,所以,這瓏死罪難逃,並且我將親手處決,否則我也不必這樣趕路回來。」
「且慢。」
「君房,你今日對我挺上心的啊?」
「呵,可不是嗎?總覺得,白娦此次奔波回來急躁的很,身上也染了不少風塵。」
「多謝君房關切。」
剎那,細瑣的冰片劃過了髮絲,劃過了額頭,一陣刺痛默默地撓搔著肌膚。
「君房!你膽敢…?!」
「白娦弟子,大司命大人的指頭都未動半分,你便這般搶著施術處刑,就怕讓人有話可說。」
「呵,好呀!君房!想不到你除了煉丹,口舌功夫也是精進的很啊!」
「哼!多說無益!」
我呆愣地望著眼前無休止的爭論,他們不斷開合的嘴唇像蛾子振展的翅,一張一合似離我越來越遠,頓時,一道冷冽的殺氣掃過,白娦指尖纏繞的細綢上匯聚了內力,猛地朝著喉間突刺而來。
「何人放肆。」
忽地,一語冰冷霸道的震攝四方,緊隨其後的強勁氣息化作紫氣游龍直搗中堂,龍游之氣撞開了圍觀的弟子,斷去了一縷鎖喉的綢緞,最後於空盤旋三圈,直化作了一線紫芒融入臉上的冰清面紗。
“星魂…。”
抬眸一看,人群盡頭傲視八方的少年在眨眼間瞬步而來,他素手一揮,劍眉豎起,不到片刻,末閣中堂下無關人等皆恭敬的退去,僅剩數名長老及五靈玄同肅穆以待。
「細枝末節,我已聽聞。」
「白娦,聽說你此次在死牢中表現出色。」星魂薄唇一勾,眼中盡是我看不明的情緒。
「多謝左護法大人!」白娦收起了方才的狠戾,露出笑顏恭敬行禮。
「可不是人人都能掌握水部祕術,更別提幻形之法。」
「大人言重了,白娦在大人面前只是上不了臺面的小弟子,若能得大人抬指垂憐,白娦夕死可矣。」
「哦?既然你有此心,那本座也不藏掖什麼,不過…。」
「大人儘管吩咐,白娦定當竭力完成!」
「呵,如此甚好。」
「呈上來。」星魂語畢不久,兩名弟子便恭敬的抬著青銅大箱快步而來,只見他素手一揮以內力開啟箱子,兩指微勾,厚重的咒卷便輕巧的飛入他的掌中。
「這些是近期堆置的水部密卷,聽聞鮮少有人能破咒卷上的術法,此刻我掌中之卷乃是湘夫人特意呈稟,看在你頗有實力的份上,我便賜你機會讓你展露身手,何如?」
「這…。」
「大人,我…。」看著白娦微蹙的眉間,稍有為難的樣子,心中也未能感受到任何快意,眼下內心醞釀的未明情緒與力量,好似在等待什麼一舉傾倒而出,而那份能解開一切枷鎖的關鍵,到了現在卻依然遲遲未能出現。
「若你做不到…。」
「白娦願傾力一試!」
我無聲地看著白娦接下文卷,晶瑩的汗珠在她的小臉上不斷浮出,當她欲解卷上咒法的那刻,一陣哀鳴隨著她施法的瞬間大聲迸出。
「怎…怎麼可…可能?!」白娦瞪大眼珠,顫抖轉身瞪著我,兩眼對視間,她那眸中不解又怨惱的怒火就像在示意,示意她對跪在此地的我,抱有著多大的血海深仇。
「以我所觀,你施術的瞬間,咒法上的術法氣息似乎與你的內力互相感應啊?你說呢,白娦。」
「左護法大人,弟子君房,方才瞧著白娦弟子施法模樣,察覺了某個微末的氣息,倒是讓我想起了近來金部的一件丹藥遺失。」
「說。」
「因為此丹藥平凡且不常使用,故此事並未上達兩大護法,最後只以看管不濟的罪刑懲處了數名守堂弟子。」
「此丹名為滯息丹,其本除了阻礙內息舒通,及干擾內功運用外便無任何作用,平常在測試弟子內力抑或修練之時會被拿出,而此丹有個特性,若它在未被服下的狀態,且在三寸以內有任何內力擾動,丹藥本身便會散出清氣,反之,若丹藥遭人服下,十二時辰內若服藥之人強行運功,抑或從外部接觸龐大內力,那麼此丹的藥性便會使得無處通行的內力搗毀筋脈,傷其五臟。若誰不幸遭遇了後者的狀況,那此人性命不到一盞茶的功夫便會一命嗚呼。而白娦弟子方才運功之時,身上便出現了清氣,故此君房特意稟明大人。」
當君房解釋完畢,思緒開始以前所未見的速度飛快運轉,一時間,他們的談話入了耳,失了聲音,丟了意思,沫泣之死的癥結就差那麼一點便要霧散雲開。
「呵,你說你名為君房?」
「是。」
「那麼君房,你適才說的滯息丹,能否在人死後在其身上尋得任何丹藥的痕跡?」
「若是一兩個時辰之內,那應當可以尋得蛛絲馬跡。」
「大人!大人,那術法…咒卷的術法我快要解開了!可否請大人先替白娦…。」
「君房,去瞧一瞧瓏懷中的弟子,體內是否有滯息丹殘留,抑或丹藥作用的痕跡,白娦,將你身上的滯息丹給本座呈上來。」
「左護法大人,沫泣弟子身上確實有著滯息丹痕跡,她的傷估計是服用滯息丹,再加上短時間大量內力湧入其身,才導致她的身亡。」
「左護法大人?!不是的…我是遭人構陷,我,我並無什麼滯息丹!」
「白娦觸犯陰陽家規條,栽贓,暗害,偷盜,三罪加總,罪刑重大,既然今日你構陷瓏弟子,那便讓瓏弟子親自處刑。」
耳邊吵雜了一陣後,空氣突然安靜下來,最後進了耳裡,入了心坎的沉穩輕語,是由冰清面紗間接傳入腦中的星魂之聲。
“瓏,我知曉你這傻子總喜以德抱怨,所以此次我未取賤婦性命,剩下的罪刑便由你親自發落,她的生殺去留我不過問,只是,你一旦做了決定,就無可回頭了。”
眼下我非驚詫在星魂面紗上暗施的傳心術法,也非動容於星魂替我著想的不殺抉擇,在這瞬間,心頭上一直未能散去的那片陰霾,那悲局的真相,終於霧散雲開,一覽無疑,霎那,那股從頭到尾躁動不安的力量佔據腦海,破開桎梏,迸發而出。
我輕輕的放下了沫泣,堅然站起,一雙冷眼掃過四周,最後冷澈的目光停落在跌坐於地的白娦身上。
她眼中是憤恨,不可置信,驚恐不已,她衣裳凌亂破爛似被氣刃削過,身軀上也染了大片暈紅,觸目驚心,縱使如此,縱使她如今狼狽落難,罪刑揭發,心海竟無為此起過半片漣漪。
「一切,都是你。」我無情一問,心中對自己語中的冰冷毫不在意。
「是你,是你害我,是你設計我,是你於罪卷上施法還下了某種蠱毒,這些惡意都是你,這些殘酷無比的源頭都有你。」
「呵…呵呵,哈哈哈!是,是我又如何?你別自以為是了,你全身上下就只因你那稍微出頭的運氣,才能保你這條賤命!如若不是左護法大人突出此意,你早就死在我手!」
「你原本的目的不只是殺了我,還打算殺了沫泣,對吧?蠱毒會使人形如傀儡任人操弄,而你,打從一開始便未想遵照那人的命令行事,我想了許久,當我從沫泣的一生中輾轉醒來,我便明白了你從頭到尾心底盤算的計謀。」
「你!你怎會知曉蠱毒之事?!」白娦聞言,臉上失了怒氣,取而代之的是驚慌失措的神情。
「假意承接那暗處之人的命令是你,暗傷沫泣的吳善也是你,餵沫泣服下滯息丹的更是你,在今夜咸陽宮,你是故意讓沫泣聽見密談的對吧?還有三月前的五靈競鬥,當我救治金部弟子之時,也是你從旁窺得我使用的術法,我說的可對?」
白娦汗如雨下的小臉,在眨眼間褪下了所有顏色,只留一層死灰的臉皮,看著她驚嚇失語的模樣,心中便明白她這是全數默認了。
「只有這樣,你才能一箭雙雕,想來當初那些路過的弟子,亦都是妳的刻意安排,如若長老們用了讀心術,也揭不出你的什麼罪名來,畢竟你早已知曉結果,你只需隨意交代弟子該去那些地方,而什麼都不曉的他們,便會恰好撞見將我定罪的事實。」
「你的怨與恨衝著我來便罷了,為何?為何你還要奪走旁人的性命?」
「呵…呵呵,都到這種時候了?都到這種時候了?!你依然說著這種冠冕堂皇的話,你只是怨我!恨我!因為我陷害你!因為我是五靈玄同!你高攀不起的存在!你別偽善的拿沫泣來當擋箭牌,我衝著你去又如何?對著沫泣又如何?從始至終,你這懦弱鼠輩只會一昧縱容,一昧原諒,到頭來受傷的只會是你自己,還有因你的蠢笨喪命的可憐之人!」
「......」
「沒錯,你說對了一件事。」我一步,兩步,往白娦走去,她見我慢悠悠的走來,身子瑟縮不停的向後爬離。
「沫泣因我而亡,小五因我而亡,他們都為了我丟了性命。」
「你知道嗎?」我失神的問著眼前惶恐的白娦,接下來出口的每字每句,彷彿似我本心亦非我本心,心中不明的思緒如同倒入海中的一杯淡水,早已分不清彼此的界線。
「當人們的惡意刺向我,傷害我,構陷我,甚至是你,是你要我的命,這些…這些我都能讓時間去寬恕,去撫平你們帶來的傷害,只因為我了解你們身上背負的太重太難,只因為你們被各種阻礙,各種執念,迷了本心,失了魂魄,斷了善念。」
「直到方才,我更是徹底明白,刀子劃在他人的肉上,自己絲毫未敢半分苦疼,這便是人,因彼此無法相互理解,互有共感,最後爭鬥而生,怨憤而活,傷了他人,亦損了自己。」
「怎,怎麼?說的,說的那麼好聽,既,既然你不想動手,哈,哈哈,你,你便…滾到一旁哭啼去,別…別在這惹眼!」
我無視了白娦的話語,終於走到她的面前,以居高臨下之態強硬的拽起她的手腕,冷言道:「你方才說我有著出頭的運氣?是,出頭的運氣?抑或災星的氣運?你根本不曉得這出頭運氣的背後,帶來的是什麼。」
「你曾渴到跪伏於地,雙手爛泥的卑微捧起眼前混濁水窪的水,感恩喝下嗎?你曾餓到啃食長滿生蛆的腐肉,咬過沾滿鮮血的碎布,只為了能夠止住生不如死的飢餓感嗎?」
「當我因通心之苦碎心裂魂時,你在背後嗤笑鄙視,當我身陷他人一生感同身受時,你在一旁得意自己的惡行惡舉。」
「世人皆苦,無一例外,任你貴為權富,賤如溝鼠,終逃不開個苦字,而人善於比較,自此有了高與低,有了長與短,但世人總疏忽了一件事,存在那裡的東西很單純,全權是因眼光不同了,帶來的感受便有了區分。」
「若是人皆能將心比心,世上仇惡少了,尊重多了,悲憤少了,歡喜多了。」
「你放開我?!一介草民拿開你的髒手!!!」白娦見我未有動作,開始胡亂掙扎起來,她這麼一鬧,心裡同樣波瀾未起,我無視她的話語重重施力,像似折斷筷子般的握緊了她脆弱的手腕,一時間她尖聲哀號未有停止。
「說了那麼多,我就一句明白話相贈。」
「你動我便罷了,可你偏生動到了我護著,守著之人,我能忍受苦痛,通人心意,但她…她憑什麼需要去承受你的這些。」
「啊啊啊啊!哈!哈…哈哈,你,你!你!我不信你!啊!會殺了我?!!!!」
「是,我不會殺你。」
我大力甩開白娦的手,她身子一個不穩跌摔在地,看著咬牙未語的白娦,我伸出了手,頓時體內那股純粹孰悉的力量盤旋在了掌上。
「殺了你,沫泣不會回來,悲劇也無法改寫,但,至少,我能讓你親身感受在你眼中視為卑賤的存在,在你口中蔑視不屑的草芥,經歷了多少苦難,流過了多少淚水。」
「白娦,只因為你未曾見過黑夜,便可在白日中肆意嘲弄蔑視黑夜的一切。」
「現在我會讓你明白,何謂切膚之痛,入骨之感。」語畢,雙手清氣四溢,蒼翠耀光綻放於掌中術法,我不曉得術法的名字,但我明白,就在此刻,沫泣這一生的種種,不論是思想,感情,經歷,均無例外傾覆白娦嬌弱的心海裡。
「如若我說了這麼多你依然不懂,那我便用你的意思,明白的說與你聽。」我蹲下身子,將嘴輕靠在了白娦的耳旁。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若你以力量斷人貴賤,那我便以牙還牙全數奉還。」語落,我堅定站起再未回頭。
當這夜悲劇過後,我做了一個夢,夢中有一名男子,我看不清他的臉,我只知道我離他很近很近,他身上纏繞耀眼奪目的紫焰,隨著他出口的最後一句話,焚灼了他模糊的右臉。
他說:「那下次,便換你守護我了。」
夢醒之後,心中未起太大的波瀾,唯一讓我在意的便是那守護二字,不論如何,這次我定會守好重要之物,那怕魂飛魄散,身敗體殘。
翌日,過往塵埃落定,水部雖少了一個白娦,雲中君身旁卻多了個癡傻懦弱的女娃,並且雲中君還相當中意她,想都不用想,白娦自那夜後失了神智,行動舉止一會瘋癲,一會安靜,她失去了過往的跋扈,變成了任人玩弄的傻子。
這間接證實了,那夜的術法使人跟死了沒兩樣,其人不是丟失魂魄,瘋魔瘋樣,就是神智不清,幼兒心智。
而我,我現在身處望疏殿,左前側的星魂正座於席,安靜的品茗茶水,右前側的月神端莊佇立,她眼前的薄紗飄動,讓人猜不透她的意圖。
片刻,月神淺淺一笑,故作溫柔說:「瓏可決定好了?」
「是辰極宮?抑或望疏殿?」月神平淡的問著,語中早已透出了十拿九穩的自信。
我頓了片刻,瞥了一眼未做表示的星魂,答道: 「是,月神大人,瓏心中已有答案。」
ns 15.158.61.42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