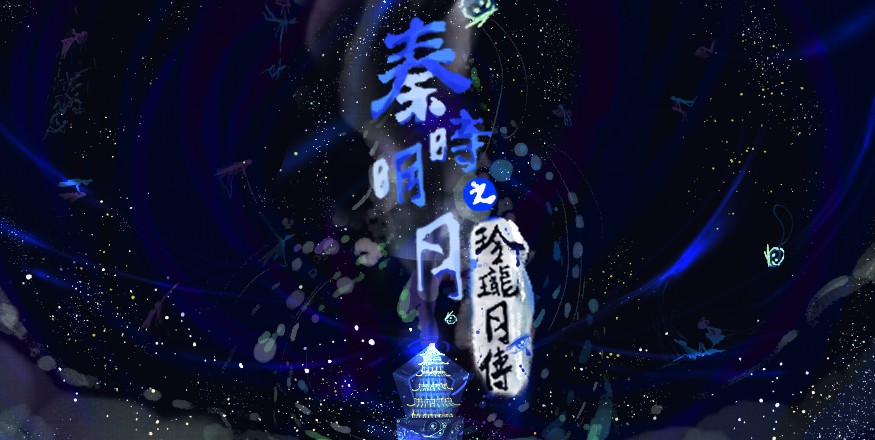在甘羅前往趙國的前一日,甘家正廳中聚集了甘氏親族,一眼望去,長幼相依盡數圍繞在少年的周圍。
眼下甘氏親族全都齊聚甘家宅邸,為甘羅送別,因為此去路途遙遠,使命重大。
這是一場賭注,是甘羅為名為利,為甘氏,更是為了他始終記掛於心的大秦國土。
我與甘羅,乃至甘家上下,無不明白此趟出始趙國背後代表的意義。
使節不同於尋常官吏,使節受命於君王,持通關符節在外遊說,一言一行要是多幾寸少幾分,便是禍害家國。
甘羅這一去若談的好,小為光宗耀祖,榮耀加身,大為豐功效國,青史留名;反之,談不好, 臭名一世,喪權辱國,便如汙泥一般玷汙了甘氏多年的名望與功勞也不為過。
但是,就在這歡鬧目送甘羅的人群中,卻唯獨缺了甘羅父母與甘櫟的身影。
甘櫟前些日子因故趕往雍城,而甘羅的父母這幾日卻是為了遊說趙王之事與甘羅起了口舌,父母子三人的關係已經冷了好幾日了。
此刻,站在少年旁邊的我,不盡受眾人灼熱的視線給影響,感到些許不自在與害臊。
「今日別過,便要啟程前往邊地關口了。」
甘羅聽了我的感慨,藍眸中的堅定絲毫未減,他揚起嘴角,意氣風發的接受了甘家族長的祝福與囑咐,依依拜別甘家的血親,最後在眾人的擁戴下,踏出了正廳的大門。
當甘羅走沒幾步,他臉上的自信與從容漸漸散去,留下一抹陰沉。
忽然間,我突然從後方感受到一股強烈的視線,回頭一望,原來是甘羅的父母站在宅院的角落。
仔細看去,他們好似想衝上來,前腳剛踏出卻又楞是停在了原地,總覺得甘羅娘親的手中捧了某塊布囊,布囊又好像被緊緊搓弄數次,變得有些狼狽。
「羅兒,你等等。」
「出了秦國後往趙國的路可是顛頗難行,路途遙遠。既然今日是最後一日留在秦國,你要不先跟爹娘好好道個別再走? 」
我話音剛落,甘羅原本健疾的步伐驟然停留在原地,他默默攥緊雙拳,深吸一口氣說: 「多留一刻,便是讓他們多操心一分。」
甘羅雖語氣堅定,但他微微顫抖的眉間卻出賣了他,而他拼命壓抑的龐大情感,也毫無遺漏的淌入我的心海。
自數十日前,甘羅父母知曉甘羅將前往趙國遊說趙王,當天他們倆便花了半日與甘羅深談。
甘羅的娘親怒目以對,認為羅兒雖聰慧過人,但閱歷尚有不足,難承受此重任,若稍有不慎,不只葬送了甘家,更是葬送了他自己。而其父親,在談話途中雖無多言幾句,但平日開朗樸實的一張臉,卻黑了大半悶沉整天。
不過,無論父母子三人談心的結果如何,王令既出,便無理由在回絕。
這數十日,直到方才在正廳上,甘羅與他的爹娘都是冷冷的,他們甚至也未來向甘羅送行。此刻,就是甘家上下百般看好,就唯獨他的父母,特別是他的母親著實不肯點頭認同。
畢竟,何人不曉,何人不知,這一去前途未卜,即便是少年天才,也必須越過千山萬水到那異地趙國。
可不管怎樣,即便他們三人再尷尬,這離開故土遠去他鄉的最後一面終是要見的,我心想那怕一眼也好,至少讓彼此能夠留個念想。
「你走之前至少再看父母一眼,或者好好道別,如此也能讓這漫漫長路走的平坦些。」我再次勸著甘羅,卻不想他聽聞後,欲再次邁開腳步離去。
我一看他這焦慮逃避的模樣,心中徒生不滿,大聲一喝,就是擋在他的前頭道:「這個節骨眼你還逞什麼強,賭什麼氣,那個一向有一說一,勇敢果決的羅兒去哪了?! 」我猛力拍了甘羅的後背,即便我深知他的背後只會感覺微風輕撫,也希望能以言語激將,動作相輔令他鼓起勇氣,令他正視他這幾日與父母淡漠相處,背後藏有的意義。
「縱使爹娘與你意見相左,你自己的感受呢?!」
「就算意見相左,你便不愛他們了嗎?!你若為了賭氣,錯過內心真正想做的事,與你真正的心意背道而馳。一向看透人心的羅兒,自信又傲氣的甘羅,不會逃避這樣單純的道理!」
剎那,甘羅眉頭蹙起,腳步一抬,頭也不回的瘋狂奔跑起來。
「喂!喂?!羅兒,你等等! 」我驚詫大喊,身子也被甘羅突如其來的舉動,給連帶拖了一段距離。
眼下,他就差沒幾步便要踏出甘家宅院,我心急之下,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拼命胡亂大喊。
「夫人!」
「夫人昏倒了?!」
甘羅飛快的身影便隨著我的嘶喊,驚顫的停在了門前半吋位置。
甘羅原本的冷俊的容顏蒙上了焚心的惶恐,他猛然回首,看見的是他爹娘朝他急奔而來,而我這個始作俑者,此刻小聲的咕噥幾句”好像……是我看錯了”便默默的退離到甘羅的視線外。
「傻孩子! 」
甘羅的娘親一聲真切又焦苦的呼喚,隨著一番急促抱擁,將嬌小的甘羅擁入她厚實的懷中。
「你這一走一停,是存心要急死為娘的! 」
眼看甘羅的娘親憤怒的罵罵咧咧,摟著甘羅的兩臂卻是越摟越緊,而甘羅受眼前婦人大力緊摟,嬌小的身軀不由得輕輕顫抖。
一時間看他們母強擁子的景象,心裡高懸的那顆心終於漸漸地放了下來。這母子二人心堅如鐵,性倔如石。就是這樣堅強不屈的二人,都不肯有一人敢於突破尷尬的現狀,放下身段。
「羅兒心意已決,不悔當初前往咸陽宮拜見大王,更不悔接下遊說趙王的王令。」甘羅原本不安的藍眸,添上了幾許不服氣的堅持。
我看他這樣子,心裡頓時明白,他又硬是把話題踩在兩人心坎的窟窿上了。
剎那,我原本心中暗想母子道別的溫馨情景,在甘羅強硬的態度下,又被無情打碎。
甘羅的母親聞言,緩緩放開了環擁甘羅的雙臂,並抓握著甘羅的雙肩,與甘羅正面對視。
我在一旁悄悄觀望,只見她平常嚴肅的眉眼無聲的消散,她的髮間多了數根白絲,眼皮有些浮腫,臉上是乾了大半的淚痕,還有,那好似多日未眠而萌生的疲憊臉紋,無序的遍佈在她的愁容上。
看來這幾日她是為甘羅操碎了心,可甘羅,又何嘗不是如此。
他這幾日的茶飯不食,睡不安穩,書簡生灰,閉門不出,連他平日精心把玩,勤奮打理的甘茂傀儡,也未在看上一眼,這些心悶憂苦的模樣,無不是被一旁的我給看在眼裡。
他們二人當真是母子,都是一模一樣的硬脾氣,兩兩相碰是互不相讓,可是,即使如此,他們終究是母子,我明白這份血脈親情,非是簡單的幾句爭吵能夠切斷。
「羅兒。」
當我以為他們二人又要再次冷言爭執,卻不想甘羅母親的眼裡浮出血絲,眨眼間,紅了眼,淚珠無聲落下,一句羅兒,聲聲都是為母的捨不得與憂愁。
「娘知道,娘親早就知道了,從四年前開始,從那次大病以後,娘知道,你不會在用欽羨的目光望著路上嬉鬧的孩童;娘知道,你不會在刻意收斂鋒芒,在同儕間避而不談家國大事;娘更知道,你比以前更加開朗更加勇敢,只是……只是娘。」
「只是娘什麼都知道,知道你心懷大志為家為國,知道你與你的甘櫟叔父瞞著娘親,不敢跟娘親提起此事,這樣的娘親,這樣的娘親卻唯獨不曉得自己該抱持何等心態來送你。」
「身為大秦人,娘會恭敬送你,為甘氏,娘會歡喜送你,可,可唯獨娘,唯獨以娘親的身分,娘是含淚欲……送……且相依,青山……萬里……隔兩心。」
甘羅的娘親低鳴顫語,眼淚像是止不住的水簾流淌而下,但無論她的衣襟被沾濕了幾分,她始終強忍著發顫的氣音,連一聲哭號都為有過半點。
我不禁被她淒苦的模樣所感,久違的再次落下了淚水,而這些淚水無聲無影,卻默默的鼓動於心,心中似有什麼正要甦醒。
甘羅的娘親說道一半,將方才的布囊給小心打開,只看那布囊中是一包酸梅乾,一枝甘家院內的櫟樹枝。
「趙國路程顛頗,這是娘親手做的酸梅,路上乏了,疲了吃幾顆,這櫟樹枝你是最熟悉不過的,想當初你……。」
只看滿臉憂容的婦人擦去淚液,輕聲柔語的為甘羅慢慢講解,說著說著,我彷彿能看見甘羅的孩提之時,想到他過去一人玩耍,閱書,與娘親相依的模樣。
一想到這,我忍住了哽咽,不敢發出任何一點聲音,來打擾眼前母子的道別。
半晌,二人的眼眶都紅了,其中一人哭了再擦去淚水,另一人紅著眼卻始終忍住了淚,唯獨甘羅的父親靜靜的看著二人。他的臉色雖稱不上憂愁,卻也未有笑顏,他從頭到尾,只是將厚實的掌心輕放在身下蹲跪的婦人肩上,一刻也未曾離開。
「甘氏,羅之名,是盼你能抓住你所願的一切,能夠網羅住你的理想,若說玉奴是指你的出生偶得的玲瓏碧玉,那麼羅之名,便是願你能夠把握住機遇,能夠把握你所珍視的一切,而羅兒,羅兒從始至終,不論是傀儡技藝,書典禮章,只要是你所求,你所愛,無一不是勇於追求,盡心對待。」
「羅兒,你現在只要記住,爹娘不認同你,是為你,如今,爹娘尊重你的選擇,亦是為你。爹娘不允你,非是羅兒不好,只是世道機巧,吉凶同域。如今為娘該說的都說了,若羅兒依然心有明路,那我這做娘親的,自然不該當你的擋路石,不管羅兒如何做,只要不愧對自己,不違背天道義理,娘都願意尊重你。倘若今日你能記住娘說的這些,於我們而言便夠了。」
「甘羅,甘羅在娘心中,永遠是最棒的。」
母子相擁許久,一旁始終未有動作的甘羅父親突然輕拍了甘羅娘親的肩膀,而她受此輕拍好似意會到了什麼,我看著他們彼此對視了一瞬,兩人朝同一個方向看去。
我尋著他們目光一看,竟是去了雍城的甘櫟,默默的站在大門遠處看著這一切。
「羅……。」我本想出口,告訴羅兒這個驚喜,可仔細一想,我還是等甘羅的父母的反應,再做打算。
只見甘羅的父母簡短的叮嚀幾句,便依依不捨的目送他離開。出了宅院,甘羅馬上便注意到了駕馬而來的甘櫟。
寬敞的行道上綠木蔥蔥,甘櫟默默地靠再他身旁黑馬腹部上。他一身米色長袍,腰間系上的暗靛色腰帶,遠遠看去身型修長的令人差點便要認不出來。
甘羅看見甘櫟的瞬間,小心拿好方才他娘親贈與的包裹,快步的走到甘櫟的面前。這時剛剛才忍住淚水的他,鼻頭微微抽搐,眼中盈滿的淚水看著差點便要落了下來。
我看著甘櫟一臉疲憊,一身素淨米色大袍沾了些許沙土,儘管他此刻的衣著打扮,給人感覺嚴肅不少,可他眼珠子裡蘊藏的無不是欣慰與愛憐。
甘櫟看見甘羅來到面前,身子離開馬腹,緩緩蹲下凝視著甘羅,一聲玉奴出口,就是少有的語重心長。
「小玉奴,自你娘生你,再有人登門贈玉;自我見了你,再注意到你那雙與眾不同的湛眸,我便知曉,你此生必定不凡。」甘櫟說罷,他臉上難得嚴肅的神情,沉穩的令人有些陌生。
半晌過去,甘櫟恢復往常愉快的模樣,他勾起嘴角,寬慰的淺笑,道:「男子漢多做少言,來。」說罷,立即從背後掏出了一個精巧的劍鞘,劍鞘古樸,鞘身上頭刻有玄鳥獸文。他嫻熟地拔出鞘中物,定睛一看,是一柄陳舊卻鋒利異常的匕首。
「你娘親會擔心不是沒有原因的,都說趙王意怒,性子衝動,即便你說服趙王,這趙國路程顛頗,難免不會碰上江湖惡人,山賊襲擾。縱使路途有有秦兵護送,遇上不懷好意的武林人士,又恐怕出了什麼差池。」
「不過,我對玉奴的運氣可是抱有極大信心的,畢竟是生遇靈玉,大病不死,少年天才,一鳴驚人。」甘櫟說著說著。臉上的倦容隨著他真切的話語漸漸消散。
「此匕首名為玄桑,劍身年古,卻非凡品,叔父日日攜配於身,你便把玄桑當作是叔父,好替我們叔姪二人彼此留的一個念想,若真遇到甚麼事,亮出凶器當可擋著幾分。」
此時甘羅不吭聲的聽甘櫟說罷,如過去一般未立馬將甘櫟手中的貴物收下,反而捧緊了懷中布囊,躊躇了半刻,才忍著淚水,強裝鎮定的顫聲,道: 「叔父今日不是早該趕往雍城,若是因替我送行而耽擱正事,那就真本末倒置了。」
「正事哪有我的好玉奴重要!」
眼前甘羅與甘櫟相談的景象,不禁又聯想想到當初兩人閒談時,甘羅總是一本正經的說了不少,而相較之下的甘櫟則是一臉輕鬆,一點叔父樣也沒有,叔姪兩人每每相見都是樂活的氣氛。
「傻玉奴,叔父雖喪妻無子,卻還有你這個好姪兒,你親手雕的祖父傀儡,裡頭蘊含的是剛烈且炙熱的抱負。我的玉奴,我的甘羅,為了甘氏,甘家,無一刻懈怠;為了故土,秦國,亦奮不顧身。」
「甘羅,叔父一生唯一念想的便是甘氏興榮,可......。」
甘櫟話還未說完,便被甘羅突然的擁抱給打斷。甘羅緊緊地摟著甘櫟的脖頸,這有違他平常作風親暱的模樣,又是讓一旁的我看的再次恍惚起來。此次別離是孤注一擲,甘羅若能夠敞開心胸好好道別,也算是對得起他心中對家人的真心真意。
前有至親父母道別,後有的亦師亦友的叔父相送,甘羅他忍了一路上的眼淚,終於還是從他眼角旁悄悄滑落。
「是叔父教我傀儡戲法,是叔父教我誦讀爾雅,叔父,叔父待我,便如雕磨傀儡,一刻一畫真心實意。甘羅答應叔父,甘羅此去定會戴功而歸,決不負甘家,不負先祖與祖父! 」
甘羅急切喊著,將頭栽進了甘櫟的喉頸旁,剎那,甘櫟肩頭的衣料染上淚漬鼻液,他看著甘羅難得親暱之舉,眼眸低垂,抱緊甘羅許久,方才淡然道: 「等你戴功而歸,叔父便教你之前從未學過的兩件事,這兩件事受用一生有益無壞。」
甘羅聽聞甘櫟要教他,突然離開了甘櫟的臂膀,兩眼發光的向甘櫟急促問道: 「何事?! 」
甘羅現在的模樣是一把鼻涕一把淚,又是把好奇心兩大字印在了臉上,讓人看了不知該哭還該笑。
「等你回來,叔父再告訴你。」甘櫟笑著,將鋒利的匕首收入劍鞘後,俐落地塞進了甘羅的布囊裡頭。
「一言為定?」甘羅抓著甘櫟的手臂急促問道,他藍眸中是藏不住的欣喜與堅定。
甘櫟靜默凝視甘羅好一會後,才淺笑答道:「一言為定。」隨後甘櫟一個起身,匆匆地拍去身上的塵土,與甘羅鄭重道別。
甘羅見到甘櫟以正禮拱手向他拜別,方才哭紅鼻子的模樣迅速收斂,眨眼間,就是整理好衣容,堅毅的向甘櫟回禮拜別。
兩兩別過,該正經地拜別禮都完了後,甘羅看著他留在甘櫟肩頭上的一抹水痕,又是不好意思的笑了幾聲,想幫甘櫟整理乾淨。
而甘櫟看起來沒想讓甘羅多待幾刻,他往甘羅背後重重一拍,一句"玉奴,我等你好消息",便上身手迅捷的躍上馬,頭也不回的駕馬速奔離去。
甘羅望著甘櫟逐漸消失在天邊的身影,擦乾了淚痕,眼中閃爍著堅定的光輝,嘴角揚起自信的笑容,朝我說: 「瓏兒,我們走。」
我愣了半刻,揚起嘴角,滿足應道: 「嗯。」
18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tAPvpDwun5
*
18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huwKSJsbuM
過了十日,顛了一路的車,吃了不少荒涼風沙,終於趕上時辰抵達了趙國邊境。
在這漫漫長路上,途經從重重關隘,遇上各種難題,甘羅皆不是以才智服人,以理相爭,方才順利到達了目的地。
我在旁是沒少看到世間的人情冷暖,什麼剛要上路認為甘羅是黃口小兒,便耍賴敲詐的,什麼走到半路,夜裡狼嚎鬼叫此起彼落,說是鬧了鬼靈妖魔的,更有的,就是流人賊子想偷搶護送車隊,又或者為了吃食互相殘殺的。
短短十日,我好像把這個世道的難處與好處都看了一遍,不論好壞,這些經歷讓我更加珍惜當下每寸光陰。
本來……是該這樣的。
「攻打燕國! 」
「不是說好只是為了讓張唐平安通過趙國嗎?!」
我不可置信地盯著甘羅,著實不敢想像眼前冷靜到有些令人發寒的少年,最終的目的竟是連趙攻燕,而非當初大秦說好的聯燕攻趙。
日正當頭,趙國國都邯鄲二十里外,數隻聲勢浩大的趙國車隊與秦國送禮的車隊依序會合,此刻的甘羅端正地坐在趙悼襄王準備的馬車裡頭,馬車裡雖寬敞舒適,氣氛卻是冷到冰點。
甘羅的藍眸冷冷地落在杯中茶水上,他白皙的素指在桌上無聲游移,寫出來的東西卻令人難以接受。
"你可知你現在所說多麼的荒唐? "
"戰國時期,諸侯割據土地,互相爭鬥,當初秦國欲聯燕攻趙,也未見你反應如此激烈。眼下只不過是變換了目標,你又何故鬧騰。
甘羅一語中的點出了我的矛盾,頓時,腦中劇鳴響動,兩個一大一小的少女身影掠過腦海。
那是一抹溫暖的橙色與面帶淚液的容顏,在這瞬間心中如遭風暴席捲,我失神剎那,硬是將欲衝破枷鎖的混亂情緒與記憶給壓了下去。
我知道,如若此時放任這股力量,那麼我恐怕又會再次失去意識沉沉睡去。
數年以來,我又何嘗沒少聽甘羅談論諸國相爭蠶食。各國戰爭在亂世乃常況,但我想,任何人都沒有理由把這些悲劇視為天經地義。
在前往趙國的路上,我看見了數不清的人群,他們眼神渙散,滿臉污漬沙土,懸鶉百結,光著長滿厚繭的腳無家可歸的四處遊走,不知去向何方。
當我問了甘羅,他只是習以為常的說,戰後的流民因各種原因逃離了原來的住所,便得無家可歸,無處可留。
我始終記得,流民群中有幾人趁半夜時偷偷靠近車馬,只為了想偷點吃食。他們各個肌膚貼附著骨頭,眼中透出的意圖,是為了生存就能不顧一切的人。
那時他們剛要下手,卻被甘羅撞見,甘羅未與護送的將軍告發流民偷竊的行徑,也未當下分發吃食給他們,而是讓兵士他們給驅趕出去。那夜過後,當車隊即將啟程,甘羅則悄悄的在露宿地方的不遠處附近,留下了一些乾糧與水,便繼續前往趙國。
當我目睹了隨波逐流的艱苦百姓,我更是難以想像,若秦國聯趙攻燕,那會是多麼可怕的情景。各方諸侯擔憂未能攻下他人土地;各方將士害怕未能殺敵爭功;各方妻小恐懼夫兒未能平安歸家。
當思慮來回打轉千遍,我才赫然察覺一件令人感到恐懼的事實。
"我也許根本就不明白,秦國一統六國的代價到底是何等龐大。一統的結果是幸,亦不幸,對大秦而言,對甘羅而言這是天大的美事,但對於那些喪國的王公貴族,失去家園的黎民百姓,戰爭,各有所表。
是為自身的利益?
抑或是高尚的情操?
無論如何,這是我內心頭一次深刻感受到,我與眼前冰冷的少年,彼此間好似出現了一道隔閡。
「我原以為大秦聯燕攻趙是木已成舟,可如今,如今若趙國與秦國聯手,趙國胡服騎射,秦國秦努鐵騎,這樣兩兩大勢強兵圍攻燕國,勢必比聯燕攻趙時損傷慘重,況且君主貪婪無度,若他們察覺攻燕有成,那燕國不損失十幾座城池,他們是不會罷休的!」
"依你的話說,若攻城略地還要顧慮他國損失,那秦國豈不只好坐以待斃,任人宰割。"
「我怎會不明白你計謀中的利益糾葛,但是,就在此刻你卻是要挑起更加慘烈的戰事,讓君王有更好的理由去進攻別的國家?! 」
「若是如果他人來襲,我們正正當當打回去,或嚇阻他們的征戰的愚行,那自然是有理有據,可現在,你就是想讓原本的戰爭擴大,犧牲無數人的性命,換來大秦的利益?! 」
"在這個戰亂無能數的世道,你跟我談人義,跟我談非攻?!"甘羅指頭迅速寫畫,一點都不難從他陰怒的冷眸與躁動的素指上,看出他此刻洶湧的氣憤。
"你聽聽你自己都說了些什麼,墨家兼愛非攻?道家無為而治?"
"若不爭失了國土,談何治理。失了家園,談和安康。如若大秦得勝,一統六國,這四分五裂的諸侯國就再也不會互相爭鬥。"
甘羅的剛硬的筆畫劃到一半驟然止停,他悻悻的握起杯盞,將杯中茶水一飲而盡後,便重重地放在案桌上。
此舉驚動了車馬外頭的趙國隨從,頓時,車廉掀起,一位面容嚴肅的男子往裏頭瞥了幾眼,見沒事後放下簾子,竟是與外頭的其餘人譏諷閒談起來。
「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哪個黃口小兒溜進來,碰東碰西,差點把裏頭鬧的! 」
「可不是嘛,我當初還想秦國使臣定是虎彪彪的結實男兒,結果,人一到,直下車,竟是一尊弱不禁風的白玉娃娃。」
原本與甘羅相爭的我,聽了外頭的閒言碎語,心裡頭不由得冷了大半,不只是為了那些小瞧甘羅的人,更是他們提醒了我甘羅現在的立場。
我原以為大秦立大功,可以是輔君王執仁政,進諫善謀,讓貪官汙吏無所遁形,善法利行造福眾人,讓百姓能夠過得安樂,吃飽穿暖,不受亂世所苦。
可如今,我漸漸想起了大秦征戰六國的原因,若欲立功,拿出敵將的頭顱當是最快方法,二十級軍功爵位制便是讓大秦成為殺戮兵器的其中一個原因。
虎狼之師的名頭終非一蹴而就,互爭廝殺的嗜欲終非一念即成。
在這個節骨眼上我既無法幫上甘家,無法幫上他,更別提那些孤苦的百姓,那現在,我所爭取的看在他眼裡,也不過就是無益處的爭吵。
更何況,我不同於甘羅,我沒有天才般的謀略,也沒有更好的手段,能夠使諸國間的戰爭停下。我此刻的舉動也不過是言而難行,出一張嘴罷了。
「你這麼做是為了大秦,為了甘家,對嗎?」我淡漠問他,甘羅聽聞,深吸了一口氣,只答:「身為大秦臣子,身為甘家之子,這便是我的本分,然,何謂本分?」
「無關意願,身必為兮行,心當為兮動,這—便是本分。」
我聽了甘羅的回答沉默以對,也不再同他說上半句,只是靜靜地閉上了眼,默想這數年來發生的種種,而剛剛被我壓抑住的混亂情感與記憶,轉眼掙脫禁錮衝撞我的意識。
剎那,五感消盡,靈魂再次沉入意識的汪洋中輪迴往復,卻不知,此次失去意識迎向的未來,將會是再一次的穿心之痛。
18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35M9EeNovY
- 18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lDHS9YFBOG
185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jQ8FlBpuqz
當瓏形影消散後,甘羅也早已沒心思注意到消失的瓏。方才的一番爭論,讓他將所有心力投入面見趙悼襄王的會談上,不過,他並未察覺,再他刻意逃避瓏的荒唐道理之際,他的腦海深處卻是將瓏口中的亂世悲哀給默默記下了。
半個時辰後,趙王的僕從匆匆領著甘羅面見趙王,寬敞的車廂裡,趙王隨意的坐於席上,他身披獸皮大氅,美絹穿起,一臉的絡腮鬍雖打理整齊,卻讓甘羅感到有些老態。
甘羅端正入座,他冷眼一掃桌上的酒器與擺置,立刻從不符合禮節的粗陋酒器,推敲出趙王心中所想。他心想趙悼襄王是不太滿意,他這位年紀輕淺的來使。
趙王見甘羅入座,兩眼珠子裡蘊藏的是甘羅習以為常的輕視。
「來人,給大秦使臣上酒。」趙王大聲喝道,一旁的隨伺立即拿著酒盞恭敬走來,突地,隨伺突然皺起眉頭,故作為難朝趙王說:「大王,小的眼拙,都說大秦男子個個是體狀如虎,身形高大,可在場除了本國人物,怎麼未見傳聞中的大秦使者。」
「瞎了你的眼,大秦使臣不正端坐在那?」趙王咧嘴笑,兩指浮誇指著甘羅,隨伺見狀嘻皮笑臉的連忙致歉,他一邊替甘羅斟酒,一邊說:「小的該死,小的該死!小的鼠目見識,實在是沒想到一位總角孩童竟是大秦使節,小的一生三十年載,生根於秦落地於趙,接待過無數諸國使臣,個個皆不是而立之年的頂上人,哪知這次……這,這次大秦怎麼會是派先生來此?」隨從刻意問甘羅,甘羅卻是從頭到尾都未搭裡他。
剎那,當甘羅酒杯中的酒水要斟滿之際,甘羅從衣袖中抽出當初父母送別時,為表相思之情的櫟樹枝。他浮誇大揮,故意擊倒酒杯,酒水頓時濺了隨從一身,杯盞也落到地上發出震耳的聲響。
車廂內的數名護衛見甘羅抽出一條長物,各個異口同聲的大喊"有兇器"後,便立馬拔劍,轉眼間,利劍早已無聲的架在了甘羅白皙且脆弱的脖頸上。
此刻趙王臉色陰沉,隨從則是老早退到了暗角,羞惱的清理身上的酒水。眼下的場面是一觸即發,甘羅若是行差踏錯半步,十日後,留給甘家,留給甘羅爹娘的,就僅剩一個死字。
ns 15.158.61.17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