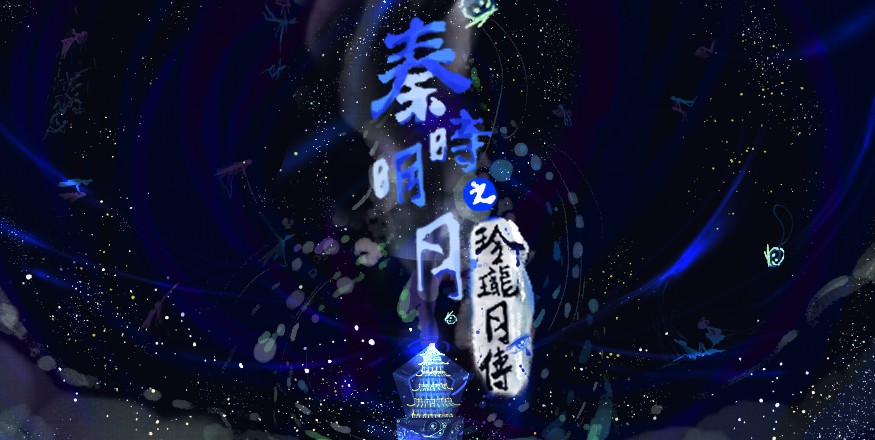馬車內,甘羅不驚不懼,手握著櫟樹枝,鎮定的向趙王問道:「大王認為這是何物?」
趙王一聽,黑眸煩躁的往上一翻,他深吸了一口氣後閉上眼,片刻,他猛然睜眼,眼中夾帶著焦躁的怒火,朝甘羅直吼:「樹棒?木枝?你與其拿著這等小兒玩意讓寡人猜,何不問問寡人,要如何處置你這不知好歹的娃娃!」
「美酒相迎,你毫不領情,一個破物,就是糟蹋寡人的心意!」趙王單手猛力的拍在了案桌上,一聲震響,響徹車廂裡外,而此舉也使得包圍甘羅的護衛顯露出了厚重的殺意。
眼下,他們就等著趙王一聲令下,就可輕而易舉的滑過利劍,讓少年的頭與身體永遠告別。
甘羅縱使是少年天才,卻難逃他是一介凡夫的事實,眼下情勢緊張,他也不免被護衛放出的殺氣給壓的喘不過氣來。
他深吸一口氣,感受到架在脖頸上的劍刃,陰寒的緊貼著肌膚,而背後冰涼的觸感是自己的官服被冷汗浸濕的最好證明。
甘羅托舉掌中的櫟枝,緩緩將頭揚起,不亢不卑的向趙王冷冷道: 「此物乃大秦櫟樹之枝,抑是緩解甘羅相思之情的貴木。眼下大王認為此物是平平無奇的木枝,而我周身圍繞的莽夫卻認為是凶器,如此,大王認為誰說的有理? 」
「管你是貴木,凶器,趙國境內寡人說它是一便是一,任憑你手上捧著天寶珠玉,寡人一句破物,就是丟進火爐你又能如何? 」趙王急促吼著,連原本厚重的聲音都因不耐煩而上揚幾分。
「是,因您是趙國之君,趙國境內,手握大權,無人可比,君王作強,萬人俯首。」
趙王聽著,臉上越發得意起來,他的眼神雖有輕蔑,嘴角卻是高高揚起。
「簡單一句,亂世荒年,強者稱王,敗者為寇,今日甘羅出使趙國之舉,就如同我掌中的櫟枝般,有人不屑一顧,有人嗤鼻笑語,更有人,珍惜此刻,只為讓箇中良機得之於手。如今的秦國,百萬之眾,千倉萬庫,其勢可斷山川,其兵可催巍牆。現在,我手中之物的意義早已無關緊要,重要的是,能夠定奪它意義的那位強者,又或者說是—六國內的最強之國。」甘羅故意頓了頓,見趙王的笑意漸漸消失,他藍眸中狡詐的精光閃現,宛如盯上獵物的雄鷹般,一刻都不會放過眼中的獵物。
「大王心裡有數燕國燕太子丹在秦國為質,也曉得如今大秦有意讓張唐出使燕國為相,這樣說來,秦燕交好的下一步,便是擇敵而攻之。眼下秦在前頭,燕在後尾,兩兩夾擊趙國,趙國必將面臨滅頂之災。」
趙王一聽,兩眼怒瞪,咬著牙,冷唇微微發顫。他被甘羅精利的開解給嚇得興致全失,他心想此刻的現狀是秦強楚弱,韓國被滅,剩下的五國中,唯獨秦國傲然獨立。如果這般強大的秦國在聯合燕國攻趙,那趙國勢必被挫骨揚灰。
趙王想到這,心慌不已,一時半會竟不知該如何應答。而一旁的護衛聽了甘羅的狂語,忍不住迸發殺氣,就好似下一刻便要取下眼前人的頂上人頭。
「大王莫急,甘羅此次有一妙計。」甘羅悠哉說著,藍眸往脖頸上的利劍一掃,趙王頓時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大膽!大秦使臣遠道而來,你們怎敢如此放肆!」趙王大聲斥喝眼前護衛,護衛的利劍立馬收入了劍鞘中。
甘羅見護衛全退到了一旁,他頓了頓,開始摸起了自己脖子自語道:「大秦律法向來公正嚴峻,今日愚鈍的莽夫攪了大王的興致實屬不該,此舉若是換在大秦,觸怒君王為一條,向使臣拔劍傷人為一條,兩條加總清算,不丟掉一條胳膊,兩條腿,不只無以讓人信服,更難平君王威怒。」
趙王聽完甘羅的冷冷地自語,又見他白皙的指頭,在脖頸上遭劍刃壓出的紅印上來回游離,心中不免急了起來。
於是,趙王大喝,拿起案桌上的杯盞朝一旁的護衛砸去,剎那,其中一名護衛被砸得頭破血流,卻也是不敢多言半句。
「聾了你們,還不快給寡人滾去領罰!」趙王故意怒吼,護衛眨眼間就撤了出去。
一旁的甘羅早已小心收起掌中櫟枝,順道偷偷拿起藏在衣袖裡的梅乾,暗暗吃了起來。
半晌,甘羅瞧著眼前鬧劇差不多該結束,心中明白趙王此次故意喧鬧讓護衛去領罰,又未說是何罰責,心中只想是把他們給打發下去了。
"瓏兒,你這回到是安靜的很。你不必擔心,他們幾個所受的刑罰,也不過就是諸國之間刑不上大夫的那種皮毛輕懲,趙王雖看似易怒衝動,但對待隨身護衛倒是留有幾分情分在的。"
甘羅一邊用手指在桌上滑動與瓏示意,一邊向趙王解釋他的主意。
「那麼,甘羅使者,以你的意思只要寡人出五座城池,大秦便願意與燕國斷絕關係,再來我們兩國和力,一舉便可拿下燕國數十座城池!」趙王樂開了眼,欣喜地誇讚甘羅連趙攻燕的妙計。
當甘羅與趙王一來一回之際,他突然楞了半刻,因為他察覺到瓏遲遲未回答他,當他心急的用視線左右找尋瓏後,他才赫然察覺瓏的身影再次消失在他的視野中。
「甘羅!」
忽地,趙王大聲一喊,將甘羅出神的思緒給拉了回來。
甘羅頓了片刻,便揚起清朗的淺笑,莞爾答:「五座城池,換燕國數十座城池,秦趙兩國互利互惠,何樂不為。」
「哈哈哈哈哈!」趙王聞言,豪爽的笑聲迴盪在車廂內。
此刻,他立馬拿起筆,迅速寫下令書,將趙國答應割讓五座城池之令書,遣人遞送至秦國。甘羅看著自己的妙計得手,不只不費一兵一卒空得五座趙國城池,往後大秦連趙攻燕之際,還有數十座城池當作戰利品。他一想到這層關係,眉眼鬆開,終於放下心中大石,但是下一刻,卻有股意外的沉悶壓在他的心頭上。
在甘羅出神之際,剛才譏諷他的隨從又拿著酒盞欲向他斟酒,隨從臉上的神情與方才假意奉迎的模樣不同,他此時兩眼睛裡裝的都是諂媚的笑意。
而甘羅想到瓏又無故消失,心裡是悶是憂,現在眼前阿諛小人斟酒的舉動,又再次提醒他剛剛隨從言談間的刻意譏諷。
於是,甘羅細眉一挑,冷冷的自語起來。
「是了,方才因正事耽擱,我這才想起來,大王剛剛怪罪甘羅,說美酒敬客我卻不領情,其實,非是甘羅不領情,只不過是酒香淺淡,酒色濯濯,倘若沒有大王的好意提醒,實在會讓人將美酒誤以為是尋常茶水。」
「況且,各國有各國的禮制,剛才未仔細端詳,只當案桌前的酒盞制質粗陋,使得甘羅一時間竟沒察覺那是招待來使的酒器,真是讓大王見笑了。」
甘羅說罷,眼神冰冷的隨意往上一帶,直接對上了隨從不安的眼眸。
趙王此時心情大好,聽聞甘羅隨口一說,腦中直接將他的舉動解讀成"甘羅不滿方才隨從斟酒的刻意試探"。
眼下趙王滿腦子都在為甘羅的妙計竊喜,他心想這次不只破了燕國聯秦襲趙的計謀,還能夠給燕國反將一軍,來討回多年以來燕國趁火打劫的惡行。
趙王君心大喜下,壓根無視了隨從所言所行,最終也不過出自他的意思,於是,趙王為了眼前小小神童,怒的拍桌,直指替甘羅面前的隨從大吼。
「寡人好好接待大秦使臣,竟不想你連出個酒水酒器都能給我搞錯,今日之會差點被你這愚昧不忠之人搗毀了去!。」
「這樣優秀的人才,高妙的計謀,如被你的愚行給氣走,那寡人是誅盡你的九族也是難平此怒。」
隨從的眼色從趙王憤慨的怒語裡,逐漸從驚訝轉變成驚恐,他雙膝一跪,匍匐卑微的向趙王焦急求饒。
「大王!大王!是!是小的該死!小的該死!小的求您放過我家裡的父母妻小啊! 」
趙王看著地上焦慮磕頭的隨從,頓了半會,咧嘴笑道: 「看在你多年無大過,辦事勤勞的份上,寡人不誅你九族。」
隨從聞言,滿臉的清涕與淚水在地板留下一攤水漬,他連忙叩首以表感謝,動作幅度大到連淚液都濺到了一旁甘羅。
甘羅的衣衫被幾滴淚水濺到,眉頭一皺,藍眸掠過了一絲厭惡與不滿,他從袖口拿出帕巾,用力的擦了擦衣衫,臉上的陰冷方才散去些。
趙王看隨從大悲大喜,從容的捧起眼前酒樽一飲而盡,隨後怒言大喝: 「來人!把他給我拖下去斬了,讓其他人看看對來使不敬是何下場! 」
「寡人不誅你九族,卻沒說不取你的賤命。」
只見車廂外的守門兵士衝了進來將隨從架住拖走,隨從原本驚恐的臉,轉瞬間黑了整片成了絕望。
他掙扎著,哭吼著,卻唯獨未將當初趙王默許他行為之事給供了出來。
不論是趙王當初聽聞秦國的使臣是一名小童,不論是趙王故意令隨從刻意打探與譏諷,即便現在刀底在他的脖子上,他始終都未說出口,這些,其實都是趙悼襄王默許的事。
他,最後面容死灰的抿緊雙唇,不在大吼,放棄掙扎,只因他明白眼前君王的意思。
"君喜無憂,君怒斷頭。"是死一人,還是賠上整個家族,答案很明顯了。
「大王,我想秦趙兩國之間的情意,自然是不會輕易被酒水之質,尊盞之貌給影響。」甘羅突然出口,趙王聽了愣了一會,謹慎的應答道:「這……甘羅使者說的甚是。」
「既然大王與甘羅所想一致,那您不妨暫且消消怒氣。他既犯錯,也就是打幾棍子的事就罷了,這般興師動眾擾了您的好興致,當真是不值。」甘羅從容的望著趙王,臉帶笑意,也不過就三兩句的功夫,便讓隨從便逃過死劫。
當白日的會談結束,趙王大喜,硬是邀甘羅入邯鄲王宮裡頭慶祝,甘羅嘴角抽笑,本就不打算待上太久,可奈何趙王語急人更急,一會兒的時間,甘羅便已身處宮廷中,看著婀娜美人翩翩起舞,聽著樂活的樂曲與趙悼襄王同歡。
一晃眼,天以黑,夜幕下,一個瘦小的身影從喧鬧的宴會中溜了出來,他疾步靜走,走到了一處偏僻卻精美的庭院。他安靜的望著被雲海掩蓋的夜空,心中來回思索無數次的是早晨瓏的話語,與她話中真心的擔憂以及哀愁。
「甘羅先生! 」忽地,一聲急促的輕喊從甘羅後方響起。
甘羅頓了頓,淡然地轉過頭去,發現是早上因自己的三言兩語,在鬼門關前徘徊的隨從,隨從看起來雖無大傷,臉色卻有些疲弱。
甘羅對他上下打量,故作驚詫的瞇起了眼,問道: 「你沒死啊? 」
隨從聽了甘羅親切的問後,臉色閃過一絲尷尬,抱拳在胸前來回摩娑,隨後立馬回復笑顏,直問道: 「拖先生的福,不過是打了十來頓,撿回一條小命。但是,小的有一事不明,為何今早甘羅先生願意出口相救? 」
「原本是小的無禮再先,您是大人有大量,還願意救我一把。」
「相救? 」甘羅靜默半刻,不由得想起數個時辰前,在說服趙王後所發生的種種鬧劇。
當初他會出口緩解趙王之怒,其因有二,最主要的一點,是瓏焦心的話語在他的腦中揮之不去。
瓏不喜殺戮,不喜相爭,更不喜因功利荼害他人,這數年來,甘羅心中有數,瓏的心思有時機靈,有時卻傻直得不似人間物。雖說她本就非人,但她的思緒與觀點卻總是能引起自己的興趣。
而當他想到瓏時常掛在口邊的"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字字句句都是道家的作派,就是不到非常時期,她絕不輕易與人爭鬥,動口動腳。
甘羅一邊想著這就是傻,就是笨,甚至能說傻的有些癡了,但是,正因為正份傻落在他的心頭,他才能想到第二點。
第二點關係到隨從的出生地,他說他生於秦國,歸根趙國,按理來說他曾經也算是秦國百姓,但不知何原因,許是戰亂,許是災荒,又或者尋求功名,最後定居於趙國。
因為他曾是秦國百姓,甘羅才心血來潮的作為曾經的同鄉人拉他一把,再者,甘羅也明白一名普通的僕從,是沒有膽子幹下故意給使臣難堪這等干係國家顏面的事,其故意刁難的言行舉止,不外乎便是趙悼襄王的默許。
「我記得白日時你說你曾是秦國人,既然我們兩有同鄉的緣分,也不用這麼多規矩,你就直接喚我甘羅如何?」甘羅揚起嘴角,內心想的是當初衛婀套話的手段。
只見隨從臉上閃過各種隱匿的情緒,是一絲為難與謹慎,一絲提防與不安,他愣了半刻,神情比方才多了些距離感。
而這些變化都被甘羅犀利的藍眸收入眼底,甘羅一笑,也算是明白衛婀當初故意試探之舉,這看突然又似無傷大雅的請求,對於洞察力極好的人來說,對方臉上任何一絲細微的表情,便是內心最好的映射。
而眼下,隨從表面道謝,內心還是藏有些許不滿與堤防。甘羅知曉眼前人懷有其他異心後,便打算隨意打發他相救的原因,繞回宮殿赴宴。
「甘羅先生,你,你的胸口?!」隨從突然壓聲驚呼,有些發顫的指著甘羅的胸膛。
甘羅順著他的所指的位置朝下一看,發現他胸口內袋發出皓皓微光,他小心翼翼的拿出內袋的玉石,只見碧玉玲瓏上頭不知何時多了幾道細小無比的裂痕,甘羅犀利的察覺碧玉玲瓏上的裂痕,心中一緊,臉上的從容隨即消失。
隨從看見甘羅手上的碧玉玲瓏發散亮光,玉色翠白相參,仔細瞧著,心中不由自主驚嘆唸起各路神仙來。
「東皇公在上!這玉怕不是哪位大王的珍物?! 」隨從臉上驚異,伸出手就想觸碰甘羅掌上的玉石。
甘羅敏銳地察覺隨從之舉,眨眼間,便攥緊了玉石貼在胸口,嚴肅道: 「碧玉我心,非可觸也。」
「這,這玉石,是了,如若先生不介意,能否請在這稍待片刻,有一位高人我定要讓先生見上一面,就當作是償還先生相救之恩。」
隨從說罷,兩腳像抹油般眨眼間就跑沒影,甘羅腦中"非常介意"說都還未出口半句,就剩他一人孤立於此。
ns 15.158.61.20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