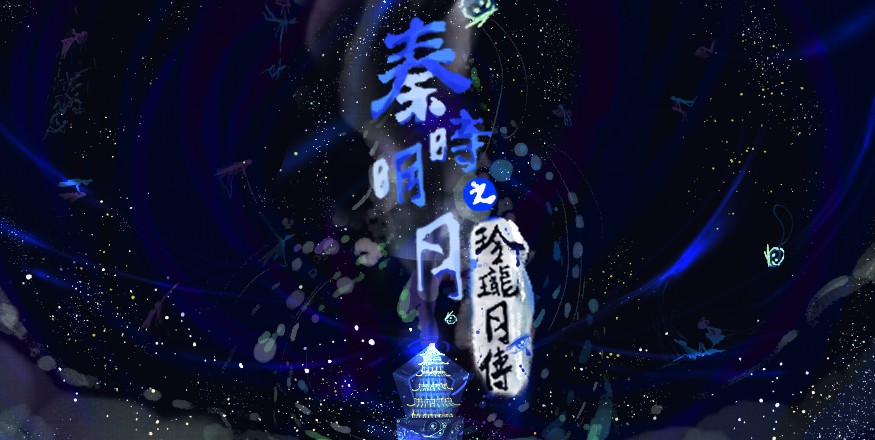日上三竿,我才迷糊地從舒服的軟被上醒來,外頭一片明亮想是暴雨已過。
昏沉半刻,腦中立馬憶起昨日發生的種種。我捧著星魂床上的被褥,摸了摸床邊空出的位置,發現上頭沒有殘留半點餘溫。
星魂他昨日以控心術把我哄睡後,自己倒是懂分寸的未與我共眠於同張床上。想到這次睡在星魂的床鋪上,我不禁想起在九天曦和時曾睡過他華麗的星河大床。
這次倒是同上次一般,床都給我,人卻跑了。
被褥上殘留的芍藥香氣默默的沁入鼻間,心頭砰砰跳著,腦中經過一番天人交戰後,小心翼翼的將臉埋進被褥裏頭。我傻笑著在床上翻滾,又想起他曾經藉由五靈競鬥,送出發散著芍藥香的冰清面紗,一不小心整個人竟飄得差點激動地叫了出來。
臉上泛起笑意,得意的猛力蹭著星魂的被褥,又在床上翻來覆去。
誰能想到大名鼎鼎的陰陽家左護法,一位冰冷邪魅的狂狷少年,竟會有這麼可愛的一面。
突然間,房門無聲打開,星魂踏步而入,第一眼看到我像隻貓仔在床上亂蹭傻笑的模樣,雙目睜大,有些不敢置信。
他尷尬地挪開視線,臉頰染上淺淡的紅暈。我見他突然進房,想到我方才的蠢樣都被他看在眼裡,匆匆地放下被褥,在眨眼間穿好鞋,稍微整理好衣服,踉蹌地走到桌前坐好替他倒茶。
我看著杯中的茶水倒映出我通紅的臉,著實想一頭撞死在牆上,。
真是什麼不看,偏生給他看到我癡傻的模樣?!
嘴角抽動,我趕緊喝了一口溫茶含在嘴中,好叫醒昏睡的腦子。
「看你這模樣,昨夜是睡得挺好。」星魂恢復往常的沉穩,走到我跟前,拿起我喝到一半的茶水一飲而盡。
我嚥下茶水,緊張地低頭,尷尬笑道:「還不都是……托你的福。」
「你還有六日的時間。」星魂嘴角勾起淺笑,提醒著高漸離行刑的日子。我腦門一抽,匆匆別過星魂前往死牢。
將軍府的死牢內,我同樣又買了一壺酒,又是好言相勸,說之以理,動之以情,在看看昨日留於高漸離牢房內的酒壺,上面長了一些灰,動都沒被動過。
看他左耳進右耳出的模樣,就算是長著一百張嘴,也說不動無耳之人,他這是鐵了心的不願當贏政琴的師。
我低眸看著這兩日奔波而越發縮水的素色荷苞,裡頭的圓錢是當初在末閣中一點一點積攢起來的,掐指一算,也不過兩日的時間,錢財如水,我這小財庫裡的財水都快流乾了。
看高漸離鬍鬚漸長,身上衣物有些殘破,我嘆了口氣,問他可否需要什麼,得到的答案是緘默的沉寂。
我深吸一口氣,再次說道:「我說過,我不會放棄的。」語畢,只留下一壺酒離了將軍府。
到了第三日,同樣的問候,同樣的閒談,結果就是我一人在偌大的牢房裡唱獨腳戲,當我以為今日這第三壺酒,又要被冷落在牢房裡的暗角時,一直閉目養神的高漸離突然開口,冷聲道:「無用的堅持,到頭來也只是一場空。」
「無用與否,是要到最後一刻才能知曉。更何況,能做了都做了,才有資格理直氣壯的說放棄不是?」
我雖不服的反駁,心中卻對今日勸說未果感到失意。我摸摸鼻子只好認命的先回賓館。
大白日的走在熱鬧的海市上,卻見多名小聖賢莊的學子結伴成行不知去向何方,我尋思著他們這個時間點應當還在聽課,心中好奇心作祟,看著天色正早,於是默默地跟上去瞧。
沒走幾步,便來到生意興榮的藥館前,左看右看,一道孰悉的氣息忽然從背後靠近。謹慎回首,溫雅的鵝黃祥雲衣袍映入眼簾,一位眉目清秀的高挑男子和藹的看著我。
我看著他有神的褐眼,想起他是金部五靈玄同,君房。
君房眉間含笑,略帶訝異道:「久別重逢,瓏弟子依然神采奕奕。」
「前先日子我從大司命長老口中得知,你與星魂大人聯手擊敗反秦判賊。依瓏此次優秀的功績來看,興許當你回到九天曦和後,會有意想不到的賞賜在等著你。」
聽到君房的客套的誇讚,我不好意思地應付幾聲,轉而問起他為何突然來到桑海城。
「你有所不知,幾日前雲中君大人不知怎地在煉丹時失誤中毒,這對於大人來說並非難事。可究竟是禍不單行,原本的丹爐在煉丹途中不知怎地突然炸裂,大人受其所傷趕忙吃了萬癒丹加以調息,卻察覺萬癒丹本身與體內毒素相剋,使得病情加重。」君房嚴肅道。
「我此次前來桑海城不只為了親自向星魂大人稟明此事,另外,雲中君大人雖重傷臥床,卻依舊操心金部事務。他聽說桑海一戰抓獲不少俘虜,特地命我前來向星魂大人求討一人供其試藥。」
我就想星魂昨日桌上的公文怎會突然增加,原來是噁心老怪這回煉丹失利傷了自己。
不過,雲中君對於煉丹術有一定的造詣,也非大意胡來之人,此次事出突然總覺得有些蹊蹺。
我沒與君房多聊,大概向他通知了星魂目前在桑海城賓館的位置,便目送君房離去。
他在離開前他還特意告知近日桑海城流傳一種名為軟溫香的密藥,要我小心為好。據說此藥服之過量身散異香,受香氣所迷可令男子渾身鬆軟,心情舒爽。
「大人!」
藥房裡的夥計走出一人,他小心謹慎的喊著我,說是喊了我好幾聲了卻是半點反應也沒有。他大人大人的喊,不禁讓人懷疑是否認錯了人。
我都還未理清事情來由,他便匆忙的將一塊玉珮遞到我手中,嘴裡不斷唸叨剛才儒家弟子的健忘,又將我誤會成與他們相識。只求我同往常一樣,將東西送至他們手上,順便把玉珮還了去。
而他口中的東西,就連夥計自己也不清楚,只知道陰陽家弟子與儒家弟子有所往來。
光憑這一點,我便隻身來到小聖賢莊外頭想要弄清楚當中緣由,畢竟陰陽家弟子可沒理由,也不可能與儒家之人有所來往。
誰知前腳剛到小聖賢莊門口,便撞上剛才的弟子。只見他著急的往外頭跑,看了我手上拿的玉珮直接停下腳步,對我說:「姑,姑娘是陰陽家的人?」
我頷首,問道:「是你將玉珮留在藥房?」
「這不昨日你們趕得緊,不小心把信物留在掌櫃那頭了。嘖,糊塗老兒每次給的東西也不一次算清。」
「先謝過姑娘親自送東西來,我還得趕課實是不能多聊。」弟子神情慌亂的接下玉珮,我都還沒出口探問就想一走了之。
我見他匆忙地要走,卻沒看到腳邊突然多了一條毒蛇,險些就要踩了上去。危急之下,我運起內力已迅速將毒蛇吸了過來。
「等等,走路當心點。」我喊住他,讓他看了看我手中的毒蛇。他見了毒蛇到也不怕,倒是停下了急匆匆的步伐。
見他不怕,我提氣將毒蛇送出百尺外的竹林地,算是將他安全放生。
「荀子師叔醫術高超,幾隻孽畜我們到不放在眼裡,就是近日不知是否因熱天暴雨引出蛇蟲,老有人遇蛇遭咬,否則我在小聖賢莊待了數年,也未曾見過什麼不乾淨的東西。」
見他有意留下,我趕緊切入正題故意試探道:「我們送的東西可好?」
「哎,子慕兄的技術姑娘還用得著擔心半點嗎?」弟子聽到我的話覺得有些荒唐,嘴角微抽,連忙反駁。
「總之,不會比你們金部煉出的東西差,這幾日的生意你又不是不曉得,可謂是蒸蒸日上。」弟子自信道,拿出自己圓鼓鼓的荷囊朝我晃了晃,裡頭錢幣撞擊的聲音沉甸甸的。
金部?莫非他指的是煉丹,他們在賣丹藥?
儒家弟子何時當起方士來煉丹賣藥了?
我故意繼續向弟子打聽下去,他雖有半邊身子在門裏頭卻沒急著離去。
「若你今日再遲到,可不是罰抄論語,周禮十來遍那麼簡單了。」溫和的聲音從弟子身後傳來,其聲似春日暖陽溫煦柔和。
「張良……先生?」就差那麼一點,我又要無禮的連名帶姓叫出張良的名字。
我怎麼偏生又遇見這麼一位棘手的人物。
弟子轉過身去,向身後的張良有禮作揖,道了歉後緊張的趕忙跑入小聖賢莊裡。
不打草驚蛇想探出點什麼看來是沒戲了。
面前的張良身著淺藍色的儒袍,衣節整齊端莊,謙謙有禮的表面下還是如當日在賓館一般,總感覺藏著一絲看不透的狡黠。
「暴雨過去,朗朗天明。」
「玉姑娘來的正是時候。」張良淺笑,我還沒來得及拒絕遂將我迎進小聖賢莊裡頭。
*
當我一踏入荀子私人宅院的剎那,迎面而來的是凶狠的赤鍊軟劍。
赤練毫不留情,招招奪命,軟劍鋒利在空中舞動,眨眼間就削下院子內外的數棵竹子與花草。我控水化形,水流聚散湧動,破開招招奪命的劍招,順道將四周無辜的花草樹木給整理一番。
「衛庄的傷……。」張良冷聲開口,赤鍊的攻擊赫然停下。
誰能料想到才剛踏入院子裡,就會發生一場激戰,我看著四周匍匐的毒蛇,算是明白為何一進門就會被攻擊。
「看來你身邊的小可愛已經先知會你一聲了。」我冷聲道,怎會忘了當初毒蛇盤在星魂周遭,眼前嬌媚殺手的所言所行。
「哼,你早就知道是我?」赤鍊瞇起眼,默默地攥緊手中的赤鍊軟劍。
「紅蓮殿下就不好奇,玉姑娘如今為何完好無缺的站在這?」張良擋在我的身前向赤鍊說道。
紅蓮殿下?
殿下?
想不到能夠操縱毒蛇流沙的殺手過去是一名公主。亂世之下,世道變化無常何嘗不令人唏噓。但是,即使如此,她曾打算殺了星魂的事實並未改變。
張良將我們領進屋內,赤練收起利劍,雖然臉色陰冷,卻仍安分的坐在我的對面。
「我的事無可奉告,至於衛庄當初不只想將陰陽家等人滅口,還想以墨玉麒麟的易容術,放走墨家,刺殺蒙恬等等罪責賴到陰陽家頭上。這筆帳,我還沒即刻跟流沙討要,流沙倒能夠理直氣壯的要我提供救人之法。」
「這又算是哪門子的求人之理。」我憤恨道。
先不說萬愈法本非尋常術法,常人無法驅使,若治療途中心念稍有不正,被治療者即刻身亡的可能還是有的。
五君過去曾言"扶桑花開,血濺十里",陰陽家真正的實力無人知曉,不都是因為沒人能夠知曉真相後還能活著。
更何況,瓏玉本源本就超脫常人認知,世人多欲,若如此強大的力量被心術不正之人知曉,豈不要再節外生枝,生出禍端。
「看來你們的國師大人同你說了不少啊!」
「子房,我說過,比起求人;不如逼人。」赤練狠狠瞪著我,慍怒道。
「還有,她可不是什麼玉姑娘。」
「姐姐說的是不是啊?」
「瓏──月妹妹。」赤練勾起邪笑朝我挑釁,纖長的指頭把玩著腰間收起的赤練劍尖。
「呦,猶記得當初望月下,國師大人傷痕累累的朝你奔赴而來,他驚惶的吼聲真是震人心神。」赤鍊雙手交叉抱胸,抬起頭傲視看我。我深深吸了一口氣,心裡一股火的實在想不到不立刻打她的理由。
我攥著顫抖的拳頭,遭周的水氣盤旋在我的身旁,彷彿下一刻便會化作凍骨冰刺往眼前人襲去。
氣氛緊張,一觸即發,一旁的張良不慌不怕,倒是勾起嘴角朝赤練溫和道:「紅蓮殿下,午時已到,我先讓墨玉麒麟將衛庄的藥湯端去了。」
不知張良話中是藏何玄機,赤練聽他這番話原本一臉的怒氣頓消三四分,她匆匆起身,迅速往外走去。
「方才難為玉姑娘了,子房在此向姑娘賠個不是。」張良突然起身拱手朝我道歉,我被他這麼恭敬一拜,不禁隨他一同起身,想到動手動腳的是赤練而不是他,心裡有些不好意思受他的禮。
「是子房思慮不周,沒想到赤練會守在門口。」張良抱歉道。
「既然先生以知曉我真正的名字,為何還要稱呼我為玉姑娘?」
「敢問這稱呼是誰告訴你的?」我謹慎問道。
「玉乃石之美,含五德,我相信南公前輩話中自有深意。更何況,玉情溫潤,子房覺得這個稱呼與姑娘甚是相配。」
想不到竟是南公前輩告訴他的,這張良何時又與前輩打交道過了。
「況且,姑娘自己不也是喚我先生而非子房。」張良雙目笑成兩道月牙,溫和反駁道。
「先生莫忘了,我是……。」話還未說完,張良卻有意接下了我的話。
「我知曉你為陰陽家之人,但姑娘也別忘了,我不僅是儒家當家抑同時是一名夫子。」
「既然小聖賢莊內有學子心存疑惑,子房為人師者當仁不讓應為其傳道授業,排憂解惑。」張良從容笑著,接著說:「墨家鉅子以下,還有九位統領,其一是先賢墨子的後人,精通機關術的班大師;善於鑄劍的徐夫子;已故的絕頂刺客,荊軻;手持易水寒,琴藝精湛的劍客高漸離;精通樂理舞蹈的雪女;力大無窮的大鐵鎚;尚在昏迷的醫仙端木蓉;有間客棧的名廚庖丁。」
「最後一位,有著絕頂輕功的盜王之王,盜趾。」
「聽盜趾兄說,近日陰陽家裏頭有一位女子面帶薄紗,薄紗輕盈如浮雲飄盪,她與陰陽家其他人不同,是唯一會提著酒進入死牢的陰陽家弟子。每日只入一次死牢,一入則待上一兩個時辰。」
「不只如此,她亦在桑海城多次向人打聽販賣琴器的場所,像安樂門等聲名遠播之地也被她探了數遍。」張良笑意漸濃,他頓了一會,再接著說:「子房猜姑娘是想勸說高漸離以精湛的琴藝讓自己能免於行刑,但途中卻遇到了某種瓶頸。」
「既然黑夜遁去,天明到來,對於高漸離行刑之事,不妨聽一聽故人之見。」
齊魯三傑張良,我都未向他透露半字,他卻只憑著墨家盜趾所得的情報便可以推測到我的目的,這與星魂不相上下的聰明腦兒,我當真可以應付嗎?
頓時,我想起他前三日前說"不妨在天明來小聖賢莊與學子一同聽課",此天明原是彼天明啊!
也罷,事到如今,此次一會就當是個轉機,更何況,墨家被大秦與陰陽家圍剿,天明他也不知有無安好。
在張良的安排下,我見到了天明,見到其餘的墨家統領。眼前的天明穿著與他有些違和的儒服,腰間的節與胸口的衣口像是未打理般顯得有些隨意,而他身後則是班大師、雪女、盜趾、大鐵鎚等墨家統領。
他笑顏依舊開朗,頭一句話卻是關心我的安危。在確認我無事後,他振奮的同我說了近日的經歷。
想不到曾經淘氣的小孩,經過機關城的變故後,被前任墨家鉅子燕丹托與重負成為了墨家掌門,墨家的鉅子。
忽地,天明突然態度一轉,認真道:「我需要你的幫忙救出小高。」
「我知道你一定會幫我的。」天明堅韌的眼神凝視著我,他眼神中的強烈的堅定就如同當初在小聖賢莊,誓死都想替我報仇一樣。
高漸離不只是墨家九大統領之一,還是一名一流高手。蒙恬不會不曉得這個道理,陰陽家配合大秦固守在死牢唯一的出口,也正是為了防範有人劫獄。
眼下唯一能讓高漸離順利逃出牢獄的辦法,只能從大秦內部人員開始疏通。
「阿朧,拜託了。」天明抓住我的肩膀真誠道。儘管他的身高比我矮了幾吋,但在此刻,他略為仰起的頭與堅決的視線卻令我備感壓力。
天明是決意要請我間接協助他們救出高漸離了。
ns 15.158.61.17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