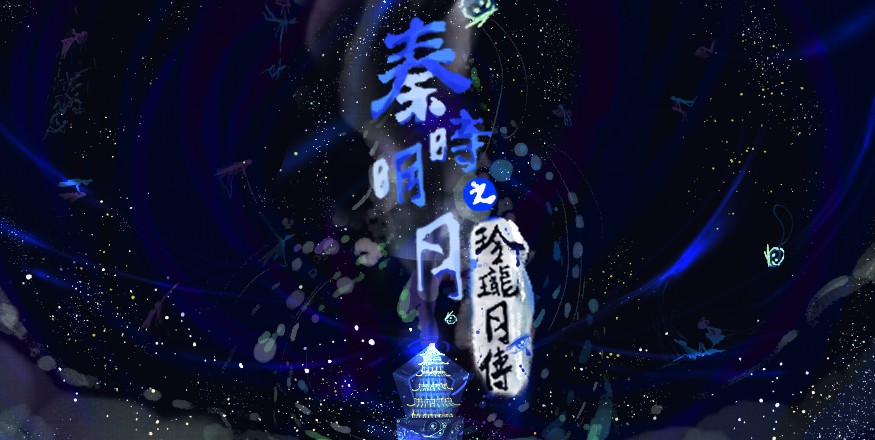將軍府的死牢裡,我蹲在冰冷的石地板上試圖勸說墨家高漸離。半個時辰過去,只換來他的冷眼瞪視,不屑的拒絕。
星魂這次沒有攔我,我也沒有伸手請他協助。看眼下的狀況,他是篤定高漸離不會答應方才同意的吧?
我並未怪他,以陰陽家的立場而言,我這麼做的確是將一隻腳踏入灰色地帶。
當初甘羅未被處死,而是成為陰陽家的星魂,大秦的國師。一月前南公前輩帶我到七宿祭台,贏政留下墨家匠人的活口,這些不外乎都應證此了一件事─贏政求賢若渴,不擾政權,則百才具用。
高漸離的琴技乃當今天下一絕,聽聞扶蘇公子是當今公子中最為賢明遠播之人,更何況扶蘇之母出自楚國,楚國禮樂盛行,若他聽見高漸離之琴音舉薦與贏政,以高漸離卓越的琴藝,像贏政傳達百姓之苦倒也不是不可能,更不用提若他能和贏政說上幾句話,那就再好不過了。
我身為陰陽家之人,陰陽家與星魂為大秦效力,在這個立場上我自是不能以暴反秦。眼下我能想到最不見血,不給星魂添麻煩的方法,唯有拜託墨家高漸離。否則,我此刻著實想闖入咸陽宮裡頭,以通心的力量讓贏政體會體會甘羅之苦,感受百姓之勞。
「天明都告訴我了,當初在小聖賢莊是你救了他。但是,即便你是阿朧,還在小聖賢莊救過天明,這些都無法改變機關城已毀,無辜百姓遭屠,陰陽家與贏政皆是一丘之貉的事實。」
「我與陰陽家的人無話可說,你走吧。」高漸離盤腿端坐於地,連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只剩下七日的時間足夠說服他,還要在七日的時間搞來一把能供他演奏的樂器,更不用提如何打通門路讓他在處刑前演奏的方法。他以冰冷回絕我的提議,即便我將來由說出試圖說服他,他從頭到尾就是"死都不為大秦效力,更遑論給贏政彈琴"這樣的堅決的態度。
「我不會放棄的。」我留下一句話與一壺剛買好的酒便離開了。
過去在機關城,何人不知墨家裏頭,劍客高漸離與刺秦刺客荊軻乃多年酒友,高漸離平日烈酒入喉自是不醉不休,就算七日後我真無法說服他,至少在這段期間還有烈酒能伴他最後一程。
出了桑海城的將軍府,我四處打探賣琴的去處與行刑之時的消息,耗了大半天直到暴雨落下,淋了我一身,我才匆忙趕回賓館。
102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SbJvVjkvxK
*
102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kiLaYT49V1
夜晚來臨,用過晚膳後,我坐在窗前看著外頭的暴雨打在大街小巷的屋瓦上。
自中午過後我便再也沒與星魂說過話,他自己除了陰陽家的事物與大秦的政務需處理,還老往陰陽家在桑海城的牢獄跑。
所謂一人做事一人當,我能做的就是以自己的力量拚盡全力去完成,至於最後的結果為何,就要看老天的決定了。
即便滿腦子裡是高漸離的事,但往窗外看去,星魂在白日坦然面對心中那份柔情的模樣在心裡頭打轉,我只要想到他身上染了芍藥清香,沉著臉強勢的親自為我戴上冰清面紗,心裡頭就安靜不下來。
今夜估計是不用睡了。
忽地,一道雷光在我眼前劈落,我身子一顫,嚇得地從窗台重摔在地。過去我曾想雷光很美,暴雨如曲,二者和一乃是天地間奔狂的頌歌。
可現在,轟隆作響的雷鳴貫穿耳膜,我再次聽見了他們的哀號,他們在雷聲中,在暗雲下,他們──沒有選擇了。
甘羅父母人頭落地的沉悶聲響,彷彿隨著我重摔在地的聲音在耳畔迴繞。
此刻,心中只剩一個念頭。
"星魂?"
"星魂在哪?!"
都說匆忙時連鞋子都會忘了穿,阿鈴與我分享過許多關於她生活的世界。而在我身處的世界裏頭,女性裸露的雙足是不可明談的羞恥,隨意暴露的事。大晚上的,我很慶幸光腳跑過一層層的賓館廊道,半個人的影子都沒見著。
我努力想著許多不相干的事,阿鈴有趣的碎唸?女性的裸足?上午的壯士?齊魯三傑的張良?
但是當震耳雷聲響徹整個夜空,這些一點屁用也沒有。
此時此刻,我就是眨個眼,眼前彷彿就能清晰看見血肉橫飛的頭顱,聽見淒厲又痛苦的哀鳴,更不用提,曾經閃爍著自信光輝的藍眸,就如隕星沉沉墜落。
這樣算來,星魂當今十六,自他十二那年來又過了近四年,他平日裡高傲冷肅的模樣,再加上他加入陰陽家斬斷人世諸多牽絆,無論甘氏,甘家的慘況都過去了,他不會因為區區雷鳴而害怕的!
腦中糾結太多,等我回神早已到了星魂的房門外頭。心如火燒,就是猛地推開房門。
「啊!!!!」
一聲尖銳的女子叫聲,伴隨著衝鼻的異香給我的腦門來上一個重擊。
我傻了,恍惚地看著陌生的兩人光溜溜的如練武一般纏打在一塊。剎那,我閉眼大聲道歉,猛力關上門,火速衝回房裡。
喘了大半天,心想不就是撞見男女之間的深度交流,這樣壯觀的畫面倒是把我繃緊的思緒給梳理了一番。我調息片刻,耳邊轟轟雷鳴,對星魂未告知我突然換房的舉動有些不滿。
我穿好鞋子整理好衣袍,在大雨夜裡不好意思的找賓館的阿婆問去。
阿婆看我來,臉上笑意開,她沒多問多說就簡單的告訴我星魂的房間在哪。結果繞了一大圈,沒想到星魂換了房竟是換在我隔壁!
來到星魂房門輕聲敲了幾下,雷鳴轟隆作響似要把全桑海城的人都給吵醒般。
我推開房門,迎來的是星魂嚴肅命令。
「衛無,我不是讓你先退下。」
「即便當初你體內的傀儡術令你不受紫焰波及,這也不代表你可以愚蠢的無視身上的劍傷。」
我看著星魂垂眸在幽幽燭火下看著木簡,他專注地閱讀沒發現是我。總覺得他桌上的文卷比平日還要再多上數倍,似乎還添了數卷金部文卷。
雷光下,星魂孤寂的倒影讓人心憐,我沒有回應他,而是施咒幻化成衛留蕸的模樣,默默地看著他。
星魂感覺到施術的氣息,猛然抬眼看向我,他有些疲乏的揉了揉腦門,說:「我說你可以退下了。」
我低著頭,看著以幻形法遮掩的衣料,想著他真是累了,竟也沒看出個端倪。我默默的站在門旁,星魂看我沒有要走的意思,沉嘆一聲,只道:「罷了。」
雷聲隆隆,望著星魂專注的臉龐,浮動不安的心緒逐漸平息,我甚至想著,就是看他安穩的入睡就心滿意足。
一個時辰過去,雷鳴依舊,卻不吵耳,更不鬧心。
星魂放下公務,走到了窗台旁默默的看著遠方,頓時,他偷偷的將頭探了出去,往我房間的方向望去,即便暴雨傾瀉而下也未淋濕他的毛髮半點,以他的實力在狂風暴雨中,走在路上晃一整天也沒有水珠能碰得上他。
星魂看了一會後便離開窗邊,徑直向門外走去。走沒兩步,我偷偷在後頭看著他走到我房門外,安靜地看著已經熄燈的臥房。
他伸出手欲敲房門,纖白的指頭又落在門前幾吋,就這樣重複的動作來來回回三兩次,感覺他已經在我房門外站了好幾刻鐘了。有那麼一瞬間我想卸去幻形法,直接拉著他,催他回床上睡覺。當我這麼一想,心裡頭不免被這大膽的想法給嚇得哆嗦,如今的星魂已不是當初七八歲,甚至十二歲的孩童,我亦不是沒有肉身的虛影。
想當初在沫泣的記憶裡,她的夫君吳善曾催促她上床歇息,而上床之後,咳咳咳,就是夫妻間的家務事了。
但是!
現在我與星魂是清清白…清,輕輕……輕輕擺著上司下屬的從屬架子不是。猶記得阿鈴曾說在他們那頭,男女情誼大方表明,就是喜歡,就是愛著,一字不漏地都說出來了也不羞人的。
虧我白日還信誓旦旦說什麼珍惜眼前,珍惜你個王八啊瓏月?!你就是不敢說,不敢說出那心尖坎上懸著的字!
想不到回到了現實,竟比做鬼時還要在膽小個十來倍,就是這腦殼裡裝的害臊無人可見,卻實實在在的影響著我。
糾結未了,星魂安靜回到自己的房內。我默默地跟了上去,卻沒想還沒進門,星魂竟直接停在門口處,令想進去的我險些與他相撞。
他轉過身看著我說:「我要就寢。」
我抿著唇,把頭壓的低低的就是不講話,要是我一出口還不即刻露餡。
「衛無,我說我沒事。」
「瓏月已醒,我的傷也托她的福已完全痊癒。」星魂語氣有些無奈,我聽著他說,仍舊低著頭不敢抬起。
星魂似乎是見我沒反應,他語調一轉,冰冷的質問道:「怎麼,這幾日龜毛謹慎的不夠,現在連本座就寢也想過問?」
我見星魂有些惱了,摸摸鼻子識相的往後退了幾步欲先退下;反正人看也看了,確認他無事後也沒什麼理由在糾纏他。
片刻,當我正要離開時,星魂又反常地把我叫了進去。我這是前腳還沒離開他的視線半步,又進了他的房裡。
莫非他改變主意要罰我?!
星魂怪乎地坐在小桌前喝了幾口茶,閉目養神一會後,漫不經心的問道:「你說瓏月是否睡下了?」
我學衛留蕸俐落的點頭,星魂挑了挑眉,再說:「你知道我不喜人碰我,尤其是腰腹之處。是以過往更衣等繁雜庶務皆由傀儡打理。」星魂一邊說著,一邊解開他身上華貴的紫絹外袍,只留下他淺灰色繡有金線星紋的澤衣與襯褲。他輕快地晃到床前,張開雙臂,並將頭微微往我這方向轉了過來,說:「過來幫我把帶子解開。」
在這瞬間我傻了,幫他寬衣解帶?說好的不喜別人碰他呢?!更遑論是碰他腰際?!
剎那我能感覺星魂犀利的眼神盯視著我,我緊張得咬緊牙,攥緊拳頭,故作無事的走到他身旁,伸出強忍顫抖地手要拉他腰間的帶子。
當我專注在眼前的金縷玉帶,周身忽感一縷冰涼,星魂用手往我左臂輕輕一拉,他的陰陽傀儡絲迅捷地纏繞我的左半身。
眨眼間,一瞬的天旋地轉,我被他按在了鬆軟的床舖上。他一隻手扣住我兩隻無處安放的手腕,另一隻手往自己的腰部挪去。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ns 15.158.61.41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