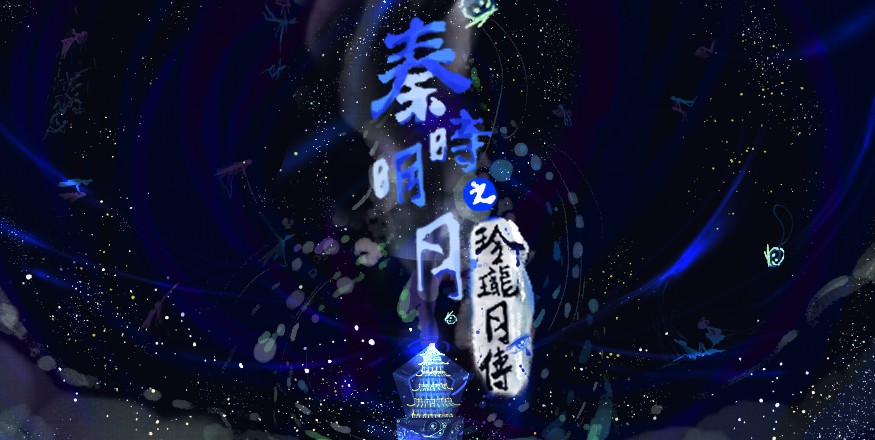星魂輕輕拉開他腰間最後一道防線,白皙精瘦的上身猛然入眼,有那麼一剎,我覺得我又要死了。就像在夢中意識消失般直接失去意識,不過這次我想我是要被嚇死,羞死,氣死了。
「怕了?」星魂壓聲低語綿而不嬌,有如鬼魅的呢喃刺激著每寸神經。他有些用力的握緊了我的手腕,藍眸裡透出以往得意的狡詐。
我不敢點頭,就怕這一點幻形法也把持不住了。
星魂靜默地盯著我,我看著天花板依舊努力的維持鎮定。就這樣我們二人沉默的狀態持續了一會,忽地,星魂再次動作,他將頭往我的耳畔靠過來。在這短短的瞬間,胸口幾近窒息,腦中彷彿迴盪著自己狠狠咬牙的咬合聲與匹敵雷鳴的震耳心跳。
「怕了就好,怕了就不會再傻呼呼的闖入男子房裡。」星魂一說完,耳廓的肌膚傳來一抹柔軟的溫熱。也不知是有意還無意,在他剛剛靠在我耳畔細語時,輕薄的唇就這麼剛好的碰了上去。而藏在他軟唇上的秘密,就是一技久違的定身術。
「你可知輕視人性的欲望只會有一個下場。」星魂頓了頓,離開我的耳旁凝視著我,一臉你早已被我看穿的神情。他嘴角的壞笑,眼中張狂的傲氣,陰陽怪氣的話語,諸多細節透出優越的好勝心令心中莫名燃起一股怒火。
我看著他獵鷹般的鋒利視線,想著剛才一顆心實實地就差那麼點原地停止,就是魂兒也差點被他給嚇飛了,而他,而他現在這樣不尊重人的教訓,倒是把心中最後的一絲羞恥與緊張給氣跑了。
好,好啊,好得很啊!星魂!
我怒瞪星魂饒有興致的壞笑,默默扯了扯嘴角。星魂邪魅淺笑,凝視著我半刻,方才解開我身上的定身術,語帶深意道:「等等出去後,可別忘了替我注意"瓏月就寢"的狀況。」
我不甘的趁他分心時學他反手一扯,一技定身術將他壓在身下,讓堂堂左護法嘗嘗我的感受,感受突然被人壓在身下的不滿與慌亂。
「星魂大人所言即是,但,您莫非是忘了,我現在也是一名血氣方剛的熱血男兒。」即便我壓低聲音仍舊不像衛留蕸。不過,那些都不重要了,他既然早已看穿我,還故意捉弄我,一想到他得意滿滿,用鼻恐看人的強硬態度,我這是氣不打一處來。
在床上講求的是人人平等,天底下可不是只有女子會受人壓制;男人也是同樣。
當初在甘羅身旁學了四年,跟在星魂身邊又學了一年半載。就是名師出高徒,在他的耳濡目染下,這一身陰陽怪氣,唇槍舌劍的功夫我是掌握的分毫不差。
「大人適才這般主動讓衛無受寵若驚。大人有龍陽之好,我不會多言半句;只是大人與我相識多年,就是有這等心思難道不該坦承相告,如此既是尊重了我,抑是尊重大人心中不敢多言的心思。」
星魂雙目瞪大,不敢置信會被我壓在身下。他的眉間因受驚而微抽幾下,驚詫道:「坦承......相告?」
沒想到等星魂認清現狀,他俊美的臉蛋倏然變色,就是比外頭狂風暴雨的暗雲還要在黑上幾分。他輕哼冷笑,頓時腦中恍然憶起為何他會被我取叫冰塊了。
眼前這位冰塊若不看他心狠如冰石的作風,就是他發起脾氣的陰冷淺笑令人感到凍心徹骨。就是曾經差點被他一刃穿心的我,看著此刻被我壓在身下的他,他嘴上的笑,眼眸裡的寒,從頭到腳無一處肌膚沒有雞皮疙瘩。
「是,是該坦誠......。」星魂收起笑容,略感同意的挑了挑眉。我本以為他的冷笑就夠恐怖了,現在看看他提起興致,一肚子壞水的輕佻樣才是真的令人寒毛直豎。
他不會是要假戲真做罰我扮成衛留蕸吧?!
衛留蕸素來跟著星魂辦事,如此想來,他難道反悔想藉此正大光明的阻斷我勸說高漸離的行動?!
冷汗從臉頰旁滑落,我對他就是不服氣,更不服輸,又怕繼續與他糾纏壞了事。糾結半會,我卻始終未能明白一件事。眼下被我壓在身下的是當初以奇才勸服趙王,功高氣傲的天才少年。這樣的他,怎會如此容易與從容地甘願被我一顆小石子給牽制住呢?
思緒未定,後背忽感冰涼,我凝聚內力欲回身防禦,但當我轉身的瞬間任何可能都消失了。我身軀僵住,一動不動。
又是這精準到令人發寒的定身術。
就在剛剛我們二人你一句我一語之時,星魂的陰陽傀儡早在他的操控下,一聲不吭的繞到我的背後。本來是死物的傀儡哪會有什麼氣息,更不用提就算有施術的氣息也會被星魂給掩蓋過去。而星魂他與傀儡在這麼短的距離能夠施法,藉由傀儡之手對我施以定身術。
陰陽傀儡,操物控心,以陰陽術法驅動某物某人供人差遣、能當替身擋暗箭、充當保命牌。若距離夠短,又是可以藉傀儡絲發動攻擊。這麼厲害的一個術法,偏生我就這麼給他忘了去,更該死的是哪不招惹,偏招惹到這位堪比偃師的奇才。
所以,怎麼最初的初衷從見他好好入眠,到了現在搞得像個冤家似的?
星魂藉由傀儡解開自己的定身術,我瞇起眼看他優雅地坐了起來,心裡盤算著趁他不注意時解開自己身上的定身術。
他沒有將我從他的身上推開,反而由著幻形成衛留蕸,高他七八吋的我坐在他的腿上。
此刻我們二人就是一尺多的距離,近到只要稍微用力,呼出的氣息就能打在彼此的臉上。這畫面別說太過震撼,就是有一種成羊騎在狼仔身上的畫面感。
「沒有坦誠"相見"是我的不是。」星魂難得道歉,語帶戲謔,聽他胡說的連我都傻了。
「坦!承!相!告!」我一字一句,分分明明地提醒他,他薄唇淺淺揚起,回道:「哦,你素來真誠待人,知曉何謂坦誠相告;我心坎裡有些芥蒂,不懂何謂坦—誠—相—告。」
這利語真是真真實實的戳在我的心頭上,是,我一開始幻化成衛留蕸騙他是我的不是,但他也不該這樣強硬的就給人壓上床去!
怪裡怪氣說一堆,好聲好氣的解釋不好嗎?!非要把我的心綁在峭壁上,在狠狠地晃它,戳它,直至最後嚇得我是半點都不敢妄動,就是想讓我服服貼貼地在他耳根前服軟。
臭冰塊,我告訴你,門都沒有啦!
「我錯了,有話好好說。你,你別給我什麼坦誠相見。」
內心的激烈嘶吼出了口,就是軟柿子一顆。我窩儾的挪開視線,不去看星魂從容拉開衣袍的手,想真真正正的"坦─誠─相─見"一番。
星魂聽到我的道歉後停下手邊的動作,他劍眉輕挑,深沉的凝視著我,嚴肅道:「錯在哪?」
我抿緊唇,雖是不滿仍是識相認錯。
「假扮衛留蕸騙你,還有……混入你房間。」
「可是!」我激昂怒吼,就是認錯也不能就這麼結束了。
「我進門前敲過門了,你又將我誤以為是衛留蕸,我只是……只是。」我的目光不安的左右游離,思量好一會。星魂看著我,倒是安分的等我回答。
「我只是想看你睡覺。」
「睡覺?」星魂愣了一剎,朗聲輕笑,這一笑令心跳漏了一拍。他蛻去表面的邪氣與高傲,留下最真實的慵懶與疲乏。
他往窗外的暴雨雷鳴瞥了一眼,眼眸低垂,思索片刻。當他再次與我對視,臉上顯露出了惆悵的無奈,我能感覺到他抓著我的手有些不安的輕顫。
「雷鳴響遍雨化血,森森白骨無人見。」
「你目睹那日了?」
不用星魂多做解釋,那日,那日便是他人生的分歧點,是成就星魂,犧牲族血的慘痛之日。
我輕輕點頭,視線落在他潔白的胸口。他與衛庄死戰的傷真的好了,即便我深知萬愈法的力量強大,卻不免被他恢復的毫無痕跡的模樣給震驚。
「衛無在本座面前犯錯可是要領罰的。」
我倔強的抬起頭,眼神藏著委屈,嘴角落寞下垂。我解開身上的幻形法,摘去冰清面紗,坦然道:「一人做事一人當,只要不要太超過,我,瓏月,甘願領罰。」
「是嗎。」星魂語中的酥軟夾雜著疲態的鼻音,他緩緩摟緊我的腰,素指拂過我臉頰的青絲細細把玩。
「但,你不是衛無。」
星魂話音剛落,身上的定身術突然解開,一股溫熱將我包覆。他緊緊的抱住我,將頭蹭到了我的耳根處。
當我默默地回抱著他,腦中想起甘羅親暱又撒嬌的蹭抱。他總喜歡在相擁時蹭到他人的耳根後頭,喜歡把整顆頭埋進了孰悉的氣味與溫度裡頭。
只不過,沒想到我又能再次感受到如此令人心滿意足的擁抱。
「別怕,都過去了,我沒事。」星魂在我耳後沉沉呢喃,我鼻頭一酸,將頭貼在地肩上默默的忍著淚,不發一語。他輕撫我的頭在到我的背,就像是在安撫小孩一樣溫柔的讓人感到心安。他鼻息間吐出的熱氣在脖頸上停留,讓體內逐漸躁熱起來。
「星魂。」我止住淚水,堅決喚他的名字。
「只要我還活在世上的一刻,我便陪你一刻;只要這份心跳仍鮮活的跳動著,為你而跳動著,你就不會孤單了。」我抱住他,讓他的臉靠在我的胸口前感受這份心跳與溫度。我感覺到星魂的身軀微微發抖,他呼吸有些急促,沉默了一會,耳廓早已紅通通的。
「滿口胡話,你覺得我會讓你出事?」星魂側臉窩在我懷裡,他的語氣不同以往的沉著,倒是添了幾分沉溺與淘氣。被他突如其來的軟語安撫,我整個人血脈賁張,整顆心像是要跳出來了。
「這話是我要說的,我才不會讓你出事。」我故作反駁,內心的激動澎湃不已。
「我知曉你的陰陽術進步許多,卻沒想我竟未能即刻識破你的幻形法,多日不見,你這顆傻玉倒是長進許多啊。」星魂離開我的懷裡,白皙的右掌在我臉頰旁婆娑。
「傻瓜,睡了。」
正當我情緒激動快要把持不住,我聽見他的綿綿細語,緊接著就是舒心的芍藥香縈繞在鼻尖,我未去抵抗星魂的控心咒,而是由著他溫柔地將我帶入夢鄉。
頓時眼皮一鬆,直倒在他的懷裡沉沉睡去。
12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ghC5cfCc1O
*
12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TfT65s2aAn
半夜三更,桑海城濱館外頭的雨是一刻也未停歇。
星魂謹慎地脫去瓏月的鞋,溫柔的將她安放在床上,並且呵護備至的替他蓋上棉被。他看著瓏月沉睡的眉眼,不由自主的傻笑起來。他凝視了瓏月許久,即便他身心疲憊,也不想打斷眼前短暫的幸福。
「你可知你今日唯一的錯處非是假扮衛無,混入我的房間……。」星魂將嘴靠再瓏月耳旁低聲呢喃。
「而是—令我亂了方寸,你不曉得,這般忍耐與當初修練幻境訣的蝕心之苦比起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你說,我該拿你如何是好?」星魂滿眼柔情,他克制著幾近無法控制的慾望壓聲輕語。
一瞬的雷暴響起,星魂的頭抬都未抬,輕輕彈指,窗門立刻無聲掩上。
「三道禁制中,五君已死消去一道。按照五君死前所言,剩下兩道禁制的容器一為東皇閣下,其二為東君,昔日的護法,有著千年難遇的陰陽術資質的奇女焱妃。」
「當初五君在死前曾言明禁制消除,必須奪取容器性命。若神女山鬼與蜀山餘孽當真有關,那麼他們許會留下其他辦法能夠解開禁制。況且,一位與蜀山關係頗深的神女,話裡真假還須謹慎以對。」星魂瞇起眼,細聲呢喃。
星魂從床邊站起,有些猶豫與緊張,最後還是伸手輕撫著瓏月的臉頰。
片刻過去,他拿定主意傲然自語道:「哼,是了。」
「躊躇不前,惦念往昔並非我的作風,唯有緊握良機,主動出擊,方可羅羅玉心,心守瓊玉。」
「從今往後我不會再放開你了。」星魂目光灼灼的凝視眼前熟睡的瓏月,他握緊瓏月的手,在床旁邊焦躁地坐了許久,內心經過漫長的掙扎後,方才在瓏月額頭上留下一抹輕吻。自己則紅燙著臉,速速穿好剛褪下不久的衣袍,往陰陽家看守的死牢前去。縱然星魂方才紅著臉,心頭撲通亂跳,但當他一踏出房門,這些模樣轉瞬消失在身處高位,乖張高傲的左護法身上。
位於桑海城的將軍府死牢內,星魂睥睨一切優雅的坐在牢獄前的椅子上。他面前的是蜀山的虞淵護衛,石蘭,而她正好是當初圍剿墨家等人時,從紫焰火海下倖存的唯一一人。
「讀心術對你起不了作用,你是蜀山的虞淵護衛?」星魂從容問道,陰邪看著地上冷面以對,不言不語的石蘭。
「據說蜀山虞淵的巫族血脈中,有人生來對陰陽術具有極好的抵抗力。撇除一流高手,心性堅定,心中自有屏障,蜀山之人有自成的一套巫術,其咒法與陰陽術頗為相似。」
「我託人治療你的傷等你甦醒,可不是為了看你浪費我時間。」
星魂纖白的素指扯動纏繞在石蘭身驅上的傀儡絲,石蘭眉頭緊蹙,雖然痛苦地躺在地上,卻是堅毅的沒發出半點哀號聲。
「大人,何必與她多費口舌,讓我把她的肌膚一寸寸給燒了去,我就不信她還不老實招來。」一旁的大司命踩著妖嬈的步伐上前,她看著自己靈活艷紅的指頭,陰冷笑道:「畢竟,在我的印象中,這方法可從未讓我失望過。」
星魂聽聞,抬手示意大司命可以先行離開。
「大人?」大司命疑惑提問。
「虞淵血脈非你可應付,你先下去。」星魂說罷,大司命不再多言恭敬的退了下去。
石蘭見狀,吃力的從地上爬起,她瞪視著眼前目空一切的星魂,冷聲道:「讓我與你身邊的瓏弟子見上一面,我就告訴你虞淵巫族咒法的卷文位置。」
「說。」星魂冰冷道。
石蘭見星魂豪不退讓,磨耗半個時辰後,才無可奈何的忿忿答道:「在千言閭,聽聞當初蜀山遺物有部分皆被千言閭閣主以重金收了去,卷文上印刻古文無人可以看懂,即便被人奪得亦不過是無用之物。」
星魂聽聞後勾起嘴角,思索一會,冷哼的傲然答應道:「無用之人唯當無用之物。」語畢,星魂起身向門口走去,他在離開前只留下一句話與石蘭。
"以不交談為前提,給予他與瓏月交談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刻鐘。"
半個時辰轉眼過去,石蘭依附在死牢冰冷的牆面上。她不曉得等了多久,直到外頭的門一開,瓏月神情冷淡的走進來,從容的坐在牢獄前的木椅上,她的紫眸低垂對上趴伏在地,神態虛弱的石蘭。
「神女大人?!」石蘭驚呼喊道,拖著一身病態死命的也要爬到牢籠前一賭瓏月之貌。
石蘭看著與畫像上長得一模一樣的瓏月,並從她身上感受到一股不凡的力量。她越發堅信她便是蜀山神女,是從前巫族祭壇中密藏畫像裡的神女。
瓏月瞇起眼,神色淡漠,不發一語。石蘭見狀想起星魂說的話,只得快速將實情相告於瓏月,在此期間,瓏月明白則點頭;反之搖頭。
石蘭急匆匆的講述,完全沒注意到瓏月冷漠的神態,她虛弱地將對瓏月道出,自古以來蜀山巫族的祭司頭領以口頭傳授的天機。
"玄女斬扶桑,斷三界。墮神集萬人之力,禍亂天地。神者相抗,相消相融,無靈存依。"
"承天運,集七源,血染地,人比天。七魂聚,萬法開,墮神出,滅天地。"
「贏政不死,虞淵下的災厄,滅天地之墮神必將重見天日。墮神再出,大地將陷入劫難!」
「承天運,集七源。如今贏政將六國一統,若神女不出手誅殺贏政,墮神必將...。」
瓏月未聽完石蘭所述,她臉色陰冷的起身,打算離開死牢。石蘭看著正欲離去的瓏月,用盡全身力氣才將她心中所想大吼而出。
「爺爺曾說神女清心淨神,引領人們,平復洪難,驅散黑暗!」
「小虞從無他求,一生在蜀山恪守守護虞淵之責。而大秦霸主,贏政與陰陽家聯手屠戮我族,毀我家園。」
「我深知自己的弱小無可報滅族之恨,滅家之仇;但唯有一件事,小虞願以命相求於神女。當初虞淵遭屠,我與一名至親失散,他名虞子淵,不只是另一位虞淵護衛,更是我的兄長。只求神女以無上法力幫我找回兄長!」
瓏月瞇起紫眸,冷漠地看著叩首跪地的石蘭默默流下淚水。她在原地思索半刻後,無視牢中少女的哀聲哭啼,頭也不回的離開死牢。
走到外頭,瓏月朝邊上的陰陽家弟子冷道:「看好她,無本座允准,任何人皆不可動。」語畢,瓏月負手踏步,散去身上的幻形法變成了冷傲的少年國師,星魂。
「墮神?」星魂煩躁道。
「嘖,是我太高估他們。」星魂惱怒的咬緊牙根,無法接受從石蘭口中聽見毫無邏輯,難以理解的荒唐話語。
「沒想到蜀山的人腦子盡裝些難以證得的......。」星魂輕蔑地喃喃自語到一半,停下急促的步伐,腦中靈光乍現,開始重複想著石蘭所說"七魂聚,萬法開",又想到五君過去所言"紫焰覆命,斷生三界",這些零散的訊息都間接指向三界之門與蒼龍七宿。
星魂在眨眼間將腦中的訊息完全梳理後,露出邪魅的淺笑。他命人備了馬車,在暴雨滂沱的夜晚,興致勃勃的回到桑海城賓館。
12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gP8amnibfH
*
12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0zznd1oN8H
小聖賢庄裡有一處私人的宅院,裡頭綠意盎然,草藥滿布。此處普通弟子無緣進入,能夠進到裡頭的除了尋常打掃僕從、弟子,以及儒家首席弟子外,也就只有儒家三位當家伏念、顏路、張良。
宅院裡的主人為儒家高人,抑是儒家三位當家的師叔,荀子。
天色灰暗,外頭的暴雨將宅院裡的花草摧殘一番,荀子看著自己珍愛花草的慘況,摸了摸臉下的長長白鬚,一臉不滿的對著身後一觸即發的墨家與流沙人馬道:「利雨兇兇,利語急急。」
「我看你們兩馬人嘴皮堪比狂風暴雨,攪的人不得安寧。流沙之首衛庄的傷,據我所知,在這天下恐只有醫仙端木蓉能治,子房將墨家帶來此處經我同意,而流沙不請自來,一點禮數都沒有。」
「流沙的毒醫是否救治墨家端木蓉我不多問。若流沙若不救,請早早離開我這院子,別擾了今夜的安寧。」荀子冷肅道。
「一向龜居齊魯之地安穩授業的儒家,何時熱心關切起當今反賊來了?」一旁的白鳳站在赤練前頭,他皺眉不滿的質問荀子,毫不將他的名頭放在眼裡。
赤練伸出一隻手擋在白鳳前頭,毫不猶豫答道:「一個月。」
「給我一個月的時間,我便可治好端木蓉。」赤練冷道。
荀子聽聞伸出手掌往門口方向擺,示意墨家等人引領赤練前往端木蓉養傷的客房。
兩方對峙落告一段落,赤練答應相救端木蓉。她與墨玉麒麟留在荀子宅院裡頭,而白鳳雖臉色慍怒,卻仍將重傷而昏迷不醒的衛庄給抱到荀子院內的另一間客房靜養。
暴雨持續了很久,當眾人都散了之後,荀子坐在書房裡,房裡飄散淡淡菊香,張良則恭敬的坐在他對面。
「桑海城近日暗中流傳一種能夠安神,舒心的密藥,此藥服用過多,身散異香。無論是服藥者,抑或聞香人,若未習武用運內力抵禦便受異香所迷。」
「以我觀之,受異香侵擾後,雖看似未有大症狀,卻會使人的脾性轉變為柔和,百依百順任人說動。其藥詭異,就連小聖賢庄內也能聽到些許風聲。」
荀子說到一半,盯著張良身上的淺藍色外袍,瞇起眼,又問:「子房,我記得你身上這件青絹外袍乃舊物,最不合你的眼,平日裡也未見你穿過一兩回。想著白日你衣杉裏頭濕漉漉的,外袍卻乾淨無比。現在換了內襯,外袍倒是穿得安穩。」
「種種奇怪行跡,莫非是與你今日去桑海賓館探訪密藥有關?」荀子白眉輕挑,狐疑問道。
「若真是如此,你體內的內傷想必也與此脫不了干係,陰陽家奇詭術法造成的內傷可花了我不少心力。」
張良一想到白日裡發生的事,嘴角不自覺的勾起一弧優美的弧度,荀子在旁看了張良的模樣,眉頭緊蹙,趕緊低頭喝了幾口熱茶。
「謝師叔惦念,子房身上的傷經過師叔的調養已經緩和下來,師叔不必太過擔憂。」
「至於白日發生之事,不過恰遇故人,所幸以禮待之。」張良語帶深意的回道。
「師叔,子房冒昧想請教一件事。」
荀子聽聞張良突然嚴肅提問,沒有抬頭,兩顆眼珠子往上瞅了一眼,向張良表示他正聽著。
「上古神話中充斥各種神鬼之說,曾有九天玄女授黃帝兵書,又是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種種故事皆紀載諸神臨世與世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難不成,這世上當真有超越凡人的神力存在?」
荀子聽聞愣了一剎,他緩緩放下茶杯,看著墜入杯底的茶梗,平淡道:「韓非也曾問過我同樣的問題。」
「儒家三位當家裡,掌門伏念穩重;二當家顏路淡漠;而你,唯獨你這古靈精怪會問這種不是當家該問的問題。」荀子嘆了口長氣,似怒非怒的看著張良。張良眉頭抽動,莞爾一笑,荀子看他有所求問的模樣,實在是拿他沒辦法。
「唉,當初的事彷彿是昨日一樣,猶記得他帶著一個模樣不凡的銅盒,神采奕奕的來尋我。如今想來,人已去,物已失,無論是韓非抑或諸侯之間流傳的七個銅盒,最終依舊盡落君王之手。」
「子房,你有事瞞著我。」荀子冷肅的看向張良,張良鎮定地看向外頭的風雨,緩緩道出遇見瓏月之事,以及瓏月數十日前隻身匹敵衛庄,心頭遭赤練劍貫穿,身染劇毒,如今卻毫髮無傷的出現在賓館。
「想不到陰陽家竟有如此神人,當今陰陽家除左護法星魂以及在外遊歷的楚南公外,就未聽聞過哪位男子修為抑或能力如此了得。況且,據我所知陰陽家之人縱有通天本領,亦未見得會輕易出手。」荀子慢捋白鬚,思量道。
「呵呵。」張良忽地淺笑,荀子眉頭微蹙,認為張良在與他玩笑便有些不滿。
「師叔誤會了,您口中的"他"是位有趣的姑娘。」張良從容回應,荀子聽聞兩顆眼珠微微睜大,有些不敢置信。他看著張良的神情,震驚道:「如此說來,不知是幸抑或不幸,流沙之主的傷依我觀,斷筋廢武,傷勢之重雖使人於生死間徘徊,卻遲遲未能取其性命。」
「如今流沙自身難保,將軍府的死牢唯一的出口也遭陰陽家與蒙恬的重兵嚴防死守。」張良轉移話題,嚴肅道。
「前些日子墨家盜王盜趾雖出手營救高漸離,卻也難過陰陽家讀心術法的關卡。眼看高漸離行刑之期近在眼前,若大局已定,木已成舟,高漸離的犧牲必將成為墨家勢力的醒神棍,墨家巨子必得韜光養晦,以待來日扭轉之機。」
「你若曉得木已成舟,難有轉機,又何必與那位姑娘說了那麼多?」
「據我所知儒家三當家可不會多說,多做無用之事,這可不像你啊,子房。」荀子莞爾一笑,故意將話題給帶回瓏月之事上。張良聽聞,恭敬拱手,一臉倦容道:「師叔,天色已晚,子房就不叨擾您老人家了。」
張良行了禮後迅急離去,完全不給荀子留一點機會在繼續深問下去,獨留荀子一人獨坐房中,悶悶道:「子房啊子房,你在數日前相救墨家之舉,已經使得你師兄伏念動怒。現在你又有意將流沙一併帶上。不得不說,我偶爾還是希望你這機敏的腦袋能夠放緩一些啊!」
「看我這幾日操心的,泡壺茶都走味了。」
荀子搖了搖頭,看著杯裡的茶水品茗幾口,又埋怨道:「明明是苦澀交融,卻會感到莫名的甘甜。唉,年輕人果然就是年輕人。」語畢便將茶水連同茶梗一同飲盡。
ns 15.158.61.55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