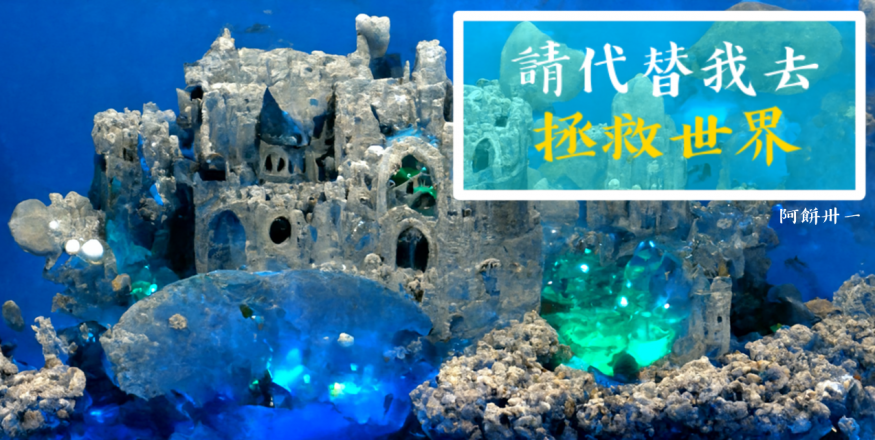薇奧拉他們在今天的歷史課上學習的是關於巫師的歷史。
在已經久遠得無法考據真實性的資料中,巫師的誕生和世界樹息息相關。
一本古代神官紀錄提到,因為開始農業發展的人類進入魔獸的棲息地,每天都有人死在魔獸爪下。即使如此,日漸增加的人口卻令人類不得不承受著犧牲繼續擴展領土。
當時人類還是以部落的形式生活。而把人類從對魔獸的恐懼中拯救出來的,就是其中一個部落的神官——薩茲‧阿斯楚。傳說薩茲從懂得表達自己的那天開始,每天都會向神明祈求人類能過上不必再擔驚受怕的生活,能夠在這片大陸上得到安居之所。
彷彿是回應薩茲的禱告,當薩茲從父親手上接過神官職務時,世界樹的種子伴隨著彩虹落到部落附近的土地中,瞬間發芽生長。幾個呼吸間,它就已經擁有一棵幾百年的老樹都未必能達到的粗壯。
一枝發著金光的樹枝伸到薩茲面前,脫落在他的手上。神明的力量透過這枝世上第一枝魔杖降臨在人間,藉著薩茲的手拯救了這個人類自己都快要放棄希望的世界。
變得強大的薩茲並沒有把世界樹據為己有,反而慷慨地給予了所有人類到世界樹獲取魔杖芯的機會。而挑選魔杖芯時不可傷害世界樹的規則,也是因為當時的一個悲劇而訂立。
在最初,世界樹已經擁有挑選魔杖芯主人的靈性。它會在所有來到它蔭下的人面前垂下枝條,為那人分裂出最適合他的魔杖芯。
可是不是所有人都甘心接受世界樹的安排。那些人認為世界樹總是給予他們幼細、純色的樹枝,為什麼不直接把它的彩色樹枝送到他們手上呢?
你看,薩茲拿著的那枝比他矮半個頭的魔杖,魔杖芯不也是發著金光的彩色樹枝嗎?他們和他一樣擁有巫師的能力,為什麼得到的魔杖芯不如他?
而在這麼想的人之中,有一個過於渴望力量的人趁所有人都入睡時,拿著斧頭砍下了世界樹的一根旁枝。受到傷害的世界樹發怒,向那人降下詛咒。
受到詛咒的人從此消失於人前。第二天其他人再來到世界樹下時,看到的就只是一棵枝幹亂舞,不允許任何人再進入它蔭下的巨樹。
從神明那裡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薩茲乞求世界樹的原諒。世界樹最終平息了它的怒火,卻不再主動為人類提供樹枝,而是任由樹枝從高空掉落,讓人類必須冒著生命危險才能獲得自己的魔杖芯。
見識到人類貪婪一面的神明也對人類設下限制,只有少數人才能擁有控制魔法的能力,成為能獨自和魔獸對戰的巫師。
薩茲一生帶領著巫師們為人類擴張領土,這也是普索索克新生們參與的滅魔儀式的由來。
據說從魔杖的外表,就能看出薩茲所除滅的魔獸數量有多麼誇張。雖然已經無法找到實物,學者發現在另一份紀錄中提到因為魔杖芯吸收的全是魔獸的血肉,薩茲的魔杖和其他人的都不同。
他的魔杖就像一枝包著魔獸獨有紫色血液的水晶,其中的血液時刻都在流動,間中會露出其中金色的杖芯。除了血液,魔獸的屍體還為薩茲的魔杖添上不同顏色的花紋,骨頭的白、肉體的淺紫,還有各種顏色的鱗片、利爪、皮毛……
那世上第一支魔杖的華麗,是現在所有人都想像不到的。除了薩茲的魔杖以外,再也沒有出現過能吸收所有魔獸的屍體,並為己所用的魔杖了。
神明是為了讓巫師從魔獸手中保護人類,才會賜予他們力量。即使現在巫師也會參與人類國家之間的戰爭,但是在魔獸威脅人類時,他們也必須放下彼此的對立,為人類挺身而出。
親眼見證過戰場的薇奧拉,不得不承認巫師確實是把這項任務刻了在靈魂中,至死都在為反抗魔族、保護普通人而戰。
雖然也有巫師寧願躲到偏僻的鄉鎮也不願接受上戰場的命令,有些甚至仗著平民需要他們的保護,趁機讓自己過上比皇帝還糜爛的生活。
但薇奧拉見到的更多是像威瑞什學長這些願意站到前線的巫師。他們和那些家人生命受魔獸威脅、主動擔起了前鋒角色的平民合作,從魔族手裡奪回了不少領土。
這也是為什麼和薇奧拉一樣只願意躲在戰場後方的巫師會受到許多人的白眼。
他們明明擁有和魔族一戰的力量,為什麼要逃避呢?
不過那些巫師之所以能逃過戰爭,也是因為他們不像那些天之驕子。他們身上沒有背負著長輩的期待,沒有享受過最高級的待遇,也就不必以自己的生命報答別人的恩情。
他們可以做一個自私的巫師,只關注自己要怎麼在戰爭中存活。
想到這裡,薇奧拉嘆了口氣,倒在床上。
……她現在也是那些天之驕子的其中一員了。
可想而知,七年後她要逃過兵役,就不像上輩子那麼輕鬆了。
她是真的不想成為別人眼裡的英雄,尤其是在明知戰爭的結局會是魔王自爆,全世界——不論是人類還是魔族,都會滅亡的情況下。
要開始為逃避戰爭打算了嗎?她實在不太想為所謂的人類大義付上性命。就算水神給予了祂的祝福,她也只是一個不敢前往戰場的膽小鬼而已。
可是逃走也沒有那麼容易。入學時所有新生都要在一塊刻著所有學生名字的石碑上留下印記,讓導師們能看到學生性命有沒有受到威脅,也能在學生失蹤時找到學生的位置。
上輩子她只是一個普通的第二班學生,在近八十人的同班級生中成績也不算突出,這才得以趁亂從戰場中逃走。可是她現在卻進入了一級只有十多人的第一班,怎麼可能再像之前那樣蒙混過關?
「薇奧拉,不是說要一起烤餅乾嗎?我準備好材料了哦!」門外傳來嘉蜜格兒的聲音。薇奧拉從床上坐起來,拿過桌上的髮圈束起頭髮。
……七年後的事,她現在煩惱也太早了。
「薇奧拉!」
「來了!」
因為對學院還不熟悉,一年級生們也沒有很多消磨課後時間的活動。嘉蜜格兒便和兩位同班好友約好了一起在帕普吉大樓的廚房裡製作餅乾。
說是一起,其實大部份功夫都是由經驗豐富的嘉蜜格兒負責,薇奧拉和澤法斯都只是幫忙給餅乾做做造型、用巧克力裝飾一下而已。
「完成啦!」嘉蜜格兒把放涼的餅乾分別裝進三個袋子,開心地鼓掌。突然,她想起了一件事︰「對了,有些餅乾裡放了咖啡,莎希你記得不要吃哦……還是我先把它們拿出來比較好?」
在一起生活的這段時間裡,嘉蜜格兒發現了澤法斯不能吃或喝和咖啡有關的東西。每當她不小心碰到了這些東西,第二天的臉色總是會比平常更蒼白。
偏偏剛才她分餅乾的時候沒有注意,等袋子封口了才發現每個袋子裡都放了幾塊咖啡餅乾。
被她抱歉的眼神弄得不自在的澤法斯拿起一袋餅乾,放進腰間的空間袋裡︰「不用了,麻煩!」
見澤法斯不在意自己的疏忽,嘉蜜格兒高興地抱住她。澤法斯推了她幾下後,也就任由她抱著了。
並排的兩張書桌,左邊的黑髮女孩專心地拼著從家裡帶來的立體拼圖,右邊的綠髮女孩則是閱讀著筆記本,時不時拿起筆在上面寫字。
寫著寫著,綠髮女孩伸手從袋子裡拿了一塊餅乾放進嘴巴。咬了一口後,她皺著眉停下動作。
……拿到咖啡味的了。
「叮叮——」右邊書桌上的鬧鐘響起,澤法斯慌忙伸手按停。慌亂之中,她手上那塊咬了一口的餅乾被她順手放回了袋子裡。
她想把桌上紅色封皮的筆記本合起,卻在完全合上前看到其中浮現的字跡。看清它們寫了什麼後,她扭頭詢問薇奧拉︰「你要去見學院長嗎?」
「什麼?」心神都在拼圖上的薇奧拉沒反應過來︰「見學院長?我嗎?」
回應她的是澤法斯看白痴一樣的眼神︰「不然呢?這裡還有別人嗎?」
「沒有……只是,學院長會有空見我嗎?」
澤法斯又確認了一下筆記本上的字,肯定地回答︰「有呀,畢竟是他自己要求見你的嘛。總之你要去嗎?」
既然是學院長的邀請,那就不能拒絕了。
雖然想留在房間繼續拼拼圖,薇奧拉也只好起身穿上外套,和澤法斯一起離開。
在離開前,澤法斯忽然回到書桌前,把裝著餅乾的袋子放到一個盒子裡,和筆記本一起放進空間袋裡。
盒子裡裝著的都是這幾天來嘉蜜格兒或是拉著她們一起製作,或是乾脆做好了再送給她們的零食,其中有些再不吃就要變壞了。
因為是接近睡覺的時間,當薇奧拉兩人來到地下的共用交誼廳時,那裡並沒有什麼人。唯一正在對話的人就是帕普吉大樓的宿舍長和監管導師。
「庫姆布老師,提亞格撒學長。」當薇奧拉還在猶豫該不該直接離開時,澤法斯已經快步走近兩人,大聲打招呼了。沒有選擇的薇奧拉只好跟在澤法斯身後,笑著行禮。
「莎希學妹來啦!布洛羅學妹也在呢。」威瑞什抬手回應,笑容和平常一樣開朗。不過薇奧拉聽出他在說到自己時,語氣隱約平淡了一點。
見到薇奧拉和澤法斯,剛才眉頭緊皺的庫姆布老師也露出笑容,向她們點頭問好。
庫姆布老師嘆了口氣,快速結束了她和威瑞什的對話︰「提亞格撒,記住你剛才說過的話。我不想讓警衛抓走我的學生。」
威瑞什笑容不變︰「我說了我有分寸的,您到底還在擔心什麼呢?」
「真的是這樣才好呢!算了算了,你們年輕人都不肯聽我這老太婆說話了!」
「怎麼會呢?只要我有時間,我很樂意和烏達茵老師您聊天的。」
「你沒有氣死我就算好事了!」庫姆布老師擺擺手,拄著拐杖回到自己的房間。威瑞什哈哈笑了幾聲,在站到他身旁的澤法斯頭上摸了摸,熟練得就像做了這個動作無數次。
威瑞什領著學妹們離開帕普吉大樓,向著學院長的辦公室前進。不過才邁出幾步,他就放慢了速度,和學妹們並行︰「莎希學妹手上的是什麼?」
「我不吃,給你的。」從空間袋裡拿出零食盒子的澤法斯把它遞給威瑞什。威瑞什接過盒子,凝視著其中的東西一會後,笑著向澤法斯道謝。
薇奧拉在旁邊看著兩人的互動,心裡那種奇怪的感覺揮之不去。
可要是讓她說有哪裡奇怪,她卻又說不出來。
……是他們之間的氛圍嗎?還是他們過於默契的相處方式呢?
苦惱著的薇奧拉抬起頭,看到了威瑞什看向澤法斯的眼神——像是學者看到了從未探究過的題目,那雙和陽光下的湖水一樣的眼睛中充滿了好奇和執著。
是因為這個吧?所以她才會覺得奇怪。
薇奧拉覺得自己已經找到了答案,也就不再在意兩人的互動,轉而思考她和澤法斯到交誼廳時,庫姆布老師和威瑞什的對話。
『我不想讓警衛抓走我的學生』?她可不記得威瑞什在未來會犯下什麼被學院警衛抓走的事呀?
……會是和他看向澤法斯的眼神有關嗎?
ns18.217.230.80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