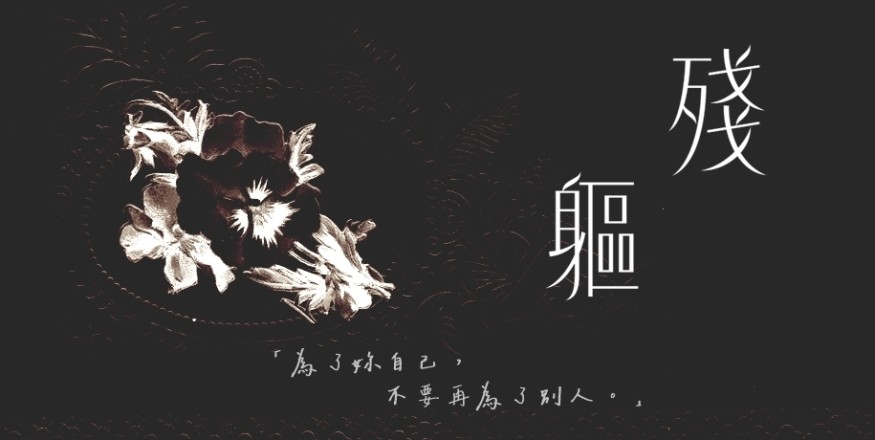羊\我說:
颯猊恩告知吃下魔法核心後會有什麼副作用,彌秧不得不懷疑,這世上什麼才沒有副作用?
體內猶如遭受龍捲風肆虐,像是一根高速旋轉的針在內臟上打轉。她抿緊嘴唇,這種疼痛還在能忍的範圍,可是當她終於將身體裡錯亂的魔力消化後,也已經快要下午。
彌秧不想浪費太多時間,在身體舒服後直接到院子,才解開「憤怒」的封印。
『有用。』它出來第一句就是大笑:『白婊子絕對有特別挑過!我感覺的出來,妳的魔力比之前多一點,如果妳再繼續吃……乾脆將所有人的魔法核心都吃掉!』
——你不是「貪婪」也不是「暴食」吧?我的身體會超過負荷炸開。
彌秧內心隱隱壓抑喜悅,體內的魔力的確有所提升,即使剛開始抗拒這種做法,此時卻像發現一條通往高山的捷徑,想起腳下走過的地方別人也走過,在差點受到「憤怒」影響時,彌秧迴避。
『妳身為我的僕人居然怕區區的小爆炸?只要妳的頭還在,我就有辦法讓妳起死復生!』「憤怒」吼著,彌秧的意識一陣動盪,對方對於力量的執著比自己還深,或許是因為著急?或者單純覺得該屬於自己?
——也得先讓身體習慣,吃太急只會噎死自己。
『膽小!』
彌秧不打算繼續跟「憤怒」打嘴砲,她開始鍛鍊身體,日落後颯猊恩準備好晚餐,她坐在餐桌前微笑三十分鐘都沒見到人,便到院子把彌秧扛進來,放在椅子上。
「妳用什麼咒語……」
彌秧悶悶不樂,她使用咒語提升肉體的效能,所以才在院子待很久,測試自己的極限提升多少。結果颯猊恩突然出現,她故意讓自己的身體變得沉重,對方卻輕而易舉的將她扛起來、帶回屋子裡。
「很簡單的小手法唷,我只是分解妳附在身上的輔助咒語,順便強化一下自己而已。」白袍露齒燦笑,推一盤菜到彌秧面前:「快吃吃看!這是釀了十年的酒醋,我剛剛才想起來自己有釀這個,味道嚐起來不錯唷!」
「酒醋?」
「嗯嗯,就像蘋果醋。」
「蘋果醋?水果可以釀成醋?」
「噗。」颯猊恩笑出來:「可以唷!不過我們常喝的酒都是用麥子釀成的,而用水果釀成的酒就比較貴,尤其是葡萄酒,越是高級的葡萄酒……」
彌秧無視颯猊恩的嘮叨,她叉一片葉子送入嘴裡。
『味道可以,妳會喜歡。』
——我看起來像是喜歡嗎?
雖然心裡這樣碎念著,她還是吃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全部進到白巫師的肚子裡,彌秧說不清自己喜不喜歡,酒醋會酸會甜,嚐起來有非常特別的滋味,但是酒氣刺鼻。
即使之後吞下其它食物,彌秧感覺口腔還藏留著酒味……想起那間整齊、擺滿價值不斐物器的辦公室,那時候的她很喜歡坐在靠牆的小桌子,吃著肉醬麵,偷瞄一眼坐在辦公桌前處理文件的白巫師。
想回到那時候,但是痛苦會重來。
這幾天很快過去,在第四天下午時,七個小蘿蔔沒有出現;彌秧被颯猊恩拖去洗澡,換上一套非常正式的白禮服……
她皺著眉頭,有點困難地開口:「我不能……穿黑色的嗎?」
「不行唷。」
颯猊恩走出來,她換上一套白絹長袍,上頭繡著細細的複雜銀線,隨著身體稍微動作,如似波浪般的光澤隨之閃爍,像是優柔的白光籠罩著聖女石像……那頭輕盈美麗的白髮、那抹淡然的微笑,那對清澈蔚藍的藍眼睛,彌秧盯著看許久,才發現自己呆住了。
「我喜歡妳看我的眼神。」颯猊恩露出愉快的笑容,用手指挑起彌秧的下巴;她說不出為何羞臊,被挑起後立刻甩頭,將視線對準白袍的身後問著:「為什麼不行?我穿白色看起來很奇怪。」
「因為在王族的宴會上,顏色是有意義的。」颯猊恩說著,替她拉好衣領:「白色搭配灰線條的襯衫是男服侍,灰裙綁有小頭巾是女服侍;貴族男士通常會穿黑禮服、女士搭配顏色較深沉的灰藍或是鮮豔紅與溫暖橙裙;戰士會穿著輕甲、腰間配劍;王族則是隨便穿,通常會穿得十分鮮豔,他們的服裝是最厚又最複雜的,身上一堆繡花繡紋,如果妳看見哪個人的裙裝特別花,對方十之八九是王族,不論男女都一樣,他們挺喜歡墊高身高,所以看見誰的鞋底增厚超過五公分,十之八九也是王族。」
「簡直就像標靶。」彌秧想像那畫面之後扯扯嘴角,腦中浮現五彩繽紛的火雞裙:「突顯自己的不同,炫耀自己的身分,對於刺客真是謝天謝地。」
「刺客倒是不用怕。」颯猊恩拍掉彌秧想鬆開領口的手:「忍耐點,脖子一定要遮住。總之,我們魔法師是穿袍子或是類似的白禮服,我知道妳不會想穿白袍,所以就挑禮服,至於為什麼不能用黑色——現在人對黑袍的印象已經是負面的,彌秧穿黑袍哪怕是我帶進去,也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而妳也沒辦法穿黑禮服,所以就稍微忍耐一下,好不好?」
「好……」彌秧咬牙切齒,如果她將世界毀了,就不用這麼麻煩。
當然,這只是隨便想想。
『嘖!想到就要做!』
「彌秧稍微後退一點,不要離我太近。」
彌秧挑眉,後退幾步。
颯猊恩從袖子裡拿出一條非常精緻的金飾項鍊戴在脖子上,彌秧感覺到強大濃郁的聖光,盯著那串有白巫師之首象徵的項鍊,項鍊一配上這袍子,從原本的聖女轉化成神聖威嚴的賢者之息。
「憤怒」磨著牙,彌秧猜它在評估颯猊恩隱藏多少實力。
怎麼忘了,這世界有許多能輔助魔法的飾品,那條項鍊還是其中之一的神器……戴上去之後,颯猊恩不知道提升多少力量,彌秧感覺到兩人之間的實力天差地遠。
如此強大的白巫師,說自己無法獨自一人阻止七宗罪。
彌秧渾身寒慄,當年的梅林又是多麼神?那年代可不像現在還有魔法輔助的各種東西……當她陷入苦思時,前方強大的聖光壓迫過來,她感覺到灼熱的痛楚,不過那雙手掌很溫暖,小心翼翼撫摸她的臉頰,兩人彼此相望,颯猊恩笑出來。
「妳這是什麼表情呀?」
「沒有……」
「嗯嗯,為了以防萬一,我現在封印它囉。」
『操!』
颯猊恩神速一拍,「憤怒」的抱怨只趕上一瞬間。
彌秧在心裡替它默哀一秒,這些日子為了順利運用自己的魔力,「憤怒」像是燭火一樣點燃後捻熄、點燃後再次捻熄,能出來的時間少之又少,現在又被啪搭一下關起來,全部宗罪裡就只有它每天要被白巫師封來封去,說出去絕對笑死其它六宗罪。
「嗯嗯,「憤怒」封印了,服裝也沒問題,臉看起來乾乾淨淨的……啊。」
「啊?」
「彌秧戴這個。」
颯猊恩又從袖子拿出一條金色的項鍊,但是花樣沒有她脖子上那條複雜,感覺低了一個層次像是附屬品,彌秧用手摸摸兩下,上頭殘留颯猊恩的魔力,這個戴上去就像被宣誓主權。
「我真要戴上?」
「嗯,以後他們就知道妳是我的人,彌秧就可以享有一些特權。例如優先借閱國家圖書館的魔法書,甚至不開放的禁書區妳也能進去,就像我一樣,有時候我需要查些古典,是能直接進去該國家的圖書館禁區借閱。」
「我這樣進去會被趕出來吧。」彌秧笑一笑:「全世界都知道大名鼎鼎的白巫師颯猊恩,誰會知道她身邊有個小跟班?」
「所以——他們現在不得不知道了。」颯猊恩甜甜一笑,在彌秧的嘴唇上一吻:「看妳要不要帶平常在院子練習的那把木劍,我知道妳房間那把比較有用,但是……」
「那種場合不適合。」彌秧翻白眼:「我知道,妳別把我當成那七個幼稚小鬼頭好嗎?我知道這條項鍊不止用來宣誓主權,也是用來壓制我身上的邪氣,想當然,用「憤怒」骨頭做成的黑劍帶過去是找死,我沒事找事做幹嘛?」
「唷,抱歉。」颯猊恩的笑意看不出任何一絲道歉,她伸出手捏彌秧的臉:「好啦,那妳快去拿劍吧。」
彌秧非常無奈嘆氣。
當她們走出房子第一步,彌秧隨手拉住颯猊恩,白袍非常順便勾住她的手臂,彌秧看著眼前闖進院子裡的惡魔,這時間點「憤怒」不在,它進來幹嘛?
『尊貴的大人。』惡魔對彌秧鞠躬:『王發現這附近潛伏一些敵人,派我在這看守。』
彌秧抽抽嘴角。
「那就麻煩你顧家囉!」颯猊恩完全不覺得讓惡魔顧屋子有什麼不對,彌秧滿臉懷疑看著對方,那副表情不像在開玩笑……她覺得自己如果知道白袍的腦袋是怎麼運轉,那世界的真理早有解答。
颯猊恩帶著彌秧大跳躍,彌秧感覺自己像是被吸入一個空間再被吐出來,睜開眼時,兩人站在一位馬伕前面,馬伕叼著菸斗、懶洋洋看過來。
「喔,白巫師跟另一位賓客。」
「這是邀請函。」
馬伕接過颯猊恩給的函件,用手抓抓頭,將嘴上的菸斗拿下往邀請函上面敲兩下,一道紫色亂中有序的魔法陣浮出,馬伕朝魔法陣吐煙,化成四匹粉紫螢光的幽靈駿馬、拖著一輛簡樸的白車廂。
「謝謝您。」颯猊恩笑著付十枚金幣,跟彌秧一起上車。
彌秧關上馬車門的瞬間,外頭立刻升起一大片白霧。
她警覺瞪過去,被颯猊恩拉住。
「別緊張,這是正常現象,我慢慢跟妳解釋。」
白袍用手指敲敲車頂,馬車慢慢行走了;彌秧看窗外是濃濃的白霧,整個人精神緊繃四處張望,不論左邊還是右邊,窗外都是同樣的風景。
「這是防護措施之一。」颯猊恩輕鬆自在說著:「國家重大宴會總是這樣,因為邀請的多半是身分地位崇高之者,所以防護上非常嚴謹。只能在規定的時間內傳送到指定的馬夫位置,將邀請函交給對方,對方會幫妳幻化出只有幽靈馬能行走的道路,那條道路正是我們此時走的這條,因此到達目的地之前,門不可以打開,幽靈馬在到達目的地時才會停下。」
「幽靈馬不會被攻擊?」
「不會,幽靈馬跟羌仔一樣,是特定區域的生物,牠們走的地方,只有牠們能夠生存,提到這個不得不讚嘆先人們。先人花了數十年的時間才找到召喚幽靈馬的方式,甚至與之維持良好的互助關係,打造出不會被白霧腐蝕的車廂,得以通過牠們的空間到達目的地,這需要花多久的時間才能辦到呢?」
「在幾百年前。」彌秧先是停頓,才繼續:「吠犬病也被認為是種絕症,它的傳染性高、發作起來會像狗一樣喘氣、嚎叫,最後會全身潰爛而死,所以只要有人染病就會被丟到荒郊野外自生自滅……直到某一位白巫師發現了解藥,在那年代,誰會相信奪走萬條人命的絕症居然是吃藥就可以治好的小病?甚至到了現在,吠犬病也幾乎滅亡了。」
「畢竟是我的領域嘛。」白袍笑一笑:「啊……當時真的好多人死了。」
「所以發現幽靈馬甚至能馴服的人,大概跟妳一樣,剛好是擅長這領域的吧。」
颯猊恩聽了嘴角上揚、眼裡滿是笑意,她勾住彌秧的手指、十指交錯,頭輕輕靠著對方肩膀。
「妳是在拐彎抹角的稱讚我對不對?」
「沒有。」
「明明就有。」
其實颯猊恩真的很訝異,彌秧知道當時發現解藥的是她。
雖然很多資料記載是白巫師發現解藥,但是是哪個白巫師卻沒有寫出來,那時候的情況太危及了。颯猊恩知道怎麼配之後,立刻將配方擴散給全國的藥師去發藥,由於當時她沒有特意說是自己配的,有不少人趁機佔功勞,傳言的藥師名稱變來變去,颯猊恩唯一慶幸的,是傳到最後沒有冠上任何人的名字,只留下白巫師這個詞。
「諾亞怎麼樣?」
「誰?」彌秧回神同時,颯猊恩一臉認真說著:「彌秧的中間名?畢竟這種場合除了我因為身分關係,其他人想稱呼妳,要是直接喊『彌秧』會有點過於親密,喊家族名字……我不曉得妳願不願意讓他們知道?」
彌秧想像一下畫面,不認識的貴族喊自己彌秧,怎麼想都有詭異的疙瘩;改喊家族名,搞不好會問是什麼家族,牽扯到上一代……彌秧越想眉頭越是皺起,颯猊恩悠哉看著對方,知道這人又開始鑽牛角尖。
「就說妳是諾亞吧!因為原則關係,所以本名、姓氏不方便透露。」
「還可以這樣打馬虎眼?」
「可以呀,因為我會先介紹妳是我唯一的助手,他們就不敢多問囉。」
偉大白巫師的助手,怎麼聽都很厲害的樣子。
「說的我像是全天侍候妳生活起居的小僕人一樣。」
「唉,可是家裡都是我在打掃,我在準備早午晚餐,我洗衣服、晾衣服又收衣服、摺衣服還要幫小孩上課,也是我出去買菜、買肉、整理菜園、播種、維持菜園溫度、除蟲、施肥,擦桌子、洗鍋子、回信、保養妳的劍,整理妳每天都弄亂的房間,還要幫妳順魔、補魔,順便一提之前還有幫妳修頭髮,彌秧就只有偶爾會幫忙洗碗!」
「保養我的劍?」整串下來彌秧只聽見這個重點:「妳保養我的劍?」
敢問白巫師怎麼保養那把邪劍?是把它擦乾淨還是把上面的邪氣磨掉?
「就算是用它做成的,武器還是武器,需要時常保養。」颯猊恩一臉認真、低聲咕噥:「怎麼說這麼多,妳只聽到那點?」
「因為那些聽來,就算我沒有跟妳同居,也是妳平常會做的事情。」彌秧冷冷說著,推測白袍應該只是單純保養,不是將上頭的邪氣剔除。
一把邪劍沒了邪氣還有用嗎?
「是這樣沒錯。」颯猊恩不打算繼續糾纏在這話題,因為馬車的速度放慢了,當車子停下來時,她看向窗外:「還不能出去唷,等外頭的白霧全散了。」
「嗯。」
白霧散去後,是一片決然不同的風景。
高高的城堡與乾淨整齊的建築,很熱鬧看似溫情,彌秧卻嘗到各種惡意,她扯扯嘴角一笑,看似華麗的外皮下皆是腐爛的心靈——馬車車門自動打開,一名接侍面帶微笑鞠躬歡迎,彌秧看對方的服裝一眼,自己先下車後回頭伸手,颯猊恩優雅地搭上她的手步下馬車。
白巫師的出現無疑帶來非常大的轟動。
颯猊恩優雅地行走,彌秧頓時覺得旁邊這個非常會裝,平常走路快的像是一陣風,現在卻保持普通的步調,還勾著她的手肘一臉很親密的樣子……彌秧非常不習慣成為焦點,尤其這焦點是旁邊那位帶來的,感覺隨時都會被坑死。
不,應該已經坑死了。
不曾與他人過於親密的白巫師居然搭人手肘?
不曾與他人共乘馬車的白巫師居然跟人一起下車?
彌秧聽見颯猊恩發出非常細微的噗哧聲,就能確定是她故意的。
回頭絕對操爆妳——彌秧整個臉黑。
ns 18.68.41.175da2












 will be deducted
will be dedu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