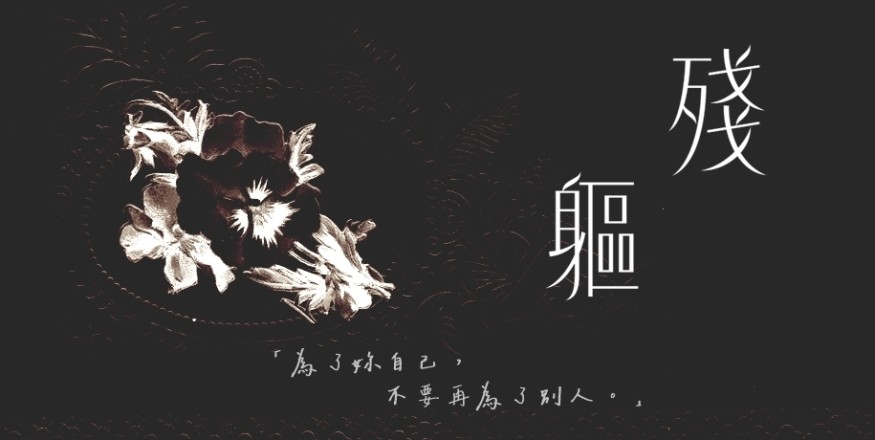羊\我說:
彌秧的眼神黯然,凝視泉水上的白袍倒影。
依靠——多不可思議的詞,從偉大的白巫師口中出現。
她正想笑自己多無能時忽然想到——白袍,其實也不算孤單吧?至少用她的年紀去算,布登崁丁爾掛掉的時間絕對不超過四十年,她想開口問,最後將問題憋回心裡。
「是唷。」
然後彌秧忘記颯兒朵能聽見她心裡的話,在一愣同時,白袍笑笑地看來。
「彌秧很好奇對吧?為什麼布登崁丁爾很知名卻又鮮為人知,這衝突讓妳覺得怪很正常,理由也很單純,他對自己的名字施法。」
「啊?」彌秧不敢肯定自己剛才有無聽錯:「施法?」
「嗯嗯,畢竟越知名帶來的麻煩越多,後半輩子他想有些私人空間,就對自己的名字下了『所有知曉此名者,皆在日落後遺忘該事物』的咒語,然後將自己關在城堡裡,只有必要時才偽裝外出。」
「這樣有用?他對自己的名字下咒不會有什麼誤差嗎?例如親朋好友也忘了自己?」
「誤差倒是沒有,老師花了整整一百年反覆修改這串咒語的完整性,複雜度高到我寧願拿去研究其它事項。總之,因為咒語生效的關係,現在人們提起他的名字時,才會想起我曾經有一位白巫師導師以及他過往的事蹟,然後又很快忘記,可是這咒語在跟他關係密切者身上倒是弱化不少。」
「可是說到他的事蹟……我隱約覺得很多,卻又說不出三個,這很詭異吧?」彌秧怎麼想就是覺得怪,認知與記憶有出入。
「因為他把我推出去擋了。」颯兒朵皮笑肉不笑,看起來挺無奈:「那時的我已經學成已久,在外遊歷了很長一段時間,所以我們的聲譽鼓旗相當,類似這樣。」白袍靠在泉邊一個彈指,四周傳來草叢搖晃的唰唰聲響,許多小石頭飛來在她前方疊起兩座高塔,一邊十顆、一邊八顆。
「十顆這個是老師,八顆是我的,彌秧我問妳一個問題。」
「嗯?」
「為什麼我的傳說這麼多呢?」
彌秧看著颯兒朵的眼睛,她笑起來的樣子很調皮,就像在炫耀自己多有成就的孩子。
彌秧沉默半晌,她不會突然問這麼沒意義的問題,想好後開口回答:「其實跟布登崁丁爾的混在一起了?」
「是的,彌秧很聰明。」白袍點點頭,用魔法開始移動十顆小石頭,慢慢往八顆的疊上去:「老師的咒語施下去,前四年沒什麼太大變化,可是隨著他隱退,人們開始遺忘布登崁丁爾這名字,而我持續活躍在大陸上,老師過往的事蹟就慢慢加附在我身上,他是故意的,再加上倫斯克拉家族的人也在幫忙他將過往的一切隱藏住……就變成現在這樣了。」
十八顆石頭疊著。
「只有我記得他真正的事蹟,其他的傳說已經被竄改成我或者抹去,只留下少少幾個……『布登崁丁爾造就了颯猊恩』、『上任偉大的白巫師之首』,每個人想起來後會這樣說,被問起布登崁丁爾做過什麼偉大事蹟卻給不出答案。」
颯兒朵輕輕一推小石頭塔,垮的一乾二淨,只留下當地基的那顆。
「為什麼他要抹消自己?」
彌秧看著颯兒朵起身,嘩啦的帶起一波水,她濕淋淋的長髮貼著皮膚,身體上不再有任何一絲傷口,隨著手指一彈全身上下立刻全乾,彌秧拿起乾淨的白袍替她穿衣。
「我想是羞恥的關係吧。」
「羞恥?」
「老師的個性跟凱特相似但是又不相同。」颯兒朵這句,只讓彌秧想到一黑一白的凱特,突然有種莫名其妙的喜感,而她繼續說著:「老師身為兄長就下意識對自己比較拘束,長久以來壓抑內在真正的性格。現在刻板要求白巫師要溫柔體貼、善解人意,時常微笑、樂於助人的形象,其實就是老師的影響,他就是這樣的人,他是好人、在妳之前的大好人,但是我知道老師內心其實一直嚮往跟凱特一樣隨心所欲,可是他放不開自己。」
「所以就發生不好的事情了?」彌秧蹙眉:「還是我爸爸殺死他……所以布登崁丁爾不介意被殺,就是因為他覺得自己有錯,罪有應得?他做了什麼?」
「關於這點。」颯兒朵語氣一停,突然轉過身來。
她們對上視線,彌秧有不祥預感。
「跟我有關?」
「不。」白袍收回視線、看向遠方:「跟妳無關,但是跟妳……可能,或許、也許……牽扯到妳母親。那段日子我已經在外遊歷,布登崁丁爾也有持續招收學生,至少在我觀察中發現,秋娜禾的溫柔吸引老師的注意,而老師過去可能曾經愛過人,又可能不明白什麼是愛,他發現自己再也壓抑不住失控的情感,尤其在得知她願意為了艾洛帝亞放棄進入倫斯克拉的機會,就更崩潰了。」
「啊……啊?」彌秧慢半拍:「放棄?為什麼?」
「當年倫斯克拉家族有缺魔法師,所以開放徵招,老師的關係跟倫斯克拉家族很親密,所以老師希望她能與知有更深的牽絆,誰知艾洛帝亞想進騎士團沒中的事情令秋娜禾也跟著放棄。所以就,嗯……發生不愉快的事情,那天以後,老師羞愧的選擇封閉自己,也沒臉再見我。」
「什麼意思!」彌秧整張臉刷白了:「他沾汙我媽?」
「是的。」
颯兒朵那句是的,彌秧整個心猛然抽痛,頓時結巴:「等、等等,有可能嗎?還是什麼——我是說,會不會是誤會?有時——媽媽肯定只愛爸爸,搞不好妳老師也沒有,只是什麼剛好形成誤會?」
「不是誤會,是確實發生。」白袍伸手捏彌秧的臉:「是妳父親,艾洛帝亞拜託我將秋娜禾救出來的,他說『秋娜禾被帶走了,布登崁丁爾不願放人出來。』所以我回去看看發生什麼回事,破除屋內層層結界,那些結界不像他已往下的謹慎、結實,而我撞見後直接攻擊老師、將妳母親帶走。之後他沒臉再見我、也愧對妳母親,活在自責裡。」
彌秧傻了。
徹底傻了。
「當時老師跟我說,如果妳父母想來算帳,哪怕要他那條命都可以。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沒有追究艾洛帝亞殺死布登崁丁爾的事情,這是他選擇的,我說了。」
「所以他下咒就是為了……」
「不是,只是剛好、恰好,在那之前咒語已經實施許久。」颯兒朵輕輕搖頭,最後忍不住嘆氣。
「爬越高、跌越深。老師一直用『幸好我已經有先下咒』來安慰自己,卻一直走不出心魔,到死為止仍在自責,卻萬萬沒想到妳父母並沒有將他犯下的錯告知天下,畢竟這種事情傳出去,哪怕咒語再有用,只要人的意識堅定清醒沒有可以作為移型的存在,那傳出來基本上就毀了,可是沒有,非常意外的沒有。」
颯兒朵眼神曖昧看著彌秧:「妳父母寧可被追殺也不說真相。我想有大半的原因是妳父母其實沒有真的想殺他,所以也陷入自責選擇自我流放……這世界挺諷刺的,好人只要犯過一次錯,就會發瘋逼死另個好人,而壞人活好好的,甚至自認問心無愧。」
她笑一笑,持續盯著彌秧:「而且還有了孩子。」
「妳是什麼意思?」
「生命的偉大,不是嗎?」颯兒朵低語:「正常來說該痛苦的存在,卻是用愛填補,艾洛帝亞與秋娜禾的愛不只對彼此,也對他人博愛。」
「我是艾洛帝亞的孩子吧?」彌秧的腦袋像是被雷劈般空白:「我是吧?非凡說我的眼神像爸爸……」
可是這樣越想越不對。
雖然布登崁丁爾的姓氏與恩瑞迪姆耶扯下不關係,但是有可能,非常有可能——是血緣稀薄的遠親。
不然,為什麼布登崁丁爾知道颯兒朵她家的暗門在哪?
然後更重要的——魔法核心同源,凱特是怎麼感應出來的?
彌秧的情緒瞬間面臨崩潰,她好不容易知道父母之名,結果現在——現在——她硬是憋住情緒,搖搖晃晃走回帳篷中,在記憶裡的父者,永遠都是堅定又溫柔的他,而不是教科書上那張肖像。
「彌秧。」颯兒朵輕靠在她身旁。
「妳從什麼時候知道的?」她顫抖聲音問著。
「有陣子了,我一直猶豫該不該說,覺得再不說會是種欺瞞才開口。」她說完後嘆口氣:「如果痛苦的話,我幫妳把記憶刪除,好嗎?把我剛剛說的話刪掉,妳能減輕負擔。」
「凱特知道嗎?」她搖頭,十指扣住白袍的手。
「知道的。」
彌秧又再次倒抽口氣。
「我告訴他說之後,凱特跑去老師的墳前大笑很久、最後朝墓碑吐口水。所以我想他願意幫忙看守城鎮,有一半的原因是妳,不然依照他的個性,不弄死人很難。」
「甚至還幫我幹掉一個代言人。」
颯兒朵點頭:「不過妳可以無視血緣沒關係,畢竟對妳有養育之恩的是艾洛帝亞與秋娜禾,而布登崁丁爾不過是賜與妳良好魔法核心者。就算那場過錯沒有誕生妳,艾洛帝亞與秋娜禾的結合依舊會生下妳,妳依舊是彌秧,妳就是妳。」
她伸出拇指,輕輕往彌秧胸口按過去;彌秧感覺到一股溫暖,原本壓抑的情緒鬆解不少。
「好好活著。」颯兒朵溫柔笑著:「這樣就好了,不是嗎?」
「嗯……」她眨眨眼:「那妳也要好好活著。」
「我會的。」颯兒朵笑完靠過去,彌秧用手指抵擋她的嘴唇:「不要親,每次親都快失控了。」
「唷?那彌秧要不要跟我一起泡冷泉,有靜心的作用喔!」
「我想一起泡就永遠沒作用了……颯兒朵。」
「嗯?」
「知道這件事情後,妳怎麼看待他的?」彌秧問著:「從妳的敘述跟凱特的反應來看,布登崁丁爾絕對跟你們不同掛,妳訝異自己老師做出這種無恥之事嗎?」
「不訝異。」颯兒朵的答案讓彌秧意外,當她想問下去時,颯兒朵舉起一根手指,彌秧乖乖閉上嘴巴聽她繼續說:「我活很久了,對於人的東西都不會太意外。怎麼說呢?當時的我已經站在他的位置,自然知道這種高壓下會有怎樣的偽裝,各種反應都只是生物的正常情緒,皆有可能發生,不會因為他是好人就絕對好;不會因為他是壞人就絕對壞,只是世間對於壞人比較好,做過一件善事永流傳,而好人犯過一次錯就再無翻身之地。」
「簡化點。」彌秧捏捏鼻梁,迅速消化白袍剛剛的長篇大論:「妳的意思是,不會因為他對我媽做過那種事情,就醜化他在妳心中的輕重?」說到這個她心底隱約有煩躁,有對自己,也有對颯兒朵。
「是的,而且硬要說,這不算什麼。」
不算什麼。彌秧咬牙切齒,深呼吸好幾口氣,想起曾經一名七聖子跟自己說的事情後開口:「因為某些王公貴族的情史更亂?」
「是的,每次我都很感嘆,他們怎麼有時間搞這些。」颯兒朵明顯對這話題已經沒興趣,有些心不在焉的一心二用,彌秧看見她這種態度內心放鬆不少。
是啊,只是這樣而已。
她有對好父母,已經親自報仇不拖累孩子,而且艾洛帝亞多半知道的,卻還是把她當成自己的親生女兒來疼愛,那她也把他當成自己唯一的爸爸不就好了?布登崁丁爾只是路人,颯兒朵告知她這些事情只是時間早晚。
雖然還是有些難受。
「彌秧——」
「嗯?」她看著又開始不安分的白袍:「颯兒朵,妳動不動發情可以嗎?」
「趁還可以的時候多多做幾次。」她舔舔嘴唇,露出壞笑:「我們暫時出去玩要不要?精靈的嗅覺太敏銳了……」
彌秧挑眉,用手彈颯兒朵的額頭。
「看來我以前說妳色是正確的。」
「就說是正常舒壓了。」颯兒朵笑著拉起彌秧,她領著她離開帳篷、優雅地告知精靈要暫時離開一會,就走往領地邊界,回頭贈與笑容。
「走囉!」
「嗯。」
兩人勾起手肘,一陣天旋地轉之後彌秧還來不及看清楚這是什麼地方,感覺到颯兒朵在周圍佈下層層結界,就將自己一把推倒,彌秧扶著石牆、抽抽嘴角使出照光咒。
「妳想打野戰?」
「這裡夠隱密嘛,氣味不會太明顯。」
她可不覺得山洞算什麼隱密的地方,頓時無言數秒才說話:「這山洞的回音不大,是妳消音了還是裡頭有通向別地方的路?」
「消音了!」
「嗯。」彌秧看著比自己還期待的白袍已經在解開腰帶,想了想感到無言,根本不是舒壓而是「色慾」的關係吧,看來泡冷泉也無法讓受到「色慾」影響的白袍清醒。
等她自己脫光跨坐在大腿上後,彌秧輕撫眼前人的髮尾,在嘴唇上輕輕一吻。
「妳想做,但是沒有完全脫下來。」
「嗯?」颯兒朵一頓:「不是都脫了嗎?」
彌秧的手指在她的手臂上遊走,颯兒朵頓時明白意思,表情複雜萬分:「不,這樣會害妳沒有性慾,我是認真的。」
「坦誠相對。」彌秧捏捏她的手臂:「要是真的做不下去,妳可以大罵我是只看外表的負心漢,這樣以後吵架多一條妳能罵我的藉口。」
「噗。」颯兒朵笑出來了:「好啊,那妳可不要後悔。」
「後悔什麼……」彌秧接受颯兒朵的吻,感覺到懷裡的女人開始有了變化——她對上那雙清澈的藍眼睛,眼睛的主人總是散發的自信消退,雖然笑著說不後悔,卻略為膽怯地縮著身體,眼神透露著害怕。
颯兒朵是醜陋的怪物,或許布登崁丁爾正是知曉她的真面目,在過去那段日子裡,兩人即使有過誹聞也不曾弄假成真。彌秧再次親吻她的嘴唇,主動將白袍拉入懷裡。
「妳是我最美麗的怪物。」
「噗,哪有人說這種情話啦?」
「我啊。」彌秧笑著:「這樣以後有人偽裝成我的樣子說『妳是我的女神』什麼,就會知道是假的了,因為我只會說妳是我的女神經病。」
「妳齁……」颯兒朵撒嬌般推拒她的胸口、終於鼓起勇氣勾住彌秧的脖子,任由她一路吻下、手指淡化過往的傷疤……
做愛只是其次,當夜色升起時,兩人已經穿回衣物靠在一起看望星空。
颯兒朵嘴裡哼著曲調,像是突然想起什麼,眼裡閃過一絲愉快的星星,閃爍中照耀著玩心,她拉拉彌秧的手,彌秧隨著白袍的魔力牽引站起,在月光下的颯兒朵隱隱發光,然後她踏出第一步,就像輕盈的天使。
彌秧瞪大眼,颯兒朵居然可以靠自己的魔力飄浮在空中。
她就像即將要離開這該死的罪惡世界,颯兒朵不停往上走,彌秧內心一片慌張、她跳起來伸出手想拉住她,颯兒朵笑吟吟地牽住,一股涼風順著她們往上捲起。
天與地、光與影,在星星之下她們是迷途旅行者,星星照映著上千條道路,她們仍選擇最艱困的苦行。
踏著風、踩著無形之體,颯兒朵牽著彌秧行走在夜空中,她們腳下是燈火稀少的城鎮夜景,一閃一閃猶如地上星星;抬頭所見的夜空又是另一座城鎮,卻是燈火通明照亮整片黑暗。
她們行走在成千上萬星群的夜晚裡,在彌秧的眼中,颯兒朵依舊是最耀眼的那顆星。
她是如此閃爍,遠比任何希望還耀眼。
「活著。」彌秧說著:「永遠陪在我身邊好不好?」
颯兒朵只笑一笑,牽著她在星星裡行走。
ns 15.158.61.8da2












 will be deducted
will be dedu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