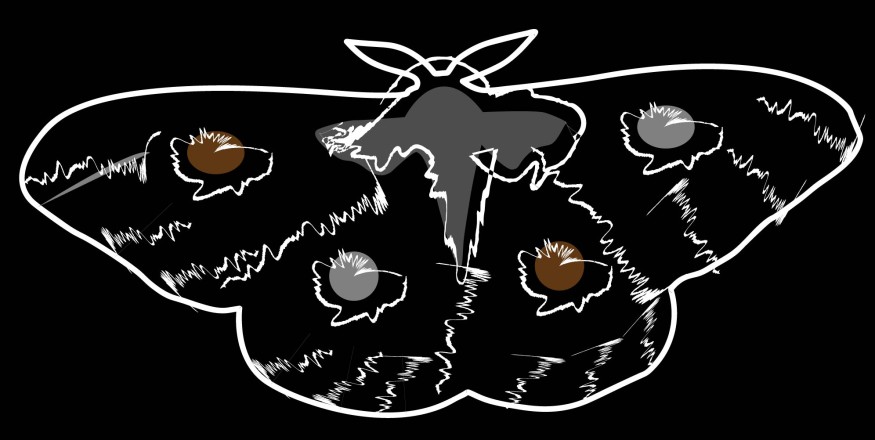那天,是解一樹第一次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走出戰場。
無法同時抱起盈盈和率優的他,不得不讓同樣虛弱不堪的傅承沐和雷鈞霆接手扛起林率優。他不能讓她們倆像是廢棄的布娃娃一樣拖著腳被拉走。
走出鬼蝴蝶形成的通道,他頹然倒地,和其他人被傷亡更加慘重的林朝日等人的部隊帶走。異生物並不放過他們,鍥而不捨地追在車後好一段路。幸好跨界師南陵友與靈貓乘著黑龍及時趕到,否則異生物會將他們全部踏平。原本南陵友和伙伴靈貓正遠在北部,鎮壓被從召喚出來後順著臺北捷運軌道四處殺戮的十來隻異生物,出征的醫藥世家與夜暝底下的維安警察、跨界師人力有過半傷亡,重傷者更是不勝其數,幸虧浴血奮戰後,異空間裂縫被關上,透過疏散捷運站內人流以及封閉站口,來不及殺掉的異生物也被困在捷運通道裡力衰死去,沒有對整座城市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只是有不少相關的影片、照片流出,恐怕動用所有媒體力量也壓不下所有消息,社會大眾很快就會知道危機已經蔓延,並且勢不可擋。醫藥世家元氣大傷,家主的妹妹、跨界師傳人更是消耗力量過度,整整昏迷了好幾天。
解一樹聽著夜暝高中北部分校的生教組長許正群和他陳述這些事,最後,他冷冷問,「及時趕到?」在人們眼中,南部的騷亂只是小事?盈盈和率優的死不算什麼嗎?退一萬步來說,南部分校附近犧牲的成人們,也就是跨界師與維安警察的同僚,那些人戰死,在師長們眼中也不算什麼嗎?
解一樹覺得以他的個性會冷笑著回嗆老師,但實際上,他應該是大吼大叫、亂砸東西,又或者出口成髒吧。總之他不記得了,只知道最後許正群摔破茶杯,指著他的鼻子要他滾出學務處。
這一切都是顏咨嬿害的,要不是她貪生怕死,寧可墮成魔也不願接受自己的命運,盈盈和率優不會死。她的魔化,就像一劑禁藥,讓本來即將力衰而亡的異生物重新充飽電……不,一切不能都歸咎於顏咨嬿。影響的因素還包括北部、中部同時發生的事,恨一個人,並不是解決之道。要是他沒有埋頭準備大考,以及在考完後和盈盈專注在放鬆與相處,他就會透過自媒體管道看見現在的世界有多混亂。盡一個學生的本分好好讀書是他的錯嗎?聽從盈盈的想法,在畢業前製造珍貴回憶,也是一種疏失?
不要再找肇因了,要是有百分之百正確的解答,南棠珍早就會告訴他了。正是因為大家都不明白該怎麼選,不到結局不知道犧牲與獲得,預見未來才不會是最強的異能。
顏咨嬿確實不是什麼大人物。她只是一個小小的既得利益者,真正掌權的人,甚至不在意放棄她。費盡千辛萬苦,解一樹一行人卻連最終大魔王的影子都見不著,多麼可悲。
終於,傅承沐前來帶走了漫無目的在校園內亂晃、嚇著許多人的解一樹。他們去了紗英在北部第三研究院所的實驗室。
躺在解剖臺上的,赫然是顏咨嬿的屍體,還是維持著身首分離的狀態。
「班長記錄,一樹幫我。」紗英老師下令,他們兩人戴上防護裝備。
進入工作模式後,解一樹暫時忘卻痛苦。直到紗英讓他們兩個去旁邊休息,他才醒來。
一切太不真實了。
站在熟悉的實驗室,看著熟悉的朋友與老師,彷彿所有事都和兩年前一樣,沒有絲毫變化。
以前的他是個獨來獨往的人,偶爾會和阿沐等人出去玩,在學校也會聊上個幾句。但他全神貫注於學業,下課時間或是用餐時間抓著書不放,失去很多和人相處的機會。他享受一個人的時光,可以更有效率地完成自己想做的事,獨自旅遊還能體會到一群人出遊時無法感知的感受。大概是從高一、高二開始,他重新認識了這群從國中時就開始處在一起的人們。改變的契機正是有點煩人、硬是把大家黏在一起的安邑潼。
過去他記得最清楚的學校天空,是黃昏時分,也就是他讀了一天書,終於離開座位去學生餐廳,可以稍微放鬆一下的時間點。通常他會從天色中得到的唯有時刻相關的資訊,偶爾他也會看著斑斕的火燒雲,但佇足的時間不過幾秒。
現在,他的腦海中有晴空、有多雲的陰天、有整個季節的陰雨綿綿,偶爾也有戲劇性的打雷,時時刻刻,天空的顏色都在變化著,在同樣的校園觀察三年,理應看見各種面貌的世界。學校裡的顏色本來就很豐富,是他選擇不去看才會錯失那麼多。把他關進牢籠的,正是自己。
他的回憶當中,有越來越多人參與。就好像那些身影本來是模糊的,在他敞開心扉後,才發現原來身邊一直有這些人在。
他並不孤獨,卻主動去擁抱寂寞。
現在回想起國中時期,已經無法理解當初的自己為什麼會喜歡那種狀態了。
那時的他,是多麼孤單啊。
4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VUXBgeL4hd
畢業典禮圓滿結束了。
為了讓同學們可以好好過,班上同學逝去的消息暫時未對所有人公布,因此,畢業那種既快樂又依依不捨的氛圍仍然在。
為了避免被班上同學看見自己的狀態,解一樹沒有再回去班上,也盡可能對同學們避而不見。唯一有在接觸的傅承沐和他一樣情感內斂,都不可能在彼此面前落淚。
之後對班上其他同學的說法,會是盈盈和率優遭遇車禍,其他人的傷也都算在那場假車禍上,雷鈞霆則不公開受傷的事,免得被發現他們同時受傷太過巧合。不過,真相終究會被大家知道的吧,或許會是幾個月後,或是幾年後。屆時,小花蕾一定會很氣他們不找她幫忙;姑姑儘管膽小,也會不甘心地說「還是有我可以做的事啊」。
到時候,要怎麼面對她們呢?
他不知道。
李夕暘老師把盈盈之前寫過的作文悉數交給解一樹。他攥著那些紙張,在校園的角落讀了起來。
在一篇作文裡,她把自己比做紙飛機。
期待的眼光像是絕望的暴雨打溼機翼,我奮力越過海洋,卻感覺自己的身體越來越沉,像是羽翼融化的伊卡洛斯,絕望地看著海面與我的距離急遽縮短。塗上蠟的機身掉到海面,還不至於馬上沉沒,在最後的時間,我首次悠閒地漂浮著,不再為任何人而前進,只作為自己,享受垂死掙扎的時光。
仰望著天空的我忽然被陰影覆蓋,在頭頂的是遠在高空的另一架飛機,設計精良,不像我是廢紙隨手摺出的。他飛得比我高更穩,對我而言的沉重壓力完全壓迫不了他。我懷疑他是否真正看見我,即便沒有,他的影子也籠罩著我,為我擋去毒辣的日光。誰都有目標,若早點感受到這份不吝嗇的溫柔,也許我就能追逐著他飛越廣闊的汪洋。
老師給的評語是:偏題,結構詭異,以考試作文來說不能給高分,但是老師又補充,可以試著改寫去投稿。
23分是盈盈拿過最高分的作文分數,李夕暘老師在唸優秀文章時有特別提出,說那篇文章打動了他。題目關於「印象深刻的旅程」,她寫了一個關於兩人在街道中迷失的故事。那天,盈盈提出不搭公眾運輸、試著用走的到目的地的遊樂園,結果不熟路線的他們迷路了好幾個小時,翻過堤防、走上大橋,最後到遊樂園時,樂園營業時間只剩最後十分鐘。
我怕他會不高興,沿途抱怨著我當初荒唐的提議;但他對我說,他覺得這樣更有趣。他和我一樣,喜歡親自探索城市中的街道。比起直接造訪既定目標,漫無目的走著更能認識陌生的城市。
和那個同樣喜歡漫步的朋友第一次見面,像是命運的巧合。為制服繡學號時,我看見前面放著的袋子有個學號是未來和我同班的學生,我暗暗記下那個號碼,想著也許會和他成為好朋友。在諸多安排好的事中,有這麼一項有趣的意外,這讓我不禁想,或許過去不好的事都會有轉機吧。
她細膩的文字中透露著多愁善感,就是她那過人的感受力讓她比別人更容易受傷、容易陷在無力的小事中無法自拔。她許多高分的故事中所寫的主角都是他。她不常寫虛構的故事,這疊作文中敘述的故事他不是親身經歷,就是聽她說過。太熱愛分享經歷的她論說文寫得則較不出色,「我記不起來那些名人的名字,誰說過哪些話根本不重要。古人寫文章又不是為了讓我們一個字一個字記起來。」
解一樹用指節輕敲她的頭:「多花時間讀。」
「我就是討厭背誦嘛。」她抱怨。看到有其他人進來,她便收起任性的姿態,重新變為文靜少女。其實大家早就都看過她耍賴撒嬌的一面,也覺得那樣更可愛。
去大阪的時候,我們在銀杏樹街道漫步,走了好久才走回破舊的旅店。不合腳的鞋子磨破我的腳跟,腿更是痠痛不已,但是只要回想起那時聖誕夜的燈飾,所有我腦海能浮現的詞語,都無法描述當時有多幸福。擠在情侶群之中,小心不和彼此分散,分食聖誕市集買來的沾著糖粉的炸麵包,如果時間可以停在那刻就好。對大人來說,或者對於多年後成人的我們來說,這是天真得可笑的幻想。希望以後我不會忘記當時的心情,因為那時的我認真無比。年輕的我們會苦惱、會遲疑,卻總是全力以赴,也許純粹的幸福只能停留在當時的年紀。
二年級的聖誕夜,那次的旅行很窮酸,他們居然在機場過夜。凌晨時機場的店家幾乎都關閉,供人小憩的休息區充斥著體臭和打鼾聲,最後他們找到一處有桌椅的少人樓層,他趴下去補眠,盈盈則拿出她的小本子寫東西。當他醒來後,換她休息,她放鬆的睡顏宛如卸下重擔的天使。
曾喜歡獨旅、覺得和再好的朋友出國旅行都很礙事的他,現在卻暫時無法踏上一個人的旅行。他知道,看到新奇的風景,「如果她看到這個的話……」的想法始終會困擾著他。
人的心實在很奇妙。李夕暘老師講解夏目漱石的《心》時談到人心的脆弱和複雜。對解一樹而言,那是個淡而無味的故事,主角們心裡一堆小劇場,極其普通的事都能想成世界末日。現在他終於感受到心理是多麼容易被攻破。人、心靈、生命,實在是太脆弱了。
「嗨。」
解一樹冷然抬頭,瞪著俯視他的蘇炯均。雖然那張臉上掛著的笑容不是真的感到愉悅,而是蘇炯均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解一樹看了還是非常火大。
蘇炯均繼續皮笑肉不笑地說:「阿沐有來問我,但是我拒絕了。」
「你還敢說?」
「經過計算,我們去了就回不來,所以我不去。」
「率優呢?」
「我們都知道這點,畢竟我們是不善長近身戰鬥的狙擊手,正面交鋒一定最先死。她的選擇是去,我的選擇是不去,我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你想把我當人渣,我接受,因為我就是人渣,但我不會道歉。」
「我沒立場怪你。」
「那你為什麼咬牙切齒地說?」
「……我可能會忍不住揍你。」
「揍啊,只會讓我的罪惡感減輕唷。」
就是因為這樣,解一樹才要忍住使用暴力的衝動。不能讓這傢伙的心裡好過。
蘇炯均忽然把話題扯遠,「你記得我們私下去花蓮那次嗎?那間爛得要死的溫泉旅館,連提供的腳踏車都很破,有人的煞車還壞掉,在那邊烤肉還一堆蚊子。阿沐說十年後再約在那裡時,你不是說不要嗎?害負責訂住宿的斑比生氣。」
「不准叫她的名字。」煞車壞掉的人是運氣總是很差的常嘉矩,解一樹恍惚地想起。
「我叫的是綽號啊。不過去花蓮前兩天訂的包棟民宿就很好,我們每天都玩到半夜,有人直接睡在客廳。太魯閣風景是不錯啦,但是不知道是誰下載錯公車時刻表,害我們等車等到快被晒死。還有去哪裡?才一年多前的事我就快忘光了,好像還去了個什麼牧場來著?」
一起在溫泉民宿睡通鋪,一起等錯過的公車,一起在豔陽下走得快脫水,而後嚐到的第一口冰涼酸甜的檸檬汁;玩到半夜還不睡,大家窩在民宿客廳,聊得累到迷糊闔上眼;在大學校園玩比手畫腳、牆壁鬼等遊戲,對升學毫無幫助,也不影響工作前途,然而回想起來,那些「沒意義」的事,都是珍貴的回憶。
「大家在一起製造的回憶好多好多,都是當時才做得到的事。」盈盈曾說過。
回憶的價值,愈是沉澱愈能讓人明白。
那時無憂無慮的他們,在記憶中幾乎是閃閃發光,閃耀得令人嫉妒。
解一樹按捺下情緒,問蘇炯均:「現在說這些要幹嘛?」
蘇炯均仍是笑笑地說:「突然覺得,我十年後大概會後悔吧。我以為我不會在乎那些,結果印象比想像中深刻,可能這輩子都忘不了。」
「你在畢旅的時候差點為『她』犧牲,為什麼這次反而不去。」
「因為我不夠了解『她』,我以為她跟我一樣,還是把我們的未來看得最重,沒想到,她早就改變了。我真是白痴。」說完,蘇炯均就轉身離開。
在畢業典禮結束之前,解一樹去學餐買了兩杯飲料。
盈盈愛喝的珍珠奶茶微糖去冰,率優會喝的柚香蜜紅一分糖去冰。兩杯飲料分別放在她們倆的桌上,他靜靜在空蕩蕩的教室角落坐下。
祝,畢業快樂。
4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RoDKxTQJw4
數十年後
從天橋走下去,是長著兩排銀杏樹的人行道。秋風調皮地吹走行人的毛帽,還在狼狽追著帽子跑的倒楣鬼耳邊嘻笑。
她搓著脖子,冷得受不了,從包包裡拿出圍巾。第一次買圍巾的她不知道要怎麼打結固定,於是由他代勞。
要替她圍上圍巾時,他失手讓圍巾落在地上。紅色針織圍巾被風颳到一段距離之外,所幸沒被吹到馬路上。
「抱歉,弄髒了。」他彎腰要撿起圍巾,但她快他一步。
圍巾沾黏上一枚銀杏葉,黃色葉片在紅圍巾上十分顯眼。她拿起葉子,鄭重地把葉片收進口袋,彷彿那是珍貴的禮物,微笑說:「謝謝。」那抹笑容令人眩目,像是冬天偶然從大樓間探出頭的一絲陽光,偏偏要和寒冷作對,帶給城市中的人們溫暖。
被風吹落的銀杏葉灑落在他們的頭髮和大衣上,她笑著替他們倆拍掉銀杏葉,將圍巾在脖子上繞兩圈後,仰起臉讓他打結。他冰冷的手指小心地不碰觸到她的肌膚,免得凍著她。
不遠處的號誌燈轉為綠燈,發出滴答聲催促他們前進。他一步也不想動,願永遠駐足此處。
如果可以多注視著彼此幾秒,或許這份感受就會化為永恆,變成壓在記憶抽屜底部的一枚銀杏葉書籤。
「學長,該醒了。」
溫柔的聲音喚醒他,當他看見陵友的臉龐那瞬間,立刻想起現在自己所處的位置。
他定時會請陵友動用夢的能力幫助他重溫過往時光。在夢裡,他不記得任何痛苦的回憶,回到少年時代,和「她」吃冰淇淋、喝珍珠奶茶,討論一本書或一部電影的結局。夏天可能是冰涼的,冬天也許暖和如冉冉營火,詳細的內容他記不太清楚,只知道他們歡笑著。
過於耽溺回憶並不好,這個道理誰都知道,但是陵友從來沒有開口說教;而他遵守著一個月一次的頻率,不多也不少,正好能支撐他走下去。隨著閱歷增長,陵友的夢造得愈來愈臻純熟,讓身在其中的他不再感覺突兀,也或許是因為陵友特別珍重有關「她」的回憶,隔一段時間就會拿出來打磨。
長大後,陵友愈發出落得清麗,和他記憶中那需要學姐作為情感依靠的小妹妹不同,如今已是個成熟穩重的大人,事業上的表現也十分出色。在她哥哥的幫助下,她背負起命運交付的責任。她的容貌和軀體不再衰老,永遠停留在19歲左右的巔峰狀態,以對抗全世界的惡意。
告別前,解一樹交給陵友一包魚乾。
「送給妳家貓咪的。」
陵友笑得開心。「謝謝,他很喜歡你做的零食。」她送他離開宅邸大門。
記憶是會流失的,就像解一樹得了阿茲海默症的爺爺,自從記憶力衰退後,他的人生宛若被偷走。有時爺爺會以為自己是十五歲的少年,或還活在意氣風發的三四十歲壯年時期。年輕的心靈困在衰老的肉體中,這份痛苦難以言喻,更難受的是,他的妻子、此生的摯愛,奶奶在他六十幾歲時去世;張開眼睛,爺爺有時會以為愛妻還在身邊,一問才知心愛的人已不在,卻出現號稱是他孫子的陌生人。回憶變成一種折磨,無法辨別真偽讓他極度暴躁,因為他已經沒有可以信任的對象,包括他自己。人生成為謊言。
在很小的時候,解一樹和父母一起看了一部電影,內容是關於女主角被控制忘記自己兒子的存在,最後憑藉著愛的力量,她成功奪回記憶的掌控權,救出兒子。解一樹那時感到的應該仍不是害怕,卻也相當不安。媽媽告訴他,她絕對不會忘記他,但年幼的他已知道,有些人就是會忘記某些事物,這不是愛或其他虛無縹緲的力量可以扭轉的。
似乎在夢夢醒醒中浮沉,真實或虛幻難辨,接下來,他就只是順著時間過每一天,不再認真探究其中的意義。
終於,在某個長得醒不來的夢,當他在夢中看見銀杏樹下的少女,他也再度變回清俊的少年。她站在那裡,恬淡的微笑讓周遭空氣的顏色融化成溫暖的色調。屬於他們的回憶的顏色。
回憶和真實總有出入,時間的沉澱可以讓原本美好的事物變得更美麗。飄揚的髮絲、不安的腳尖等熟悉的元素,都真實到不真實。
她看著他向她走去,一語不發,但是眼中盛滿收斂的熱情。她期待著他先開口。
那天溫柔得模糊的景象,重現在眼前。
他看著遠比印象中更美麗的她,唯一能說出的話是:「對不起。」
顫顫巍巍地,這句話剝開他舊傷的厚疤,酸楚和疼痛傾瀉而出,吞噬掉其他的想法。
他違背了諾言。就像無法阻止衰老帶走他的生命力,珍貴的記憶被切割成細碎片段,像細砂般一一從腦海流失。到人生的最後,他甚至無法記得她的樣貌,或是在醒來的時候想要找她,卻被告知她在幾十年前就過世了。每天都被迫重新感受一次失去摯愛的痛。生命是段漫長的刑期,他只能承受著。
但是,他又再度遇見了微笑著的她。
儘管肩上承載著過重的塵埃,她的笑靨有著未被世俗摧殘的單純,周身散發的柔和一如既往。
「沒有什麼是永遠不會失去的。」她說,她眼眸中的暖煦傳遞給他溫度。「即使被忘記,也不會消失,因為存在過的事實不會改變。」
她伸出手,靠近他發抖的手。兩人指尖相觸剎那,所有遺落的回憶都以跑馬燈的形式歡騰地重映。
從最初到最後,那些早就遺忘的細節,清晰無比地竄流在他們之間。
「不過可以想起來和被想起,真是太好了。」她說。
他看著淚中帶笑的她,終於釋懷。
「我一直相信。」他說。
「相信可以再見到我?」
「對。」
「你的堅持終於有回報了。」
解一樹緊緊地擁抱住鹿盈盈,她的輕笑停駐在他的耳畔。
於是孤單一詞,正式與他們走上陌路。
4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Cf8t4vnD7Y
更久之後
異國陽光為她的瞳孔鑲上一圈金邊,她仰起頭,眼中燦爛的顏色充滿生命力。身邊經過的人們對自己即將面對的危險一無所知,偶爾有幾個人被她獨特的氣質所吸引,回頭看了這個穿著純白東方武裝的女孩
不老不死,這樣的恩賜,是為了迫她不斷前進。
自小到大,她的夢想都只有一個,旅行,走遍世界的每個角落。認真去品味,就連醜陋雜亂的街景,也會在回憶中被美化。然而,她對於前行的熱情逐漸消褪。當身邊的人一一逝去,所有景象,都成了孤獨的隱喻。
好孤單。
快要被寂寞淹沒。
她在回憶中載浮載沉,或許早早溺斃是比較好的選擇。否則要背負著悲傷走下去,也太痛苦了。
即便如此,要等到任務結束,也就是世界毀壞或是她被粉碎,她才能夠自由。
靈貓的爪子搭在她的小腿上,將牠所見傳遞給她。她抬頭,凡人會看見正上方的天開開始聚集起陰鬱的雲絲,靈貓看見的則是一道空間裂縫的生成。
她抱起靈貓,讓牠爬到她的左肩。一人一貓挺直身板,無畏地正視那一觸即發的危險。
「我們一起走下去吧。」她握著靈貓伸出碰觸她臉龐的爪子,輕聲說。
並且對著從異空間裂縫中擠出的身影,揚起銀棍。4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5nGpvhqC4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