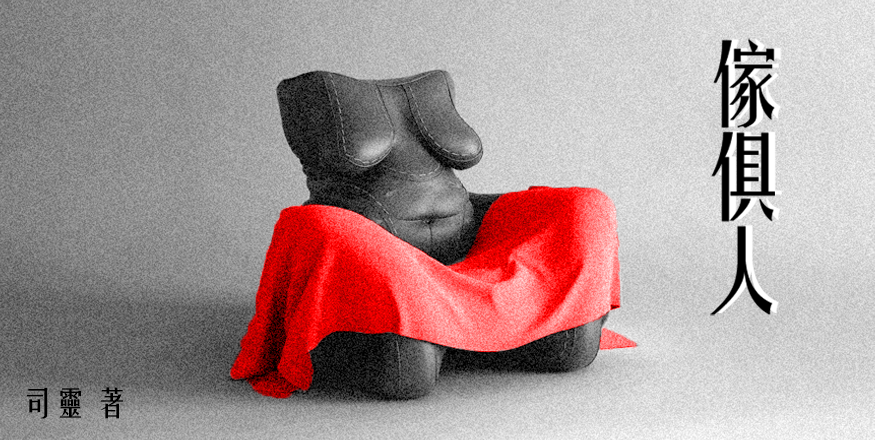當母親投入我的懷中時,我的身體亦染上母親的氣息。對方的觸感自有記憶以來從未嚐過。母親的心跳,原來是這麼虛弱;母親的體溫,又原來是這般冰冷。母親安心地躺著身上,我宛如捧著快要碎掉的瓷器,溫柔且小心翼翼地對待。
在這種場合,以如此形式,才能彼此近貼地感受對方,實在過於諷刺。
主人一併攀上了床,修長的蛇足纏上母親。她見狀不禁別開了臉龐,反而徹底坦露髮絲下紅透了的耳根。主人注視著自身膝下的美景,得意地揚起豔唇,顯然不會忘記床的真身正是我本人,同時是這位女性的血親。可是她卻沒有絲毫在意,不,正因為得悉,才能成為歡悅的情趣。
二人份的重量不留情地施加我的身上,經歷著比以往更撕裂般的劇痛。痛苦並非單純的加法,二人份的痛苦抵達臨界點後就分不清差別,超越了自身所能承受,宛如身體化作痛苦本身。可是這片空間與我體內翻騰的撕裂相反,充斥異常的寂靜,那宛若暴風雨的前夕,彌漫不安的同時混著曖昧的氣息。
我猛然醒覺,床的另一個用途。
床,不止是休息身心的地方,亦是連結彼此的場所。
此時此刻,我僅被當作拉近二人距離的道具。道具是沒法拒絕,也沒法逃避。從來沒人會使用道具時在意它的感受,然後問候一聲「可以用嗎?」。在二人陶醉的花花世界裡,我甚至沒法納入他們的眼角,身下的那件「東西」毫不重要,只要不影響接下來要做的事就沒問題了。
拜託!給我停下來!
拼命的吶喊,始終無法化作有形之聲。
縱使我渴望出手阻攔,卻沒法制止;渴望發聲警告,卻沒法傳遞。比起肉體上的虐待,精神的折磨更將靈魂的劇痛扯至瀕死般的顛峰。
我掙扎著,掙扎著,渴望從這不亞於地獄的空間逃離。可是傢俱人連闔上眼皮抑或掩蓋雙耳也沒法做到,猶如被強迫綁在處刑椅上,只能眼睜睜地觀看著如惡夢般的荒謬,在我的身軀上放映。
全裸而任人宰割的母親,以及俯視而魅笑的主人,二人無言地對視。母親主動劃破寂靜,她深吸了一口氣,連著臉上的羞澀吞進肚子。只見她緩緩張開雙臂,混濁的黑瞳深處映出了最後的決心,那像是要擁抱一切,又似是要捨棄一切的眼神地投向主人。
「主人,請將我身體的不淨去除吧……」
母親的願望落入主人耳中,化作甘甜的誘惑,誰人聽狀也無法奈住矜持。主人端看眼前期待良久的果實,舔了舔豔唇,濕滑的舌尖為指尖塗上了潤液。未等母親反應之際,修長淨白的手指探向母親的雙腿間,使對方忍不住洩出一聲輕吟。
「你放鬆一下,接下來交給我就可以了。」
母親輕闔雙目,咬著唇角地點了點頭,放任主人輕柔的愛撫。伴隨時鐘上分針的挪動,櫻唇中的吐息從平穩轉為吝亂,沾上臉龐的髮絲泛著汗水,腳指開始不安分地緊繃亂晃,為二人的空間染上一片桃色。
女人的理智與矜持早已被一次又一次竄遍全身的酥麻抹去,只能任憑釋放的欲望緊握對方的手腕,又不由得地放開,從嬌喘的唇邊無數次地嚷著主人。眼前的女人已徹底淪為自己的所有物,一舉一動亦牽動對方的身心。主人享受由自己栽培調味的佳餚,這份無可比擬的征服感。
然而一切僅是開始,母親全心沉醉美妙愉悅的體驗,卻沒為意主人臉上那副鬼畜的邪笑。只見將摳弄的指尖緩緩探入深處──
探入的不止指尖,
指、掌、腕、臂,
直到主人的右手被完全吞沒,對方的腹下猶如貪婪吞噬的蠕蟲,擴張得讓人駭然。尖厲的嘶吼從母親的喉嚨深處擠出,戳破方才粉紅色的泡沫,周遭的氣氛剎那劇變為獵奇的混沌,眼前的情景讓人不禁聯想牧畜的分娩。
「很痛!主人我很痛!」
母親苦苦哀號,只見五官揪成一團,緊咬的牙關滲出了血絲。可是主人沒有放輕的意思,而是凝視對方的雙瞳,像要挖出深處的本心。
「即使如此,但不想我停下來對吧?」
「……」母親片刻凝住,就連嗚咽也吞進腹裡,只是默默點頭。
「誒,只是不想我停下來嗎?」
「我……還希望更多……」
面對主人荒唐的探問,母親不但沒有否應,反而吐出匪夷所思的渴求。扭曲的她失去母親的身份,更失去了作為人的資格。
「很好,那才是我出色的僕人。」
主人對回答頗為滿意,並往右手施多幾分力度,好像要將內臟絞碎似的,動作沒帶半分憐憫。比出產更強烈的劇痛竄遍身體每個角落,母親的四肢頓然抽搐癲癇,唾液不自控地從嘴角淌下,房間被撕聲力歇的叫喊淹沒,那恍若來自地下酷刑的尖叫傳遍整間宅邸。
快被衝昏意識的她胡亂抓劃,只顧狠狠抓緊我身體的一角,彷彿快要將我扯撕。對方的痛楚亦沿著深深陷進床單的指尖,毫無保留地傳到我的身上,一同體驗這份不講理而刻骨的痛苦。
匪夷所思,使人費解。
一幕又一幕讓人窒息的景象在眼前上映。
此刻發生的一切大概是搞錯了什麼,我從一開始不應該身處這種地方。明明幾個月前我還是一個懷著美夢的小女孩,有著不正常但勉強維繫的家庭,過著姑且的日子。
或許這純粹是一場不幸運的惡夢,然而每當我試圖如此催眠自己,身上清晰的痛硬生生地將我扯回現實,強迫我正視比文字更刺激數倍的瘋狂。在無休止的撕吼與扯痛的浸染下,我已逐漸放棄了抵抗,也放棄了理解,一切只會徒增痛苦。
開竅了的我放下了執住,轉而擁抱受苦的母親。儘管她是無可救藥,但我彷彿從她身上看到了自己,替她分擔是我現在唯一可做,亦是正適合傢俱人所做的事。縱使作為傢俱人無法做到真正的擁抱,但我仍能盡我所能,運用主人所說那份「心」的力量。
「你現在的姿態前所未有地耀眼。」主人湊近她的耳邊,如床伴甜蜜般微微細語。
母親已失去對身體的支配,甚至不曉得有沒有聽到主人的讚美,那宛如在生死邊緣爭扎的慘狀,正被主人盡收眼底。母親愈是痛苦,主人愈是愉悅,猶如擔任冥府的指揮師,享受當下由悲嗚構成的演奏曲。
「忍多十秒就好了,這十秒我要你細心咀嚼,品味,並盡情投入。」
若幸福是由人自行定義,那痛苦也可以是幸福的其中一種形式。這十秒的痛,將引領至從未體驗的頂峰,那是超脫肉體,抵至靈魂的極樂。
「十、九、八……」
伴隨主人持續的低語,母親逐漸在地獄中尋得愉悅。本來扭曲的五官,漸漸咧嘴而笑,劇痛而淌的涕淚滿塗不相襯的笑顏。從旁人眼中,彷彿被惡魔附身般詫異無比。
「四、三、二……」
空間逐漸扭曲,陷入天旋地轉,不,扭曲的不是空間,而是自身的意識。腦袋如同嗑毒一般,步入瘋狂的螺旋。
「一、零……!」
主人的倒數完畢同時,腹腔裡的拳頭蠻力抽出。伴隨母親猛然誇張弓背,一陣讓人不適的排泄聲從腹下持續傾湧,那是本不該從人體裡發出的聲響。
房間不絕的嘶吼畫上了休上符,重返寂靜的四周卻換上另一種沒法言明的詭譎。似要虛脫的母親如脫線的人偶,失神地躺在我的身上,混雜汗水和體液的分泌物早化為一灘灘水印,將我無情地沾濕。
母親身上的痛楚褪去,無聲的快感瞬間灌入全身,這種如乘坐過山車的解放我最為瞭解。無視大腦萎縮,放任神經燒斷,腦袋像要將人生本有限度的多巴胺不顧後果地拼命搾取。母親雙眼反白,挖盡喉嚨深處仍無法哼出半聲,源非痛覺的殘留,僅是被氾濫的禁忌愉悅淹沒。
母親努力重拾呼吸,眼眸恍惚的餘光,掠至被體液沾濕的主人的纖手。手上端著的,並非人形的東西,亦無沾上血跡,說到底那連生物也不是,若要從熟悉的東西中挑選匹配的名詞──
一朵鮮花。
人當然不可能誕下植物,將人變成人外之物,那是主人一貫擅長的把戲。
無法細數的花辮繞著花蕾的綻放,花冠彷彿吸盡了血,比世上見過的花更要鮮艷,更要腥紅。仔細凝視,花辮上的脈絡像活物似般律動,混然散發著不祥之氣。
主人轉動花柄,讓每一寸花瓣淋浴在燈光之下,仔細欣賞親自摘取的收成。食物要吃在新鮮時,主人未花上太多時間觀賞,她將鮮花貼近了同樣鮮紅的唇,然後直接一口吞下。
本應是生命之物淡然消逝,無限的可能性被迫迎來終焉,換來的,是主人洋溢陶醉的臉龐。
母親將視線落到空空如也的下腹,該處已不會再孕育喜或悲。她輕闔雙目,感受至出生從未體驗的輕鬆。從她身上掏去的不僅是胎兒,更是身為女性的部分。
我意識到身前這位母親,已不再是我的母親。同時我靈魂中佔據重要的一角,亦如抓不住的灰燼,於風中隨之散滅。
一切將要落幕,皆要步入尾聲。
在這齣悲劇的最後,她臉上盛開的,卻是如新生嬰兒般不知苦與惱,無比安寧的笑顏。這副與剛才混沌相反,只有純粹的景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靈魂之中。
原來,人是可以掛上這樣的表情──
這副捨己的姿態未能稱得上正確,但絕非錯誤。
若要評論美醜,那想必是美。
若要辨別善惡,那想必是善。
任誰目睹這副如同象徵幸福的表情,所有理直氣壯的嗤笑、指責、辱罵,全都一一吞回肚中,心中不禁傳出躁熱的悸動。
「想必,這就是我靈魂的渴求之物吧。」
是母親的心聲流入我的腦海嗎,抑或是……
無論如何,對母親而言,這才是最適合她的結局。
「前菜差不多結束了。」
主人凜然地劃破了安寧,一手扯下正要拉上的布幕,絕不允許如此輕易結束。戲謔的眸光俯瞰剛回復過來的母親,對她伸出了沾濕黏稠的纖手。
「那正式開始吧,從親自清潔被你弄髒了的地方起。」
深夜的弦月仍然高掛,這片無人打擾的空間,彌漫著意猶未盡的芳甜氣色。
母親怔住半刻,似乎明白接下來將發生何事。她與主人四目深情相交,手指輕撫頸上的項環,緩和著未完全褪去的痛楚,又似是在期待內裡又一次的填滿。
在她的眼瞳中並沒有不安,也不用再感到不安了。
「好的,主人。」
啊,這漫漫長夜,似乎仍會繼續──30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bsDHMCYyfS
30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dgUwzAEbFV
307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sViTqgHi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