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距離很近,他幾乎是能感知到青年霎時屏住再舒展開的呼吸。臧十認真注視著那雙有些心虛的深邃黑眸,鼻尖抽動幾下,漾在空氣中的是家裡肥皂的淡淡香味。
「呃、不,不是……。」
青年撇開視線,單手握上男人粗壯的手腕,將其移開,先暫時置於腿上。
他想著對這個人也沒什麼好不說的,不過畢竟臧十是救過自己的人,提起隨意被棄置的生命可能還是多少有點不禮貌。
「是祭司做的。」
「你不是說你沒有這個問題?」
「是。我昨天是被派去解決祭司的人,但剛好我和他比較熟,所以就……拜託了他一點事。」
聽寧沒有明講,或許是顧慮他、或是認為對他這個才認識沒多久的人說那麼多沒有意義。他知道的,也從對方的話中聽出了端倪。
寧……似乎在尋死。
漂亮的金色眸子黯淡下來,男人放開攬住青年腰部的手,向右邊挪動身體,給他一點空間。
他不打算追問,也不覺得自己能夠影響對方的這種想法,更不會覺得自己拯救了這條想死的命有多了不起。
「……對不起,讓你救了一條這樣的生命。」
青年壓制微微發顫的語尾,低垂著頭,黑短髮落下遮蓋清秀的眉眼。他雙手輕放在蓋著棉被的腿上,左手覆蓋著右手腕,有意無意地摩挲,就像是習慣動作。
「我不這麼覺得。昨天我找到你,然後帶你回來。你醒來第一件事也不是殺了我,這樣就好。」
男人起從床鋪起身去倒了一杯水,幾分鐘後又拎著像牛奶瓶的玻璃小杯回來。看著面前仍像隻落魄小貓一樣的青年,他忍俊不禁,用微涼的玻璃瓶抵上他的髮,總算是讓那張委屈巴巴的小臉抬了起來。
「你都那麼說了,我也不留你,你隨時都可以離開這裡。但至少喝點水再走?」
下垂的眼尾令人心疼,但臧十只是把玻璃瓶貼上他的臉頰,突來的涼感使他顫了一下,才伸手接過瓶子打開來喝。
仰頭暴露出上下滾動著的喉結,飲得太急,嘴角便溢出幾滴透明。被瀏海蓋住的眼睛看不見表情,但不知為何在那之下也流著透明的淚。
玻璃瓶口離開嘴的那一刻發出了啵的一聲,軟舌舔了舔嘴,兩片唇瓣好像開開合合說了什麼,卻過於輕聲細語以至於臧十都要覺得面前的人兒好像換了一副靈魂。
只是提到了他們做這一行常常在面對的死亡,區區了結天使的祭司就慌成這副德行,實在不讓人覺得他有勇氣面對自己的死。
所以才要請別人下手嗎?那麼他可能找錯人了。那位說是和寧比較熟的祭司,在開槍和下刀的時候都避開了重點部位,甚至胸腔都沒被開洞,這樣的作法非但不會輕易了結性命,只可能令目標是因為失血過多而死,並且徒增痛苦。
稱得上熟人的話便不該這麼做的,除非他也害怕做這種事。
男人蹲下身,將左耳湊近青年嘴邊聽著他的聲音。微捲的髮絲撓著他的側頸部,他感覺到一旁的人兒往他這裡低調地蹭了下。
「抱抱我。可以嗎?」
「……這種事不是隨便可以做的。」況且我們才認識沒多久,更不是彼此的誰。
他與青年拉開距離,雙手捧起被淚痕摧殘得亂糟糟的清秀臉龐,使力像在捏糰子那般揉了揉。「雖然是很久以前就有的東西,但現在也還有人在用。這我可是知道的。」
他對這個世界還有依戀。臧十不信這樣的人能夠輕易捨去生命。
要不是手中的寧在這之前與他素不相識,他都覺得自己都要跟著碎掉了。心臟,靠近心臟的地方好像因為面前這名青年說的話而稍微動搖了,感覺有點悶悶的痛。
誰會向一個常在奪走性命的天使求助?男人甚至覺得他雙手一捏,就可以摧毀這個看起來易碎的漂亮青年。
然而寧沒有任何回應,就是任著他的動作,讓他下不去手。
白皙肌膚下的血液湧動第一次讓他感受到生命的真實,按在頸部的小指感受到了一跳一跳的脈搏。刀槍皆可,但他意識到自己無法以雙手了結這樣的活物。
男人緩緩將雙手由青年的臉部下移到肩頭,身體湊近,輕輕擁著對方。老實說先前講的還是有點誇大了,他聽過這東西,但實際做起來又是另一回事。
臧十感覺到與他相觸的那副身體微微顫抖著,接著拉過他只是搭在肩上的手,狠狠地相互擁抱。
懷中的寧身上都是肥皂淡淡的花香,得要將鼻尖貼上青年後頸的熾熱肌膚才能稍稍將那股清雅與人的味道都收至鼻腔。
從未做過的親密接觸是與一位剛認識不久的青年,或許是因為他不懂這之中的含義所以不覺哪裡奇怪,反而在觸碰過對方之後變得稍微能夠接收對方的情緒,產生了有點想要聽他說話的想法。
但也只是一點而已。身為天使,他第一次拯救人、第一次親吻、第一次擁抱。不過或許這些體驗也會是最後一次,因為這個人將死。
寧只在他這兒待了半天多一點,向他小聲道了謝之後便拖著扭傷的單隻腳離開。他說如果要那麼做的話,不必養好身體再去。
如果說栩巍是為身為天使的他畫上了生命中的第一個暖色調,那麼寧就像是夏夜的煙火般,華麗且暴力地闖進他的視野,卻又在抵達最高點之後匆匆離去,不留痕跡。
要不是自己的衣櫥裡頭真的少了一套夏季私服,臧十都要覺得這或許只是因為自己太累而幻想出來的夢了。6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T4YGmHQtS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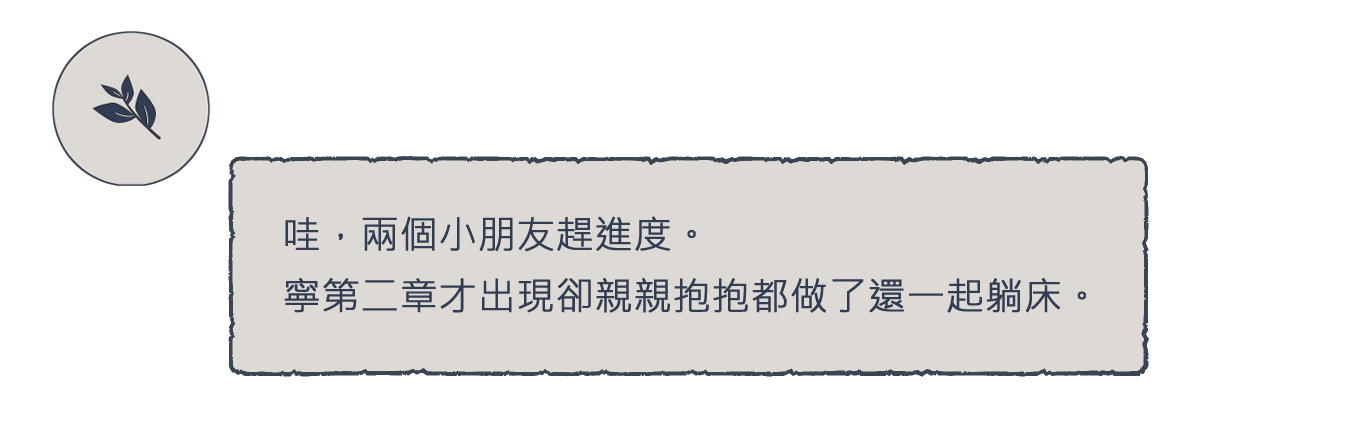 6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DYckb3oEUr
66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DYckb3oE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