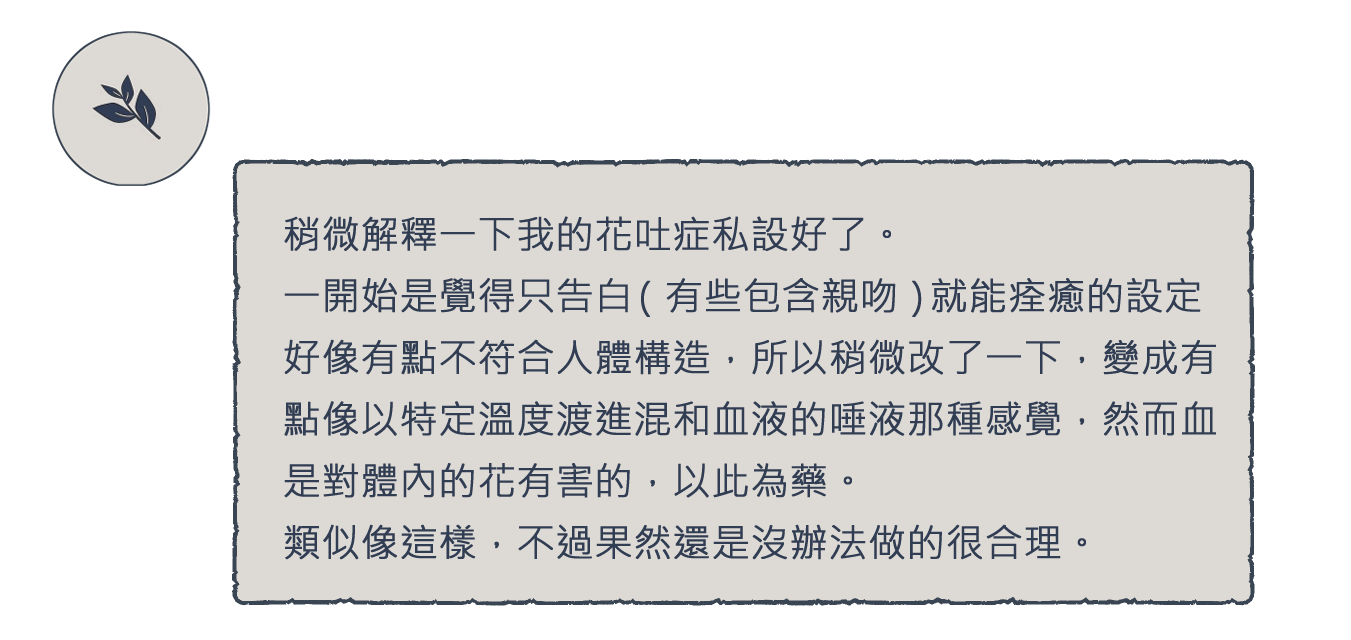「——蕭織,請把寧給我。他很可能快不行了,我得想辦法救他。」
花吐症。曾經在夏林身上出現的精神病症出現在他腦海。
明明這個時代因為醫療和科技發達的關係,多數身體疾病都有治療方法,但出現在人們身上的精神疾病卻越來越多,甚至還有基因遺傳的傾向。
花吐症便是如此,且會致死。無可救藥地愛上那個人,卻無法在花開之時得到對方的愛、交換一個吻和對花朵來說是毒藥的血液,便會令體內的寄生花瘋了似地蔓延擴散,直至摧毀整副身體,宿主死亡。
隨著病況嚴重,宿主會從嘔出破碎的花瓣到整朵完整的花。那時候就差不多了,表示寄宿在身體裡的花已經成熟,準備摘下甜美的果實,而養分便來自宿主濃濃的愛意與血。
夏林找到了夏楠,解除了屬於他的夜來香詛咒。但寧呢?他在這種關鍵時期硬是要離開,最後倒下了。這肯定不是去找解藥的樣子。那麼,是誰?
「寧哥讓我帶著他逃走,不管誰來都不行。」
少年高䠷的身軀微微發抖著,或許是被剛才樓下戰鬥的槍聲嚇著了,兩隻眼睛瞪得大大,努力盯緊左手臂全是血的男人。
「拜託了,我不想傷害你。」
「……我不可以為了自己,因為寧哥可是『目標』。」
臧十怔了一下,趁著這一瞬,蕭織看向他的眼神變了,手裡拿著他們第一次見面時,他在競技場裡刺下岳染的匕首。
銀色刀尖在陽光照射下亮著光,對上那雙添了一絲威脅性的眼睛,臧十仍然沒有退卻,或許是因為知道自己可以贏過這名少年。就算對方曾展現過過人的精湛近戰技巧,有實際經驗的臧十還是比較佔得上風。
他還是沒有要傷害蕭織的意思,所以當對方背著寧向他衝過來時,男人手上沒有拿任何武器,就只是準備好雙手,在刀刃碰到自己之前的近距離抬腿踢掉,捉握少年的兩肩,一個翻身將少年固定住,令他無法動彈。
或許對方背後背著的人兒也是牽制他的一種手段,他們知道他傷不了寧。
臧十盡量放輕動作,用大衣外套的腰帶綁起蕭織的雙掌,身體將他按住,從口袋裡掏出了快速助眠藥劑讓他吞下,掙扎沒多久便起了藥效。
他讓少年平躺在屋瓦上,解開他手上的束縛和背後背著的寧。碰上身體發冷又虛弱的青年時,男人心疼得恨不得把自己的命都給他。他怪自己太晚發現寧的異狀,怪自己隨便就接受了對方沒什麼大礙的說法。
寧已經失去意識,全身沒有什麼力氣。這也是當然,剛才臧十在陽台看見的曇花,八九不離十就是出自面前這人。
男人牢牢抱緊青年冰涼的身體,溫熱的雙掌捧起蒼白的臉,額頭輕靠、鼻尖廝磨。
寧還有一口氣。就像當初把人撿回家的景象一樣。
但是是誰?讓寧沉醉其中的人是誰?他得拿到那個人的血才行。
——爸爸,你喜歡寧哥嗎?
——爸爸你不要怕,寧哥有說過他也愛你。
「……寧,會是我嗎?」
與體溫一樣熱燙的淚從男人的眼角滑落,滴至青年毫無生氣的臉。面前這個人不會回答他,但沒有試試看誰知道呢?
臧十麥色的臉龐湊近青年,薄唇微啟,齒用力咬破嘴唇,軟軟地貼上對方,有些害怕地利用舌頭把自己的血液渡到寧嘴裡。
輕含著冰涼的嘴唇,男人小小力吸吮著,想要藉由這樣也把自己的體溫傳過去。漫在兩人口中的血味此時沒有腥臭,反而因為淚水而帶著淡淡鹹味。
小舌還不太會控制力道,奮力侵入著青年張開的口腔,對方軟軟的舌卻仍然平放,沒有反應。
好痛,他好痛。心好痛。他想看見的是寧的笑臉和漂亮眼睛、溫暖擁抱。不是這種。
這個吻一點也不美妙,他不想在對方是這種狀態的時候吻他。
拜託醒來。
小口小口喘息,臧十離開青年染上血液的唇又吻上去,一直想著該給多少血量才夠,他害怕最喜歡的寧死在自己手上。
顫抖著擁抱,鮮血從青年嘴邊溢出流下。男人不安地將手指置於他的鼻下,探到微弱卻穩定的氣息,稍微放了下心,再次抱緊懷裡的人兒。
脫下外套罩住穿著單薄的青年,他不斷說服自己寧是在大冬天的穿這麼少才那麼冰冷,一邊將包上外套的青年背上背後,再用外套綁帶固定脫力的身體。
兩手扶著寧懸空的腿起身,他壓根兒還沒想好等等要怎麼出去,身上背著寧肯定無法像剛才那樣戰鬥。
放開穩穩固定好的青年雙腿,男人也抱起因藥睡昏過去的蕭織,準備再從剛才的陽台處下樓。
「等等!臧十哥。」
清爽稚嫩的少年音在他身後響起,男人穩住腳步,燦金色眸子對上岳染那張擔心的表情。
「我沒有要傷害他們,岳染。」他連忙解釋道。
「我知道,抱歉我剛才躲在後面偷看你們。我替蕭織向你道歉,其實、其實他這幾天剛成年當上天使,心理狀態不太穩定才會——」
「嗯,謝謝你,岳染。」臧十走近少年並在他面前蹲下,讓睡著的蕭織倚著自己的身體,空出來的那隻手握上少年,讓對方的目光正對著他。「我大概有猜到。你別擔心,我只是讓他吃了藥睡著,這同時可以讓他冷靜下來。醒過來之後陪他聊聊開心的事,精神狀況應該就會好一點了。」
「——!謝謝你!那個、呃,蕭織交給我就可以了,我帶你們從這裡下去吧。」
少年接過蕭織輕盈高瘦的身體,轉身往屋頂的另一邊下樓,帶臧十經過他們兩人的房間,放下昏睡的少年之後繼續往連他都不知道的密道離開宅邸。
把尚未恢復的人放在後座,臧十向岳染道謝之後便匆匆驅車前往醫院。他認為還是有必要去讓專業人士檢查一下剛才他渡給患者的血到底有沒有起作用,況且寧有合法身份,不必再顧慮其他。
在大白天拖著滿是血的受傷左肩,手上又抱著一名昏睡的青年,任誰看都會覺得奇怪。進了急診,不知為何多數人都讓了位置給他,寧也很快就排到檢查。
醫生確定是花吐症,現在他的身體正在努力對抗種子,有逐漸轉好的跡象。
臧十如實告訴醫生寧不久前才被餵了血,也從醫生那裡獲得接下來的照護辦法。他說寧的情況不需要住院,但在家照護可能會比較累和麻煩,若是要住院直到身體狀況和意識好轉也可以,在這裡會有專業人員幫忙。
「我覺得還是不用了,我應付得來。」說起來也是他害的。
「一般人很難察覺這種病,難不成你是當事人?」
「……以前有遇過。我的朋友也有這個病,剛好就是他的血親。」
「哎呀,但這可怎麼辦?這位先生身上的花種子並不是遺傳的呢。」穿著白袍的醫生看了電腦一眼,或許是在確認病例。
寧是夏林的哥哥,兩人都為這種精神病症所苦,卻不是遺傳?
臧十思索一陣,腦中忽地冒出一段青年之前和他說的話。
——她偷了我的身體,冷凍起來,存封二十多年再注入抽取一堆有的沒有的。
這就是後天播下的花種子嗎?為了牽制寧,把他留在身邊而埋下的不定時炸彈?
各種資訊都詭異得能夠對上,臧十打了個冷顫,下意識握起床邊青年逐漸恢復體溫的手。
「我們剛才有幫他打了藥,會加速身體恢復的穩定性和速度。在家照顧記得注意安全,恢復期大約是兩週到一個月不等,因為先生的情況比較嚴重,所以等待甦醒的時間會稍微長一點,其中有任何異狀都不要隨意餵血,先送過來醫院讓我們評估。」
「我知道了,謝謝醫生。」
拿了藥之後回到家,醫院的人還幫忙他處理了肩膀的傷,所以現在不怎麼痛,也有力氣抱著青年回到房間。
挪開棉被,男人輕輕將寧放到床鋪左側屬於他的位置。拆開包著瘦弱身軀的呢絨外套,替他墊好枕頭,薄薄一件圓領長袖上衣實在不足以應付飄著小雪的台北冬天。
臧十偌大的手放上青年撩開瀏海的白皙前額,稍微比自己低了一點,那表示體溫正常。他洗了濕毛巾來放在床頭,溫暖的濕布以剛好的力道由上而下擦拭青年的全身,臧十還順便幫他換了一套溫暖一點的冬季睡衣。
蓋上棉被,闔著眼平穩呼吸的青年看起來不像是熟睡,而是更深層的意識脫離,臧十總感覺寧現在或許不是和他們在同個地方,而是一個人在體內與花種奮戰。
男人緊握青年,頷首在對方的手心吻了一下,接著雙掌包覆那隻骨感的手,輕輕貼上自己正重重跳著的心臟。
就算寧感受不到也沒有關係,他會一直在這裡陪著他。
「你一定要好起來,寧。」
42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ajfIpEjhy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