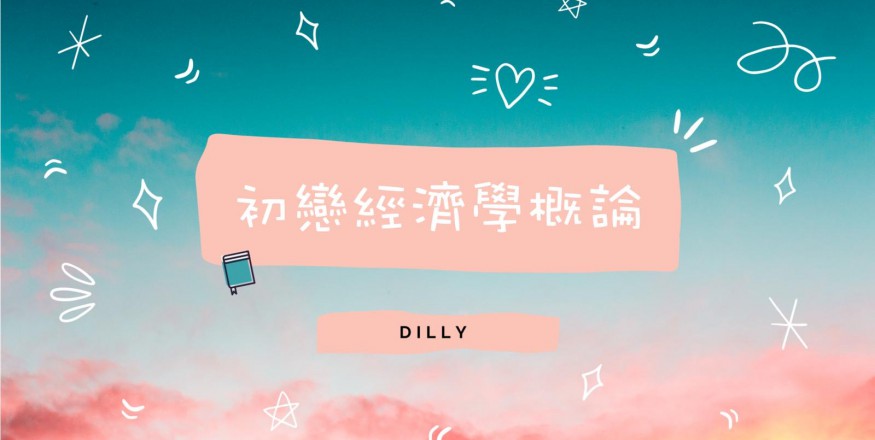阿寒繫上圍裙,把意大利粉放進滾水,同一時間在另一個平底鍋煮著白汁,動作有條不紊。他把兩碟似模似樣的意粉端出廚房,母親剛好下班回家。
「你那體育課程讀得怎樣了?」母親一邊吃著阿寒炮製的大餐,一邊問道。
「還不錯,和同學們有時侯會一起去做運動。」
「話說嘉嘉最近只匯錢到我的銀行戶口,都很久沒回來和我們吃飯了,你問問她甚麼時侯有空。」
阿寒默然,過了好一陣子才說:「嗯,我問問。」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他沒有再和嘉說過半句話,也沒有像個傻子般跑到她學校。他滑著社交媒體,嘉卻始終沒有更新過任何東西。最終他打了一通電話。
「喂,貝以寒?」林以愛吃了一驚,她到底有多久沒接過阿寒的來電?
他尷尬地乾笑了兩聲,「我找你是想⋯⋯」
「你和張羚嘉的事,我全都知道了,所以你有話就直說。」以愛還是那麼的爽直。
「我有些東西想託你交給她。」之前嘉說總覺得宿舍少了一個攬枕,他便特意到家品店精挑細選,沒想到竟然再也送不出。
「星期五晚,十時,宿舍樓下等吧。」
去到宿舍樓下剛好是十時,他不敢早到,怕與嘉撞上。以愛並不是從宿舍下來,她在遠處和一群人分別,然後朝他走來。「就是這袋嗎?還有其他東西要交待嗎?」
「張羚嘉⋯⋯最近還好嗎?你們相處得來嗎?」
「說起來也好笑,她以前一定對我恨之入骨,對我有偏見。誰會料到我會當上她的同房呢?放心,我們沒有打架。」以愛開玩笑說道,想起嘉現在處身何方卻欲言又止,猶豫著該否如實告知。阿寒見她有口難言,馬上焦急起來,情不自禁地大聲追問:「她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你不要騙我。」
她抿抿雙唇,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在嘉墜落時抓緊她,那就只有阿寒,非他不可。半小時後,他們來到了位於尖沙咀的一間酒吧,阿寒一眼就把嘉找出來,她醉倒在一片燈紅酒綠之中。他粗魯地趕走圍在她身邊的年輕男子,把嘉的手臂搭在自己的肩膊上,想要第一時間帶她離開這污煙瘴氣的地方。可是嘉已經醉到神智不清,猛地說她不認識阿寒,後來以愛加入幫忙,才勉強把她拖上了的士。
「她這個狀態維持了多久?」阿寒問道,他沒料到才那麼短的時間,嘉竟已判若兩人。
「就由和你鬧翻了開始。」以愛語調平平地回答,無意讓阿寒感到內疚,但阿寒心裡還是一陣抽痛。
「你怎麼不好好看著她?」他一時情急,並非真的想怪罪於以愛。
她還是處之泰然,「她是我室友,不是我女兒。」
「貝以寒啊貝以寒,」以愛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雖說我們再見亦是朋友,但我真沒想過你會因為另一個女生而找我。你說命運是不是很有趣?」
「以愛,我能拜託你一件事嗎?」以寒語氣堅定而誠懇,眼眶濕潤起來,一副快要哭出來的模樣。
//
星期四是嘉與以愛不用上課的日子,以愛竟在書桌前做功課,嘉在床上睡得東歪西倒。這個景象著實罕見,他們就似交換了靈魂,做著與自己人格不符的事情。以愛推一推嘉,她翻了身,卻沒有醒來;在嘉耳邊播放著重搖滾音樂,放了十多分鐘,她終於睡眼惺忪地坐起身。「你不要放了,我的頭很痛。」
「你這叫宿醉。」以愛遞了杯熱茶給嘉,「喝完去刷牙洗臉,我要帶你去一個地方。」像她這麼沒心沒肺的人,當然不會隨時準備解酒茶,那是阿寒打了好多通電話千叮萬囑她買給嘉的。
嘉喝了熱茶後,感覺沒有那麼頭昏腦脹,跟著以愛出門,本以為以愛是帶她吃午餐,怎料她在校園裡的心理輔導中心停下腳步來。
「我們進去吧,我都預約了。」
「林以愛,你這樣是甚麼意思,讓人看見了怎麼辦?」
「就讓你進去聊聊天,把這些年來所有的不快發洩出來。」
「我沒事!我跟你很熟嗎?你別替我作主!」嘉嘗試控制自己的情緒,可是最後的理性還是被一一擊潰,開始歇斯底里地嚷著。以愛把她帶到一個較遠的角落, 以免其他人圍觀,好讓嘉卸下心防。她看到嘉連哭帶喊,又想起了阿寒憂心忡忡的模樣,不禁心痛起來,可是嘉卻不斷推開她,想要轉身離去。
「張羚嘉!」以愛提聲叱道,雙手抓住嘉的肩膀,溫柔卻充滿力量。「我們一起進去,我先去跟他們聊天,如果他們不夠好的話,我馬上帶你走;但如果我聊得舒暢的話,你就答應我給他們一次機會,好不好?」
嘉依舊哭著,卻沒有再大吵大鬧,只像個無助的小孩在走失後慌得痛哭。以愛放輕了聲線,認真地說:「這個世界是殘忍的,沒有所謂美滿的童話,我們都有缺陷,但你已經做得很好了,沒有人能做得比你好,所以你可以讓自己呼吸了。」
「我們都在這裡,一直都在。」
嘉低頭,淚水早已爬滿她的臉,視線變得模糊不清,所有事物都化成幻影,她唯一看到自己的手腕,那幾道自殘的疤痕赫然在目。她是真的累了,她以為她已失去了所有的賭本,甚麼都輸清光了。以愛牽起嘉顫巍的手,邁步走往那包容一切棱角的收容所。
起初幾次面談,嘉都不發一言,只是靜靜地等待時間流逝。輔導員也不慌不忙,沒有逼她說話,她看起來頂多三十多歲,總是放播著藍調音樂,這次她點上香薰。
「我以前房間裡都會點香薰,味道跟你的很相似。」這是嘉說的第一句話。
「這種味道淡淡的,讓人很放鬆。你一向喜歡點香薰嗎?」
「沒有,別人替我買的,希望我不再失眠,可是我的失眠已持續了十多年。」
「那現在呢?」
嘉苦笑,「喝了酒便睡得不省人事。」
「時間到了,我們下次再談。」
後來嘉的話漸漸多起來,「你想念親生父母嗎?」
「親生父母的死,我是早就接受了,偶爾也會想起他們;但被貝阿姨收養,一直是我心裡拔不走的刺。連我的親戚都對我避之則吉,她卻花了十多年照顧我這個毫無血緣關係的人,這個責任是要抱著一輩子的。」
「所以你覺得自己欠了她,是不是?」
「是。」
「你可以簡單說一下,欠了甚麼?」
「養一個小朋友,興趣班、買書、學校活動費、雜費、衣食住行、電費、水費,哪一樣不用錢?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得清。」
「從你的角度而言,你覺得如果從來沒有你的話,阿姨的生活會更加好?」
「可能是吧,我不知道像我這樣腐爛的人,還能不能帶給別人溫暖。」
「那阿姨有抱怨過嗎?」
「最大的問題就是她從來都沒有。所以我是討厭我自己,明明是我麻煩了人家,怎麼又覺得自己受了委屈?我很矛盾,我想一巴掌打醒自己。我想不通,為甚麼我小學時不會把自己放到那麼低,可以和阿姨開開心心相處。我曾在社區中心當義工,那裡的小朋友不是寄養兒童就是被領養,我想不通為甚麼那些小朋友可以坦然面對,但我學到現在還是學不會。」
「人類的感受沒有開關,而且你應該也聽過,你不必為自己的感受而覺得抱歉,又或者覺得對不起任何人。」
「你現在還有甚麼煩惱嗎?」
「住在兒童之家、寄養在別人家庭,到了十八歲也要離開,那我今年也十八了,是不是代表我也要離開?」
「你有跟阿姨說過這些嗎?」
「沒有,從來都沒有。」
「那我們就循序漸進,不必急著當她是母親,甚至不必當她是親人。就當她是你成長路上一個很重要、你很敬重的人。你有甚麼煩惱的話,你會去找她傾訴。不嘗嘗敞開心扉的話,只會一直停滯不前。你不必預先想好該說些甚麼,找個舒服的地方,那一刻想到甚麼就說甚麼。」
「要放下執著,知易行難,尤其是當我們已念念這麼長的時間。現在你有機會解開心裡的繩結,不是所有人都這麼幸運。」
//
「喂,貝阿姨?這個星期六我想回來,你在嗎?」嘉打給阿姨,和她約好這週末回家吃飯,她知道阿寒參加交流團到台灣了,才敢回去。
她提著兩盒便利店的叮叮飯,阿姨笑逐顏開地歡迎她:「你難得回來就應該吃吃煮家飯,怎麼提議吃叮叮飯呢?」
「我就嘴饞,突然很想吃。」
吃過飯後,她們坐在沙發上休息,嘉一臉凝重地說:「阿姨,我有事想跟你說。」她眼進阿姨的眼裡,第一句說出口的話就是:「我競選學會主席落選了,結果早已內好定。」
阿姨先是一愣,沒想到嘉竟然會主動和她報憂,很快便露出體諒的微笑,安慰她道:「沒甚麼大不了,這裡不公平,不代表處處都不公。他們沒選上你,是他們的損失。」
「我其實一點也不想當甚麼銀行高層,甚至想到這界別就覺煩厭,可是我不想令你失望。」
「我很怕自己一個不小心犯了錯,就會惹你討厭、惹別人討厭,所以我一直以來營營役役。我努力讀書、努力掙錢,那是我的責任;身為班長為同學服務,那是我的責任;在家裡守著規矩,不惹麻煩,那是我的責任;我規劃好人生,確保未來可以高薪厚職,那是我的責任。我就窮得只剩下了責任。這次學會幹事人選是內定的,我最介意的不是黑箱作業,而是怕一旦我沒有了對別人的責任,我會發現自己原來甚麼都不是。」嘉沒有想像中那麼激動,好像把別人的煩惱娓娓道來。
貝阿姨搭住她的肩,好讓嘉把頭靠在自己的身上。「你就是太有責任感了,可是你也要對自己負責任,不要只令別人開心,想想做甚麼才會讓自己開心。」
她抽一抽鼻子,迷惘地說:「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想做甚麼、想走怎樣的路。」
「你們還年輕,這些年來你給我的家用我都替你儲起來了,要是大學畢業後還未找到方向,就再去讀個碩士繼續探索。」
「對不起,讓你背了我這個重擔這麼久。」
「與其說對不起,不如說謝謝。」阿姨的眼眶忽而濕潤起來,「我就想告訴你,比起你平步青雲賺大錢,我更加想你簡單快樂,活成自己喜歡的模樣。」
貝阿姨欲言又止,「還有那個⋯⋯你跟以寒⋯⋯」
「別提他了。」嘉此刻只想和阿姨珍惜當下,這個當下與貝以寒無關。
這次系上的人又聯同投資學會辦了一次雞尾酒會,嘉沒有推三推四,反而爽快答應,同學們都顯得有點驚訝。嘉穿了一件黑色小洋裝,那是貝阿姨剛給她買的,昂然踏進酒店的餐廳裡。席上的對話依舊枯燥無味,成績、旅遊、實習。「你們都找到了實習對嗎?如果有需要幫忙,儘管出聲,我一定找人幫。」一位男同學豪氣地說著,煞有介事地望向嘉。
嘉便接過話來:「是嗎?你找到了甚麼實習?」
「就我舅父的諮詢公司,本來是沒有空缺了,但我跟他說一聲的話,應該可以把同學一併帶過去。」男同學不以為然地說。
嘉依舊喝著最平價的一款酒,舉杯喝了一口,說道:「你們真應該擁有屬於自己家族的公司,你們的家人真有先見之明,我覺得自己倒是沒有這個需要。」然後掛上一抹躊躇滿志的笑容,「因為我一點也不擔心別的公司不會請我。」
只有自己才有資格說自己奇怪。她第一次覺得,世界為她放晴了,儘管現在是黑夜。
ns 15.158.61.37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