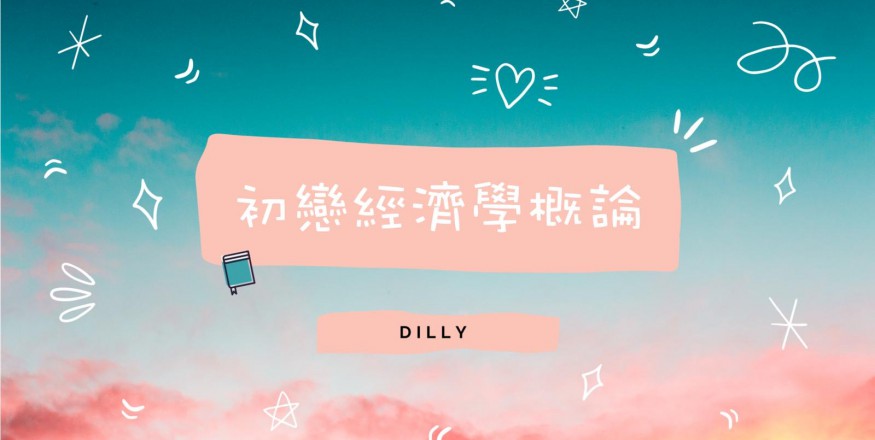鬧鐘才剛響起了一秒,嘉便從睡夢中驚醒,按熄鬧鐘,不讓它吵醒林以愛。她打開手提電腦,開始埋首準備接下來的面試。聽說這個投資學會的血統優良,過往的幹事人才濟濟,只要成為新一屆的幹事,就等同鋪展了良好的人際網絡,對實習就業都有莫大的幫助。她查清了歷年幹事的背景,被問起了也不至於啞口無言;她甚至預先擬定了當選後學會接下來的活動規劃表,作好最周全的準備。這一戰,許勝不許敗。現在能做的事,就只有竭力抓住她還剩餘的。
「張羚嘉,聽說你想競選投資學會下屆主席,是嗎?」和嘉一起上管理課的女生問道,她並非屬於嘉的學系,只是同樣讀商科,兩人偶爾會說上幾句話。
「是啊,今天晚上最後一輪面試。」
女生一副有口難言的樣子,「那個⋯⋯你不知道,他們一早選好了下屆的幹事人選嗎?」
「甚麼?」
「你們系的Jessica就是他們內定的主席呀,她和上屆一半的幹事本來就熟,更是中學的師妹,然後Jessica 也有份挑下屆的幹事,挑選親信嘛。」
一股厭倦的情緒湧上心頭,勞勞碌碌、腳踏實地,這個世界仍然不是為她這種人預備。她感激那女生告知她真相,不然她真傻呼呼跑去給人看她笑話。回到房間後,她先拿起除塵轆,黏走地上深深淺淺的頭髮;用除塵布把桌上的物品一一清潔,然後拿起抹布,把房間每一個角落都擦得光亮。地上的污漬異常頑固,她捏緊了抹布,拼了命地擦,擦得手指頭都快要破損了。
林以愛終於回來了,她抽著一大袋啤酒,臉頰緋紅。她目光沉沉地看著嘉,嘆了一口氣說道:「張羚嘉,這裡是大學宿舍,房間是我們倆的,你有份,我也有份的。你真的不用時時刻刻也在打掃,更不用好似寄人籬下般小心翼翼。想笑就笑,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想罵就罵。」
嘉聽到「寄人籬下」四字,身體馬上僵硬起來,嘴巴微微張開,疑惑地盯著林以愛。難道是貝以寒甚麼都跟她說了嗎?
以愛向來是個聰明的人,一眼就看穿了嘉的心思,緩緩地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你不要誤會,不是阿寒告訴我的,他比你想像中更加在乎你。」
那時候以愛和阿寒還在一起,他們瞞著所有人翹課去了澳門。玩到筋皮力盡,他們隨意跳進了一間酒店去,金碧輝煌的設計,精雕細琢的天花,鑲滿水晶的吊燈,他倆就在這奢華的大堂裡坐下來歇息。
「要喝飲料嗎?我過去買。」以愛點點頭,寒便從錢包拿出一張鈔票和數個零錢,握著錢就跑到大堂另一端的咖啡店去。以愛有點無聊,見寒的錢包就擱在背包中,於是便拿來隨意看看。裡面是八達通、學生證、一大堆單據,她輕輕翻了翻,發現單據後藏著一張合照。她定睛一看,相片裡的女孩是隔壁班的吧,好像叫張羚嘉。此時,一雙球鞋映入眼簾,她一抬頭,阿寒就說:「我和她是認識的,但我不能解釋,因為這事關乎她的私隱。」
她不自覺揚眉,淡淡地說:「不,沒有解釋的必要。我不清楚發生甚麼事,但說真的,我不想知道。」以愛一手把錢包還給以寒,一手接過那杯咖啡。「我們走吧。」說完就逕自朝出口走去,留下一臉錯愕的阿寒。
在阿寒聽來,她的一席話是逃避吧,以為不聞不問就可以相安無事,繼績一起。看到相片的那刻,她心裡就清楚他們只是逢場作戲,不是因為她假定寒對她不忠,而是她第一個反應是欣賞著那幀合照,想著這張相片多好看,後來才醒起裡面的男主角是她的男朋友。連半點妒忌難過也沒有,那不是放心,而是她可能從來沒上過心。Paixão 不是甚麼美好的愛戀,而是迷戀與激情。
不出她所料,他們一個多月後就分手。合則來,不合則去,這種遊戲法則會傷人嗎?兩個都玩得起的話,輸了也自然能好聚好散。只是,感性的人總比理性的多,認真的人永遠比玩遊戲的多。男女之間就是場賭博,小賭怡情,大賭傷身。誰懂得見好就收,誰不執著於損失,誰就是最大的贏家。這一次,他們和局。
她拿起開瓶器撬開啤酒的瓶蓋,骨碌骨碌地喝了一大半。「那次之後,我也沒刻意去查你們的關係,反正你們在學校也沒甚麼交流,多沉悶啊。」以愛調侃著她,「我沒有甚麼特長,最大優點就是朋友多。我在料理班認識了一個女生,談起了前男朋友,她看到了阿寒的相片,就說他們唸同一所小學。她說阿寒跟一個女生特別好,那就是你。」
「她甚至說你們住在一起,他媽收養了你,她言之鑿鑿,我猜她沒有說謊。」以愛剛剛在火車站看見了貝以寒,他招呼也不打便匆匆離去,估計是與張羚嘉不歡而散。
嘉看著滿桌的啤酒,拿起了一瓶,笨拙地打開瓶蓋,嚐了一口,苦澀從舌尖蔓延至全身。儘管如此,她還是裝模作樣地喝了一大口,想要驗證那句借酒消愁。「林以愛,你甚麼時侯喜歡上阿寒的?」
她一點也不覺得被冒犯,施施然地說:「我也不知道,中一第一次一起時感覺很兒戲,到後期才覺得他是個很好的玩伴。」
「我比你們每一個人都更加早喜歡他,為甚麼我們要在一起就困難重重?」她又喝了一口啤酒,才有勇氣繼續說下去。「喜歡阿寒就像玩命。你有聽過俄羅斯輪盤賭嗎?在左輪手槍的六個彈槽放入子彈,隨意轉動轉輪。參加者一個一個拿槍對準自己的頭,扣動扳機。呯,你林以愛中槍了,馮奕姿膽怯黯然離開了。我拿著那把手槍,以為我能堅持取得最後勝利,扣動扳機,最後還是爆出腦漿,或許這場遊戲只有阿寒能贏。他今天質問我的樣子,好像覺得我從來沒有爭取過他、為他而努力過。他和你一起時,一句『你在學校假裝不認識我吧』向我擲來,我沒有問過半句,安安靜靜地自己為他付出;他在男童院時,我在門外徘徊不敢進去,替他擔驚受怕;他一出來就跟你復合時,我只有自己生悶氣,逼自己接受他根本不會給我機會的事實;他把我們的距離拉得很近很近,轉過頭又跟馮奕姿走在一起,我有半句怨言嗎?我有放棄過他嗎?他憑甚麼把一切說成是我自私讓他等我?」
以愛像教育孩子一樣勸說:「張羚嘉,你太善良了。」
「阿寒說過,我的善良是迫出來的,不是發自真心。」
「太善良就會讓人覺得虛偽,因為一般人就會覺得哪有可能有如此善良的人,所以一定是裝出來的。」以愛突然笑起來,「我覺得你很像灰姑娘。」
「甚麼?」嘉以為以愛也開始有醉意,牛頭不對馬嘴。「哪裡像?」
「和她一樣笨。明明那間房子應該是自己的,明明那繼母得寸進尺,肆意橫行,她還說甚麼要善良要善良。我是她的話,一早就拿玻璃鞋把那些醜惡的人打到頭破血流。」
「這大概是我喝醉酒這概也做不出來的事。」嘉苦笑,摸摸額頭。更何況在她的生活,根本沒有甚麼壞到不行的大反派。
「一瓶解決不了的問題,就喝兩瓶。」以愛理所當然的說,轉頭看看嘉已經醉醺醺了,眼神迷朦,「也是,喝一瓶就已經這模樣,喝兩瓶還得了。」
以愛看著灰白的天花板,若有所思。「你太不會喝,我就喝太多了,如果可以合起來除二,可能我們就不用在這裡喝悶酒了。」
「這樣去反抗真的有用嗎?」
「既然你其他方法都用盡了,那換個方法有何不可。」以愛豪氣地把酒舉去來喝,然後又眨眨眼說:「不過不要打死人喔。」
「張羚嘉啊,可能你都不太認識級上的人,但我們偶爾也會提起你,你都不知道我身邊的朋友多麼崇拜你,說你才華洋溢,卻又懂得收斂鋒芒。我不否認,但我覺得像你這樣能發光發熱的人,實在不應該活得這樣卑微。」
嘉忽而覺得身體酥軟下來,眼前的事物模糊起來,這一切有如南柯一夢。她想起了阿寒,想起了他轉身就走的背影,淚就如缺堤般湧出。以愛沒有感到驚訝,喝了酒的人本來就特別容易傷感。
「我和阿寒是不是永遠不會見面了?」嘉哽咽著問。或許由始至終,比起愛情,她更渴求自由和解脫。
以愛繼績凝視著天花板,幽幽地回答:「不會的,沒有甚麼是永遠的。」
ns 15.158.61.54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