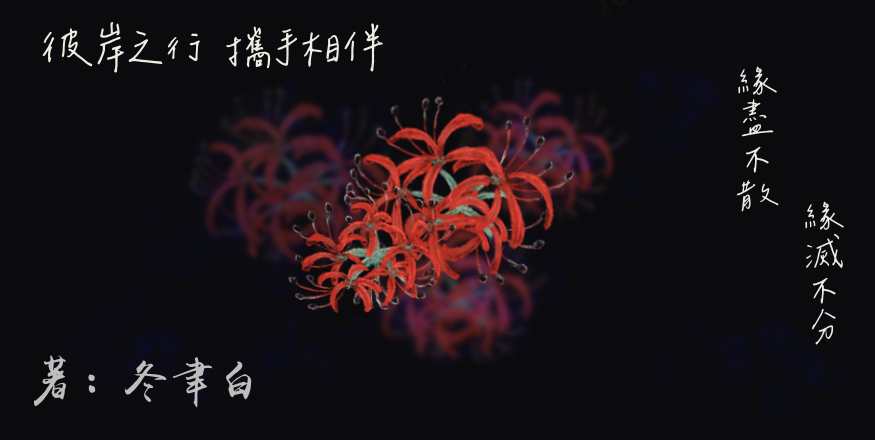自容宴出現後,人魔也終於被徹底釋放。近期人魔殺人、食人的事件頻繁增加,縱是沒有靈力的凡人也感受到不對,社會動盪不安,如今人心惶惶、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陡增,對立與衝突也成了家常便飯。
政府為解決此事,主動請術法界協助介入處理,而作為術法世家中的大拿,席家當仁不讓地成為其中之一,與其他幾個深耕術法界多年的大世家一同討論如何解決人魔之事。
今日便是他們相約商議之日,大家聚集在對人魔早有關注的席家議事堂內。然而在人們熙熙攘攘地走動時,不喜人煙也不好出現在眾人面前的彼岸,便只能待在房內不得踏出半步。
失去引渡者之力,他本也沒地方可去,但這幾日過於安份地待在席家足不出戶,依舊讓顧行雲等人很是詫異。
彼岸似乎很明白自己的處境,盡可能地減少了存在感與麻煩他人的機會,若不是顧行雲與席破軍會來找他,席家上下幾乎都要忘記有這位座上賓了。
對彼岸而言,寄人籬下他十分熟悉,無須旁人多提點,也知道該如何做個好客人,只是總有兩個人不想讓他過清閒的日子,每日總愛輪番來吵鬧,令他不堪其擾。
「彼岸,今日跟我出門一趟吧。」席破軍照舊敲響他的房門,但不等他應聲便自己推門進來。
自他不再是引渡者後,席破軍對他少了層敬畏,多了點同齡人的親近,因此連稱呼都變得熟稔起來。
彼岸這時正在悉心照料窗台前的小綠植,聞言僅瞥席破軍一眼,毫不留情地拒絕:「不去。」
「為什麼不?」經過這幾日相處,席破軍很習慣他的拒絕,反正軟磨硬泡後還是會答應。拒絕不了他人不算過分的請求,這大概是引渡者的職業病?
「今日不適合出門。」彼岸指的是議事堂那群吵雜的人群。同為有靈力之人,只需一眼便能察覺他的異狀,這會造成席家多少麻煩,他清楚得很。
席破軍自然也知道他在擔心什麼,拍拍他的肩,又在彼岸皺眉前迅速移開,與他那舅舅欠揍的模樣學得十成十像。
「我是要帶你去母親的墓地。初次見面時畢竟冒犯你了,現在想來,你那時大約只想拜一拜母親,沒想到我反應激烈。」
「沒事。」彼岸澆完最後一盆綠植,將雙手洗淨,毛巾擦乾,才肯鬆口:「走吧。」
席破軍就知道他一定會答應,毫不意外地領路在前。
去往席家後山的路不需經過議事堂,但或許是席破軍上次強烈的敵意讓彼岸感受到了排斥,來席家暫住的這些日子,席家什麼地方都被顧行雲帶著去過了,就是不曾再踏入後山半步。
彼岸跟著席破軍抄近路,不一會兒就來到後山荷花池邊。現在正值夏季,一大片荷花綻開於水面,水面倒映著藍天白雲,微風輕拂時泛起漣漪,還能聞見些許荷花香氣,身處其中彷彿與天地合一般,遠離世俗塵囂、清淨自在。
彼岸本較為嚴肅地神情,也因這療癒之地而稍稍放鬆。他自第一眼見到墓碑,便知道墓中之人深受席家愛戴,這後山荷花池能如此美麗清新,想必是受人精心呵護。
「母親,我來看您了!」席破軍來到後山第一件事,必定是先向母親問安,掃除墓旁雜草,外加整理周邊環境。雖然他每日都來,這裡根本沒有機會變得髒亂。
「席知夏……」彼岸輕聲唸著墓上刻印的名字,見席破軍跪地而拜,便也隨他一同祭拜舊人。儘管他才是真正作古之人。
「我母親最喜歡荷花,如果你以後想來看她,帶荷花就好,或者也可以不帶,就是別帶些庸俗之物打擾母親清幽。」席破軍閉著眼,雙手合十,神態虔誠,嘴裡吐出的話卻十分犀利。
彼岸嗯了一聲,聽是聽進去了,但他不知道還能不能再有下次。
躲在席家只是暫時之計,若不是他手上握有不聿,大概無人會想將他這個燙手山芋留在身邊。容宴既然知道不聿在他手上,那等容宴查出他身在何處時,便是他應該離去之日。
席家好心借他一時庇護,可不能讓席家因此成為目標被襲擊。顧行雲說席家有他在不必擔心,但再強大的國家都能頃刻滅亡,席家不過是一方地主,怎能與心狠手辣,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容宴相比?
倘若席家人能親眼所見幾百年前那些人是怎麼死的,想必他即刻就會被驅逐吧。史書終究只是文字,文字寫得再多麼驚心動魄,都比不上親眼瞧見來得震撼,更別說容宴不知將史書內容改寫多少,或許後世的歷史根本沒記載這些事。
席破軍做完每日必做功課,回到墓前便見到彼岸還在望著墓碑發呆,不禁覺得好笑:「你在想啥呢,又沒貼照片在墓碑上,總不能是一見鍾情吧。」
彼岸回神,為掩飾尷尬趕緊找了其他話題。「你有她的照片?能見見嗎?」
只要聊到席知夏,席破軍總是顯得很高興。這是彼岸在席家待不久,也能觀察出的小細節。
「我身上就有,隨身帶著呢!」席破軍果然笑容滿面地從懷中小心翼翼地取出照片,儘管被隨身攜帶也一絲摺痕都沒有。
照片上的女人眉目清秀,笑得溫柔動人,淺綠的洋裝襯得雪白的肌膚更加明亮,淡綠的瞳孔中有無盡深意,彷彿有無限話語述說。雖稱不上絕世美女,但也算一方佳人。
一般人見到,即使客套也會連連稱讚,然而彼岸卻瞪大雙眼,驚得差點拿不穩照片。
「你小心點!」席破軍見狀,趕緊搶回照片。
「……這是你母親?這是席知夏?」彼岸忍不住往照片上的女人多看幾眼。太過熟悉的容貌令他晃眼,昔日記憶再次爬上心頭,即便他努力不去想,也總逃不過所謂「故人」的糾纏。
有時他也會想,他在這之中究竟做錯了什麼?
可即便他認為沒有哪一件事是錯的,結局依然不盡人意,即使不是他所樂見,卻也與他息息相關。他確實無話可說、無法辯駁。
「這當然是我母親,你為什麼質疑?」席破軍不知怎地有些生氣,肉眼可見臉色差了不少。
然而,彼岸此時已無暇再去顧及他的臉色,腦中充滿了「席知夏」的身影,那總愛跟在師父身邊的女教徒,是他一生的摯友,也是唯一一個直到最後依然相信他的人。
那時她不是席知夏,而是「顧茗荷」。
等等……顧?
彼岸覺得頭痛欲裂。他從未思考過「顧」姓出現在身邊的概率,這是師父賜給顧茗荷的姓氏,他從未質疑過姓「風」的師父,為何會突如其來地給了「顧」姓。
他太過信任師父,師父所說所做的每一件事,他會毫不猶豫地信任。
他一直不願去想顧行雲與他師父的關聯,可當有一條明晃晃地線索擺在面前時,他還能不去思索其中涵義嗎?
他能以此斷定,顧行雲與他的師父是同一人嗎?
「原來你們在這。」
遠處傳來一聲輕笑,兩人一看,是顧行雲不疾不徐地從低處走來,離荷花池約有幾百公尺的路,可顧行雲幾乎沒怎麼動腳,人已至他們面前。
顧行雲懶得用腿爬這一段山坡的路,因此每走一步就用風推一把,每一步都像往前瞬移了一大段,前進速度飛快。
彼岸此前未曾注意,但此時他卻因為這一點習慣而微微顫抖。這習慣與師父一模一樣,他當時還羨慕好久師父能驅動風力。如今,他卻一個字也說不出,僅是凝望顧行雲許久,想從他身上找出其他與師父相仿的部分。
「怎地看我看傻了?難不成現在才察覺我帥氣逼人?」顧行雲再度揚起那十二萬分欠打的笑,然而這次卻沒等來彼岸的嘲弄,令他有些疑惑。
彼岸無視他這句話,只不停想著,究竟怎麼做到人明明未死,卻又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
他確信若師父僅是換著外觀出現在自己面前,他也斷不可能認錯,唯一的可能性只有師父受了重創,甚至忘記了他的存在。但此推論仍有疑點,師父終究是個人,有辦法活幾百年嗎?
等彼岸再度回神時,席破軍似乎已經將他剛才的怪異行為告訴顧行雲了。只見顧行雲朝他一笑,手上揮著席知夏的照片。
「這也是你故人?」
彼岸輕輕點頭,小聲說:「幾乎一模一樣。你相信嗎?」
這聽起來像在半路認親,彼岸很認真地思考該不該說清楚,他不是為了想一直待在席家才這樣說。
沒想到顧行雲竟也認同:「相信。她從來就不是塵世能束縛住的存在,若不是她於席家有一份責任心,想必會雲遊四海再也不歸家吧。」
彼岸愣了一下,顧行雲說的與他記憶中的顧茗荷性格十分相似,果然是同一人。他望著席破軍吵著讓顧行雲多說點,而顧行雲嫌煩地神態,不禁心想著:你也是我的故人。
ns13.58.93.211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