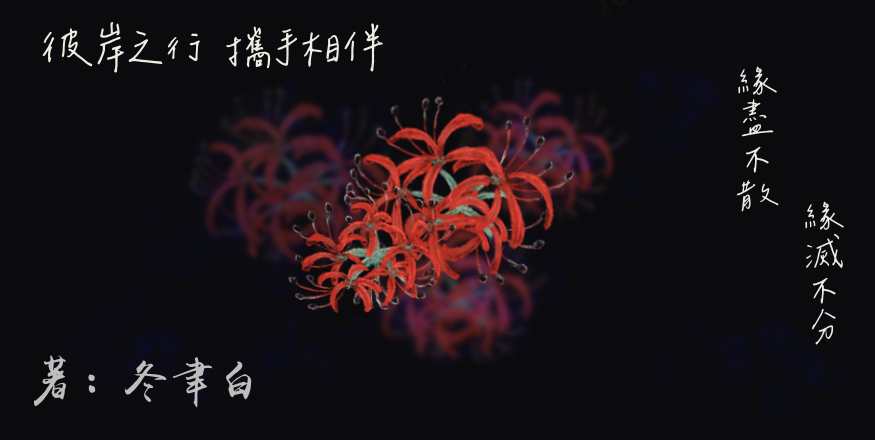![]() x
x
No Plagiarism!n3i1CbHs5sfPL5wkW5ksposted on PENANA 商議幾日後終於定了案,所有參與其中的術法大家們兵分幾路包圍吾山,主動出擊直搗魔窟,不讓容宴有反應的機會。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zu87GR6giu 維尼
席家作為其中一支主力軍,自然得扛起壓力走較危險的路,席從命本想讓目前無戰力的彼岸留在席家,顧行雲卻不同意。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GeLNNDjghd 維尼
「要是容宴趁機找到席家呢?他還有個能勘破虛妄的女祭司存在,指不定早把我們這次行動給摸透了。」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F7QVQMJNya 維尼
席從命卻不認同:「他現在連身體都是凡人,根本受不得一點衝擊,這是場硬戰,你如何在戰鬥中分神保護他?」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Bl7HcexDJ9 維尼
「如果連我都不能,你認為還有誰能?」顧行雲瞥了站在左後側的彼岸一眼,見他低垂著眼,也不知道有沒有在聽。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KtBc7kRtf1 維尼
席從命氣笑了,比實力自然是贏不過,但不能讓顧行雲僅以這點反駁自己。誰知道去到吾山會遇見什麼?比起世間紛亂,他更關注席家人是否安然無恙,危難關頭即使做戰場逃兵,他也希望席家人能全數回到家。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6il4McEAC7 維尼
「不然讓他自己決定。」席從命犀利地眼神轉向彼岸身上,無形中對彼岸施放壓力,要他識相點自己說留下來。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3eNxvmez89 維尼
顧行雲察覺這點,以身擋住席從命的目光,轉身面對彼岸,用再信任不過的語氣問:「你當然會跟我一起去的吧?就像之前一起合作那樣。」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ZZpKlzmf3A 維尼
彼岸望著他那雙與風玄默極為相似地金色眼眸,低聲說:「但我現在沒有力量了。」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h1szoz8MUy 維尼
「這有什麼?」顧行雲完全不以為意,目前還沒遇到能傷他的敵手,或許未來也不一定會出現。「我會保護你的。」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jKFnQJrfmp 維尼
我會保護你的。這是多麼相似的一句話。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KMDzBrXFQK 維尼
彼岸心一動,原本虛握的手緊了緊。以前他從未拒絕過師父半次,如今也是一樣。他想跟師父一直待在一起,即使師父根本不記得他,即使他力量盡失,再無辦法可尋。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5Mt4KNkkGO 維尼
「……好,我去。」他輕聲答應。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Zea8NetWV3 維尼
席從命不可置信地瞪著他,這幾日安安份份的客人竟在緊要關頭刷存在感,不禁怒道:「你去會害死他的!」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7WkO6jVfWq 維尼
彼岸頓了下,本就需調養的臉色顯得更加蒼白。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Ou42ZG7zqn 維尼
顧行雲不滿地反駁:「我不會出事。如果我會出事,那席家軍也一樣可能全軍覆沒,到時候誰也說不了誰。」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pujP3anFQe 維尼
席從命怒意更甚,一把揪住他的領口:「你的口無遮攔要到什麼程度?他究竟是你的誰,讓你拼死要幫他?」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qFEaBfGaQJ 維尼
這問題顧行雲答不上來。他跟彼岸什麼關係都不是,為何要這麼執著?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mLgU4bArZz 維尼
「抱歉。」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eHw4k0cBXI 維尼
聽他道歉,席從命臉色緩和許多,嘆道:「既然知道錯,就不要帶他……」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Sy28FXicLu 維尼
「我道歉是為口無遮攔一事,不是為了帶他去這事,我還是要帶他去。」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S4wDFBjIoc 維尼
席從命臉色立刻就黑了,正想著不如打一架,反正顧行雲不會對他下死手,把顧行雲打到出不了門、參不了戰,也總比讓他出外亂來好。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BVgK8gyzvo 維尼
「行了,都安靜點。」拄拐聲從議事堂入口傳來,正是昔日的席家掌權人席常在,如今已成了白髮蒼蒼的老人,慈眉善目地朝幾位年輕人瞧了瞧,又對彼岸笑了笑。「這幾日身體不太舒服,沒有歡迎遠方來的客人,有失禮節了。」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7mLuZ0RVss 維尼
「爺爺,您唸唸他!」席從命一見到靠山,立即打小報告:「他硬要在去危險地方的時候,帶一個需要分神保護,還手無縛雞之力的人!」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VWBgS3FsnT 維尼
席常在卻沒如預想的幫他,僅是望著彼岸好一會,便對席從命說:「從命,時候到了。」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F0YQzYZHOM 維尼
席從命原本忿忿不平的神情頓時呈現出怪異,目光在彼岸與顧行雲之間徘徊幾次,而後才喃喃道:「原來是因為這樣?我還覺得奇怪……」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cfJ25FEPWC 維尼
顧行雲發現自己跟不上這段對話,不禁蹙眉問席常在:「師父,您說什麼?我怎麼聽不懂?」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q7vVeW8wP5 維尼
席常在搖頭笑道:「告訴你的時候未到。反正我准許你帶客人一同前往了,這事從命不得有異議。」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irrVJwSZw9 維尼
席從命咬咬牙,儘管內心不滿,但他不會違抗席常在的意思,更別說席常在早就告訴過他們等「時候到」時,誰都不能阻止顧行雲做決定。這也是他們從小不特意規定顧行雲做任何事的原因,也才會養成顧行雲這樣無拘無束、口無遮攔的性格。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nSgkBlDc2w 維尼
席從命壓下心中不安,揮手下令道:「準備好,明日出發。」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uQGQC84Sij 維尼
12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Mah2eAZcHq
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bGSacXAAft 維尼
*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UnIyalTdZp 維尼
12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Fam1Za0iXi
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TyorK5Rllk 維尼
為了掩蓋彼岸的行蹤,席從命只好讓顧行雲帶著彼岸另外走,自己則和幾世家聚成的大隊一起行動,免得令人生疑。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41z3uL88z1 維尼
雖然顧行雲那邊人少,只帶了幾位席家小徒,但走的路也較無危險,席從命左思右想後,還是把席破軍扔給顧行雲了。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7KC5Dq57Ts 維尼
一樣的配置前往吾山,只是這次少了程育,然而一想到程育的女友,被容宴推出當擋箭牌正好死在彼岸刀下,這也正是彼岸失去力量的主因,幾人又更加沉默了。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htTvO0oPpD 維尼
身後的幾位小徒們倒是沒他們這麼消沉,活躍地交談接耳,只把這次行動當作一次歷練。有顧行雲在,他們一點也不害怕。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DHV2ReULue 維尼
有個因崇拜顧行雲而學著扎馬尾的年輕徒弟名喚大峻,興奮地說著:「這次要是遇到危險,就能看大師兄展露身手了!」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VQugeYae5q 維尼
另一名臉上帶妝的女徒弟不屑地嘲弄:「到時候你也看不到,因為你肯定第一個逃走。」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u4i9ecw8Li 維尼
其餘幾名小徒聽了哈哈大笑起來,甚至一同應和:「就是,平時練習你連曉曉都打不過,就別指望能派上用場了吧!」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dk9PKO2y30 維尼
大峻漲紅了臉,氣得想罵人,偏偏一個人又說不過大家,況且還被偶像顧行雲聽見,正懊惱到快哭時,前方那看起來十分體弱的少年突然說話了。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zAgTZSEJic 維尼
「逃走並不丟臉,能活著也挺好的。」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iE4QxmMzO5 維尼
幾位小徒見尊貴的客人都發話了,自是不敢在背後說三道四,朝大峻扮了個鬼臉就紛紛閉上嘴。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c7P6F50uYr 維尼
大峻熱淚盈眶地看著彼岸的背影,心想偶像不僅厲害,就連偶像的客人也很通情達理,不會無故嘲笑他。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fQcKkNo0dB 維尼
他們道行尚淺,看不出彼岸不是常人,可彼岸身邊兩人都知根知底,聽見他這句話更是百感交集,一時也不知說什麼好。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PaFb24RZ9e 維尼
不過彼岸並沒有他們這麼多感觸,只是真心認為逃走並不可恥,這代表還有想活下去的動力,有動力生活才能繼續前進,這是好事。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mzpC1RvpTf 維尼
他們繞的是遠路,因此走了一天山路才到半程,傍晚只能在樹林裡扎營過夜。徒弟們分工迅速,一些人撿木柴、另些人生火做飯、還有幾人原地搭營,很快就把工作搞定。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Is8rGQfPFe 維尼
「都回來了嗎?我算下人數。」席破軍很自覺地擔任與徒弟們溝通的人,數了數發現人數不對,只好再數一次。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Rl5uk6mfDU 維尼
一行人不算上他們三位應有十位徒弟們跟著,可無論再數幾次,人數還是不對,少了一人。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wB0RM01ctE 維尼
「少了誰?」席破軍有些緊張,心臟開始撲通撲通跳得飛快,或許這是即將出事的徵兆。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murGmawnAF 維尼
「我看見了……」大峻忽然開口:「我看見曉曉被一個怪物給襲擊,我不敢上前,因為怕被發現就自己回來了……」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dfn6jkZIaJ 維尼
席破軍一看,這不是早上剛被說肯定會逃跑的徒弟嗎?果真逃跑了!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bSlDiGAugt 維尼
「你為什麼不早說?她什麼時候被襲擊的?!」席破軍語氣不佳地質問。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KBDgYmE0Tl 維尼
大峻像是被嚇到了,小聲地說:「我怕你們笑才不敢講,但她應該已經沒救了。」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Dv0sM36eEL 維尼
在場徒弟們的目光皆帶著譴責,不理解他膽小怕事就算了,竟連事情輕重都分不清,白白害曉曉失去被救援的機會。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AVtUFiYOxm 維尼
「我不是故意的……」大峻也知道自己錯了,頭低得更低,一點也沒敢抬頭迎接那些指責的目光。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30O9loTwEU 維尼
坐在帳篷前的顧行雲將烤好的肉串遞給彼岸,自己站起身,迎上眾人敬畏的目光,神態卻怡然自得,看不出一絲慍怒或緊張。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WDZSwSa1Hs 維尼
「大峻,你頭抬起來,我看看。」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EYqEbKiJxx 維尼
大峻搖頭,頭仍是低著。「我錯了,我知道錯了,不要懲罰我。」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Js2GXUphyg 維尼
顧行雲卻依舊堅持:「你先抬頭。」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GqHrJ3lrqy 維尼
大峻依然不停搖頭。越搖越大力,越搖越快速。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ZWDHrkr0VU 維尼
這下徒弟們也終於感覺到異樣,紛紛害怕地退後,退到席破軍與顧行雲身後去。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xz1IDoiaON 維尼
大峻不停說著「我錯了,別罰我」,可嘴裡卻發出女人尖銳地笑聲,令在場眾人倒抽一口氣。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4tafxQ9dsG 維尼
「大師兄,這是怎麼回事?」那帶妝的女徒弟嚇得花容失色,驚慌失措地詢問。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dS6HmvutAy 維尼
「他被控制了,應是有特殊能力的人魔做的。曉曉是否遇害不清楚,但大概率跟大峻一樣下場。」顧行雲一邊解答,一邊拿出御風巽,毫不留情地揮出金風,瞬息便斬斷牽引著大峻的絲線。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A3nAuTEfc1 維尼
聯繫沒了,大峻自然應聲倒下。幾個膽大的上前去看,只見大峻面色死白,脖頸處有一條被勒死的痕跡,早已不是常人神態。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dLXuouf8Eg 維尼
「他死了!」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NImCOJp6Jl 維尼
有些徒弟們抱著只是來這進行歷練的心態,並沒想過危險會主動上門,更沒想到會來得無聲無息,他們甚至沒能察覺大峻的異常、沒能感知危機近在咫尺,還傻呼呼地與被控制的死者待在一起!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tSxqPfPcGI 維尼
最終,這盤散沙亂成一團,說要回家的、說要退出席家的都有,願意留下的僅剩少數兩人。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doDLrEbp1a 維尼
顧行雲看著這情形不禁額角青筋浮現,席從命不讓彼岸跟著他,倒是讓一群空有靈力卻無用武之地的人跟來,簡直可笑至極。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pgD7eg1xRs 維尼
「你們兩個,想走也能走。」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LEZOXtGNAb 維尼
顧行雲扔下這句話,本想回到營地前,卻本能地感受到不對,猛地一回頭,卻見留下的兩人頭上也有銀線閃過!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v36Cxxv8GU 維尼
「御風巽!」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xBudliO4Cq 維尼
他立即召出金扇,故技重施將那操控屍體的銀線斬斷,卻未料那銀線像蠕蟲般爬了滿地,待一找到屍體便又能重新連接、再次操控。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xPJCXEYT7G 維尼
僅以風無法揪出幕後兇手,顧行雲回頭喊:「破軍,用雷!」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YvQyqTdE56 維尼
「好!」席破軍興高采烈地召出武器「破軍星」。雙刺刀以玉製成、質地溫潤,可上面覆滿的雷電卻不好惹。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ERKzr8srVy 維尼
席破軍難得有機會表演,立即開大絕。頃刻間,天地變色,一聲驚雷順著絲線一路攀爬而去,沒過多久,他們便聽見前方樹林隱蔽處有一聲慘叫。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ARBYeykprv 維尼
顧行雲哼笑一聲,「看來是捉到了。」8964 copyright protection124PENANAINUSiaWoI6 維尼
3.140.250.157
ns3.140.250.157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