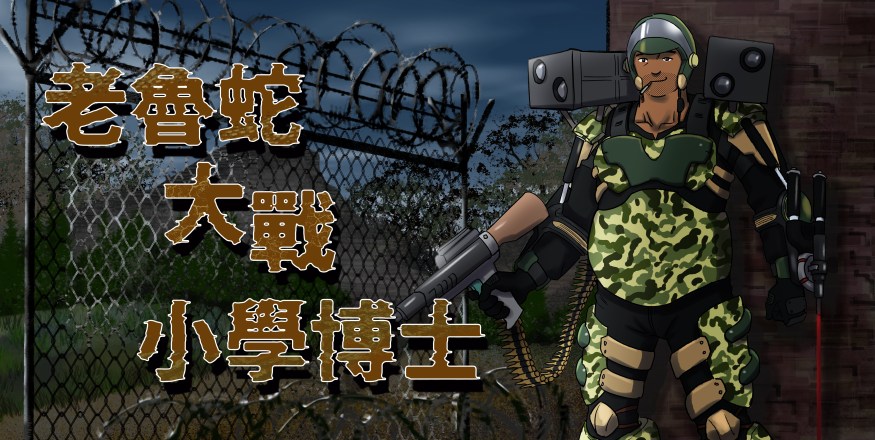5-2
我望向阿豪:「這……這能辦到嗎?」
「你等著看。」他補充,「中國人愛打雞血,能忽悠,重視精神戰力,還真的能轉換成實際利益。」
隨受困機身救出只見裝甲車旁的空降兵越聚越多,多到了旁邊有人插不上手幫忙推一把的程度。人群裡發號司令的軍官見了,指了指一旁「看戲」的空降兵,又指向裝甲車的另一端。那看戲的士兵稍有猶豫,就遭軍官一通大罵,只好小跑步跑到裝甲車底盤那頭。
「這……裝甲車輕的也有一二十噸,翻過來的重量一個人撐不住吧?」
「你等著看。」阿豪一副見怪不怪,成竹在胸的樣子。
共軍跟國軍果然「師承黃埔」,用起力來,都是「一二、殺……一二、殺……」地叫。估計這支空降部隊人人都接受過病毒強化體能,側翻的裝甲車沒幾下就被共軍推得左右搖擺。他們用口號協調著節奏,趁著一次擺蕩,共軍拖長了「殺」聲,裝甲車終於擺過了重心的極限,往底盤那頭壓了過去。
你知道的,那頭只有一人。
頂著底盤的那人失聲大吼,腳上倒退的速度卻跟不上裝甲車底盤的重壓翻傾。他像被拖鞋拍到地面上的蟑螂,壓在了裝甲車輪之間。那小兵胸腔被碾進了輪子,全身只剩脖子亂轉傳達出他的痛苦,一聲嚎叫也發不出口了。幾個小兵轉過裝甲車,拍拍他的肩,就爬上了裝甲車車身。鑽進車子,發動了引擎。
共軍的第一輛陸軍重裝備,轟轟地噴出第一道濃烈黑煙,正式在臺灣的土地上前進。
那個被自己人碾死的小兵,他的同袍們還是看在眼裡的。他們蹲下來搜刮他的彈匣、手榴彈等物。來的晚的小兵甚至翻來覆去搜查他的屍身,最後找到他的水壺,拎起來左右搖晃,扭開壺蓋喝得一滴不剩。
阿豪說:「看吧,這就是精神戰力。那小兵站到裝甲車底盤一邊,是要當落地的緩衝肉墊。只有那小兵以為自己能扛住裝甲車壓下來的重量,這肉墊才能發揮作用。」
我渾身閃過一陣冷颼颼的涼意:「嗯,你們習主席說過,『社會主義是要拿命換的』。」
阿豪似乎發現我的口氣不對,說:「跟中國當局打交道就這麼回事,你跑得夠快,熊就吃別人,你就暫時安全了。」
「是啊,鐮刀割韭菜,總會越割越低的,總有一款鐵拳適合你。」
「懶得理你。」
共軍奇蹟似地重整了旗鼓,他們甚至裝了彈,抬高自走迫擊砲的砲管,在飛機殘骸的掩護下瞄向了後撤到跑道另一頭的悍馬車。
阿豪回過頭對我說:「亦凡,你帶著同志們走吧。」他在共軍繳獲航警的槍堆裡撿回他的克拉克手槍,檢查一下彈匣,再插到自己的後褲腰。又說,「撿把槍,在戰時很有用。」
我有點感動。阿豪不論何時,不論我怎麼批評他、不諒解他,他都像個哥哥般替我著想。
我向他伸出右手,「好,人各有志,如果我們活著的話,保持聯繫。」
他也伸出能動的左手,「嗯,了解。我活著的時候,看到好康的會通知你,死前也第一個通知你,跟你說哪裡有雷。」
我握住他左手,「好,就這麼說定了。」
我剛鬆開阿豪的手,噠噠震天的直昇機螺旋槳噪聲很快地由小轉大,到了人人無法忽視的地步。我們面面相覷,不用彼此提醒就一起蹲低了身子。那巨大的噪響從塔台後方傳來。不知何時,再外看101已經完全熄燈——不對,應該說臺北已陷入一片漆黑。
共軍突襲松山機場的消息想必傳遍全臺,是當局進行了燈火管制。我瞇著眼朝噪聲處望去,只見到直昇機點點的定位燈。直昇機的朦朧黑影只比復興北路上的大樓高些,忽然「咻咻」聲響,在燈火管制的夜空中,兩道耀眼之極的火線,朝共軍集結的飛機殘骸處飛去。
火線終點,正是發動成功的裝甲車。車旁的共軍或跳躍,或臥倒,我卻看傻了眼,忘了完全藏身掩體之後。火線觸碰到裝甲車和自走迫擊砲,就像捅破蜂巢一般爆出了火球。兩部車爆炸的震波把我震坐到地上,我頓時失去了聽覺。身後震波打到了塔台與機場建築,回聲再臨。我轉過頭,直昇機兩側已噴出金黃熱燄,一拐頭撤離了戰場。
阿豪蹲在警車構成的掩體之後,一把將嚇呆的我揪到他旁邊。他搖著我,催我恢復過來,又將手槍塞到我手裡。我依稀看見他對我大喊,但耳裡嗡嗡亂鳴,什麼也聽不見,我問:「什麼?再大聲一點?」
連自己的聲音也遠得像隔著大樓的玻璃帷幕。
阿豪用力指指跑道盡頭的牆,那裡不知何時已翻進了一大群人。他們走路的姿態很是奇怪,像踩了溜冰鞋,步子邁得大大的,前進飛快,上半身卻壓得很低。我還沒看清他們的身影,一聲「臥倒!」指令過後,那群人便悉數趴了下來。
「射擊!」
那群人朝飛彈襲擊過後,破碎得不能再碎的飛機和裝甲車集火。火星點點,槍響砰砰,漸漸治好了我的暫時失聰。由槍口火光推測,攻堅的國軍約有二十人。他們停火後,一半的人更換步槍彈匣,一半人待命。
跑道兩頭再度陷入了沉默,一根紫紅信號彈劃出弧度,落到了飛機殘骸上。搖曳光影下,殘骸前後空無一人。
「躍進前進!」軍令過後,部隊得令起身。忽然間火光槍聲閃過,部隊中一人「唉呦」痛呼出聲,隨即摔倒在地。其他人緊急臥倒,對敵人開火處集火。豈料,這是共軍的聲東擊西之計,幾道朦朧人影趕在開槍前躍起,像武俠片裡的高手,飛起兩米,往我們藏身的掩體彈跳過來。
ns 15.158.61.18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