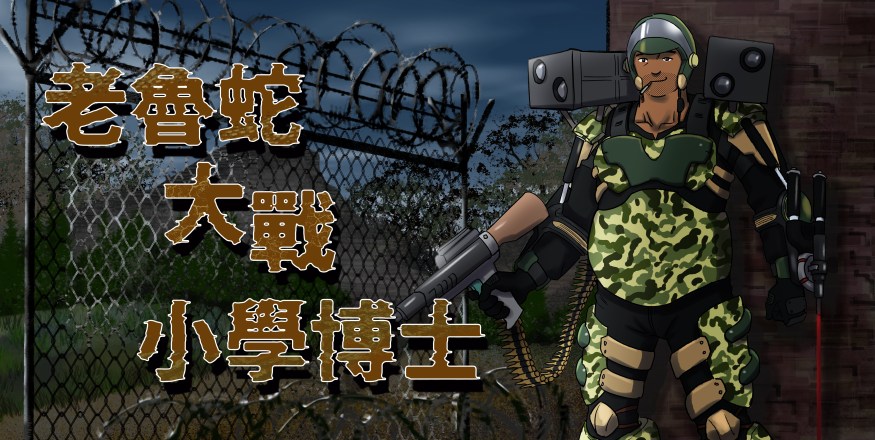4-7
我們決定去機場公務門附近埋伏,等待空廚的卡車靠近,就整車劫走。在埋伏的同時,阿豪忙著在黨裡尋找是否有松山機場工作的成員。我們苦等了三個小時,等得天都黑了,還等不到一輛空廚送來的卡車。住松機附近的黨員層層傳遞過來的消息稱,所有國際航線的座位都被跑路的人一掃而空,幾家航空公司都取消了飛機餐的服務,來縮小機艙勤務人員數量,也就是空姐的出勤。
航空公司也心知肚明,現在飛國外的就是要跑路。只要能正常飛離臺灣,安全落地,且當局同意入境就行,其他的服務,旅客都不在意。
回頭看看我們自己。累了一天,擔驚受怕的,黨員們都沒好好吃一頓。阿豪跟我分頭清點人數,其實五分之一的黨員已悄悄脫隊了。現在還留下的人,都十分清楚。一旦落單,就要自己擔驚受怕地四處流竄。販運贓物的勾當就不可能了,沒人接應,遇到黑吃黑提早送命。就連隱姓埋名躲到村鎮,也要遇到那些死忠的老人對我們情緒勒索,收了錢還要打電話告發你逃兵。
組織起來團結對外,才是亂世苟活的唯一活路。
群眾們的目光再度匯聚到阿豪身上。
阿豪說:「靠搶劫空廚餐車雖然比較容易得手,但幹這一票之後,我們也被盯上了,下一次要做一樣的事,就容易遇到抵抗。而且吼,像野狗那樣搶食物,又能撐幾天?如果大家有種幹的話,我倒有最後一個點子。」
達文西喊:「哥,我今天沒吃東西,餓得前胸貼後背了。除了殺人吃人肉外,什麼我都願意做。」其他人紛紛附和。
我對達文西打了一個抱歉的手勢。達文西完全是聽我的話來小坪頂幫忙的,還幫忙打開不少保險櫃,大伙逍遙快活每天開趴,他有一半功勞。
阿豪看了看黨員們沒有反對的聲音,才又說:「我們就算搶,也要搶那些平時有錢炒房,雙重國籍隨時跑路的吸血鬼、寄生蟲對吧?」
「對!」
「那我們旁邊就有一堆這種寄生蟲,為什麼不去搶他們的?」
「在哪?」「我熱身好了?」「劫財還是劫色?」
大家笑了起來。
「不要笑,」阿豪表情嚴肅,指了指身後,「在機場裡面。」
住松機附近的黨員表態自己不幫忙,但拗不過我們的請求,還是跟他叔叔要了進口車展售中心的鑰匙,開了後門,讓我們去搜刮所有需要的工具。
我們在展售中心裡找到了一把三米合梯跟一條棉被。等我們把梯子搬到「飛機巷」牆外時,已是晚上10點半了。機場跑道牆外緊鄰居民住宅,為了飛航安全,飛機掠過頭頂的時候才能看清同伴的五官長相。機場照明雖不強,但滑行道上的飛機首尾相銜直排到了航廈樓空橋處。航班搶手,同時間就連沒空橋的接駁機位也停滿了客機。
這些急著起飛的乘客,在我們眼中就是一架架包裹好的空運肥羊。
我們架起合梯,替牆上的蛇籠鐵絲網蓋上棉被,正式吹響了入侵機場的號角。合梯跨過圍牆後,阿豪當先,黨員們接著魚貫地爬進機場。阿豪選了一架機翼比合梯矮的雙引擎窄體客機,單槍匹馬阻在滑行道上。他掏出槍,槍口對準了駕駛座的窗口。
沒有人知道隔了三十米以上,客機的窗口還能不能被克拉克手槍打穿,我猜機長也不想知道。機長舉起雙手,阿豪揚了揚槍口,我帶著隊伍提著鋁梯衝刺,躲著引擎,就著機翼架起梯子來。這應該是有史以來最癟腳的劫機,我硬著頭皮爬合梯,再跨上機翼。機翼下的同志等著我的手勢,把聖母像拋上我的高度。我接住了,這時,第二個人已爬上機翼,我們一起衝著機翼上的機艙門。
砰砰砰砰,聖母像的底座重重敲著飛機安全門。機艙裡的空姐猶豫了幾秒,我便作勢往窗口砸去,她嚇了一跳,趕忙讓安全門前的乘客退開。她一低頭,安全門往外掀開。
我抓著聖母像,衝入機艙,艙內乘客驚呼聲不斷。艙內所有的乘客連同被我趕走的那三個乘客都望向我。受矚目的感覺真的有點爽。
我學著驚恐的口氣:「完蛋了?去不了美國了嗎?」我照著阿豪教我的說詞念,「不,飛機還是會起飛,不會有人受傷。我只要錢不要命,請各位把身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交出來。」
ns 15.158.61.19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