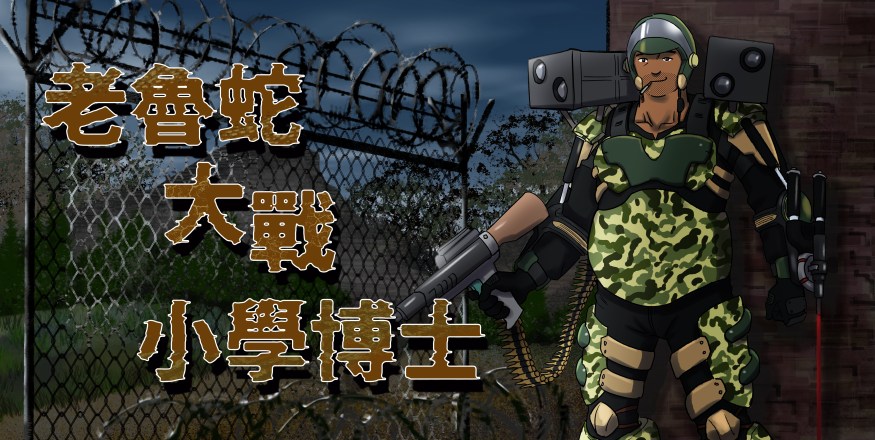8-7
直接暴露在火箭筒毒霧中的人都死了,包括班長。
防毒面具的防護功能顯然不足,可是直接暴露卻是必死無疑。
這煙團到底是化學毒氣,還是生化武器,我還不能確定。我甚至不知道現在的抵抗和逃命是否有用,我們會不會和中箭流血的獵物一樣,獵人一時無法殺死我們,但終有毒發身亡之時?
我、阿健、嘉豪和另外三個弟兄,面罩底下的雙眼被毒氣嗆出的並非鼻涕和眼淚,而是怵目驚心的血跡。
我的咽喉還像確診了武漢肺炎那般灼熱疼痛。
我偷眼望去,瓦斯分裝場外的停車場上躺了一個共軍,現在沒空管他同伴死活了。遇到運氣好,沒被炸彈震暈的共軍,我們現在恍恍惚惚的也沒辦法抵抗。
樓下炸得面目全非,分裝的鐵棚裡火焰還燃燒著,若是儲氣槽點著了,那才是翻天覆地的大爆炸。我們慢吞吞地跨過樓梯旁的女兒牆。樓頂上的鐵皮加蓋,下大雨似的承受剛才炸飛的碎片回落。那是分裝場爆炸炸飛的殘渣。
他媽的,還好老闆為了漏水,建了這座頂加,砸下來的聲響,比暴雨還響亮。
樓下搭了一個違建邊緣的塑膠雨遮,雨遮和底下的名貴禮車,成了我們落腳後最好的緩衝。
喔,對了,這些就是華國美學的招牌帶給我的安心感。喜歡大紅配深綠的老闆,總會偷偷摸摸增設一些些違建;他們永遠會為了方便,犧牲一點點安全措施。
這就是臺灣暖暖的人情味。反正他們早就私下存夠了共匪打過來,隨時落跑爽爽退休的海外帳戶。
我們六人翻出瓦斯分裝場的大牆,沿著海水淡化廠旁的木棧道踉蹌逃亡。我不知道爆炸的震波能阻攔共軍多久,也不知道我們中的病毒還是毒氣,要多久能殺死我的命。
總之就是沒了命地逃。
我們穿過一個露營拖車飯店,我實在喘不過氣了,脫下防毒面罩,讓弟兄們四處散開尋找乾淨的飲水。灌進嘴裡的第一口水,我只漱了漱口就吐掉。第二口以後,才勉強撐開灼燒腫大的咽喉,吞進肚子。不知道是不是毒氣的緣故,我覺得肺功能降低許多,即使用力喘氣也難以吸到空氣。
戴回防毒面具,可能在中毒以前,就會缺氧悶死了,我反正不想再戴了。但又不敢丟棄,只得掛在槍上。但沒走多遠,就遇到了「安檢所」
我愛死了安檢所,安檢所是平時海巡隊的駐點。而海巡需要派駐人員的地方,十之八九是因為漁港!
而港裡可能有船!
建築裡可能有槍械彈藥,可能沒有。但可疑的飛行器嗡嗡聲由遠至近,使我打消了搜索的念頭。我只幹走了安檢所門口的人形立牌。
海巡隊的人形立牌,跟交通警察立在省道上警告駕駛別超速的形式沒什麼不同,都是制服筆挺,持槍警戒的男性形象。如果共軍因為忌憚我們設下的陷阱,要探明情況,甚至放一枚迫擊砲彈重創我們,那無人機就會是最好的選擇。
這也就是我怕死了嗡嗡聲的原因。我們一跑進漁港,就要所有人散開,去尋找港裡存油最多的漁船。我則替人形立牌打扮了一下,為它戴上了防毒面具,指派他「擔任」防波堤牆邊站哨的工作。
當我們笨手笨腳地解不開水手繫繩,一群人蹲低躲著等我開槍打斷繩索時,無人機嗡嗡的噪音攻進了漁港。追擊我們的共軍好像忌憚了,無人機一發現人形立牌,就帶著上頭的迫擊砲彈衝向立牌。
炸了個轟轟烈烈。
以致於我再開一槍吸引不了旁人目光。
我們磕磕碰碰地調過船頭,調整方向,沿水道緩緩駛出漁港時,一男一女兩個共軍總算追了過來。他們像吃了自己的迫擊砲那樣,扣著扳機,對著船尾瘋狂射擊。他們用來當主武器的通用機槍威力又大,子彈又足。漁船的駕駛艙又直通船尾的平台。是人都怕子彈射,我們都躲到了船頭,躲到了駕駛艙前方的小小平台躲避子彈,沒人敢鑽回駕駛艙!
駕駛艙冒出黑煙,被他們這陣狂轟亂射,這玻璃纖維船身的漁船似乎已經失去了動力。
忽然,共軍停火了。
「舉手投降,沒用的,你們逃不出港口的。你們不投降,我們就活活射沉這艘小船。」那女兵喊話,「這樣吧,你們誰把領頭的綁起來投降,就能換取寬大處理。人民軍隊忠於黨,人民子弟護人民!」
又是共產黨的老招。先統戰,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最後再各個擊破。
我望著高懸駕駛艙兩側,長長的漁船釣竿,忽然有了想法。
「嘉豪,替我抽出這兩條釣竿的繩子。」
「一凡哥,這是拖網的繩索,這兩根像釣竿的東西,是撐開漁網的支桿。」
「叫你抽就抽,那麼多廢話幹嘛?」
「不是,一凡哥,我們不會出賣你的,我們絕不投降。」
我壓低嗓音,「你才要投降,你全家都會投降!」
「不!一凡哥,我不會把你綁起來的!」
天哪,嘉豪他那顆黃魚腦袋還沒轉過來。
ns18.116.42.179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