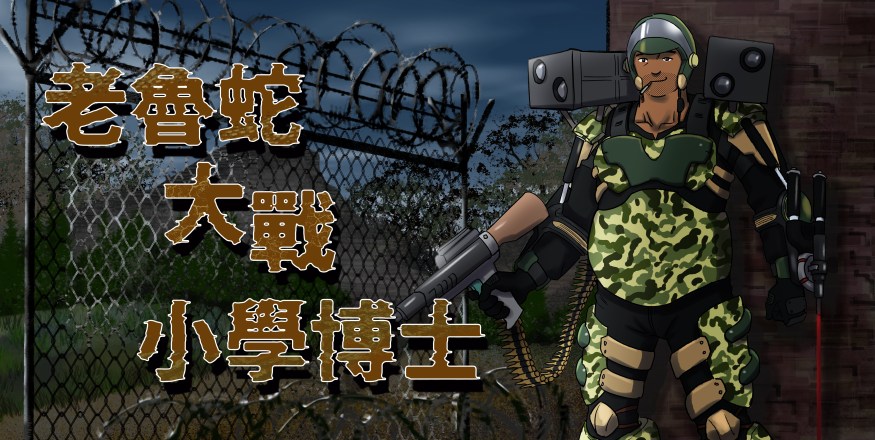5-3
共軍才不管什麼「三行三進」「S型前進」等躲避敵火的要訣。跑幾步,彈跳一下,以高度落差創造出難以預測的行動路線。眨眼間,我們身邊幾陣風吹過,共軍就蹲進了我們之間。
女兵大罵阿豪:「讓你看守他們,怎麼全解了手銬?」
跳進掩體的共軍不過寥寥五人,那個跟同袍打情罵俏的女兵也在其中。他們人人眼角、鼻孔都掛著血跡,就算沒死於裝甲車的殉爆震波,也已經受了內傷。強化人雖是血肉之軀,頑強的生命力卻大大超過了強人。
女兵揪住阿豪脖子。她身高跟180公分高的阿豪有點落差,但揪住阿豪,就跟提起玩厭了的洋娃娃一樣簡單。她問:「頭兒,這臺灣人兩面三刀,很是滑頭,怎麼處置他?」
掩體外,國軍乒乒乓乓地重新開火。那共軍軍官要眾人先抵抗,不重要的事等會再說。但悍馬車配合國軍行動,五零機點放開火,尋找著這座只有半面掩體、緊臨機場排水溝防禦工事的弱點。沒多久,在掩體外臥射的一個小兵中彈死了。我們抱著頭、趴在溝裡的污水裡,他們縮在掩體的一角,形勢越顯侷促。
「等一下!」共軍軍官一面喊,卻拉亮了一發信號彈,朝天空丟擲。這直上直下的一擲至少五層樓高。我的背後一緊,不由自主地被抓了起來,一管冷硬的東西指著我的後腦。共軍其他人見狀,也各自拉了一人當作人肉盾牌。這幾下來得好快,信號彈落到草地上,我們已全數被共軍抓到手中。
我身後的軍官說:「不要開槍,這些都是臺灣同胞。我們有錯在搭錯飛機,在兩岸局勢緊張的時候,來到了寶島。現在請你們後退,讓我們慢慢地談。聯絡你們的領導,也讓我有時間跟我軍領導彙報。記得嗎?有好些臺灣同胞在我黨的照顧下,我們能友好協商交換人質事宜。」
脅制了我們的共軍不再龜縮在警車構築的掩體後面,直接把我們當作了擋箭牌。來援的國軍槍口跟著共軍腳步移動,我有種被幾把步槍對準的感覺。
兩軍協商,讓共軍退回滑行道的民航機底下,那裡困著更多平民。共軍宣稱這樣才能避免武裝直昇機再回頭施放飛彈。
國軍軍官說:「你們應該知道,不穿防彈衣的平民,是可以輕易射穿的吧?」
共軍軍官答:「我自然知道。但你們也該知道,我們手中的六七式機槍,可以輕鬆打穿民航機的蒙皮吧?」
國軍軍官說:「好吧,你們不要激動。我去報告上級,這裡不要再有傷亡了。」
我們順利回到剛才打劫飛機的機腹,共軍派一人看住我們,其他人開會議事。沒過多久,他們似乎做出決定,單獨點了阿豪出來,拉著他討價還價似的討論了很久。
這段時間裡,機場牆外反映出的紅、藍交替閃光越來越密集,圍牆上也部署了越來越多的槍口。不知是特警還是特戰部隊的狙擊手,想來每個共軍頭上都被幾個槍口盯上。這場首都機場的空降突襲計畫,完全變成了與恐怖份子對峙談判。
過了良久,共軍總算放了面色凝重的阿豪回到我們之間。
他說:「他們想劫機回大陸。」
我嚇出一身冷汗,「這……這怎麼可能辦得到?我們頭頂這架飛機的機艙已經破了,他們得再搶別架飛機。」
阿豪說:「這沒什麼問題。強化人的身手不須爬梯就能跳上機翼,再讓機組人員打開機翼上的安全門,就能進飛機艙。」
今晚的見識,還有上海乘黃包車的經驗,讓我對中國基改強化人的體能毫無懷疑。
「可是,我們頭上的飛機還堵著滑行道啊。」
「對,他們在抽籤,看誰要進頭上這架,指揮飛機移動。」
「那我們怎麼辦?他會放了我們嗎?」
「說是那麼說,但我懷疑他們的字典裡沒有『信用』這個詞。」
「那怎麼辦?」
「臨機應變吧。」阿豪說這話的時候,臉上閃過一絲壯烈。
共軍軍官押著阿豪當作人質,離開飛機下方,去到滑行道的盡頭談判。台灣當局緊急派員負責談判。共軍軍官指指我們頭上的飛機,又指指我們,指得台灣代表不斷點頭,而後,代表又比比我們後方一長串的飛機。共軍軍官手指圈出了我們這架飛機,在空中劃出一條分界線。談判代表輕輕點點頭。意思大概是答應了,只留我們頭頂上的飛機作為人質,其他飛機都可以疏散。
共軍軍官仍是虛以委蛇,隱藏了真實意圖,去交換眼下真正的需要。
「媽的,司令員明明知道我們在機場不順利,怎麼還不打導彈掩護我們?」
我轉頭望去,是女兵向情郎低聲抱怨。士官也只「噓」了一聲,表情頗有為難。
ns 15.158.61.18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