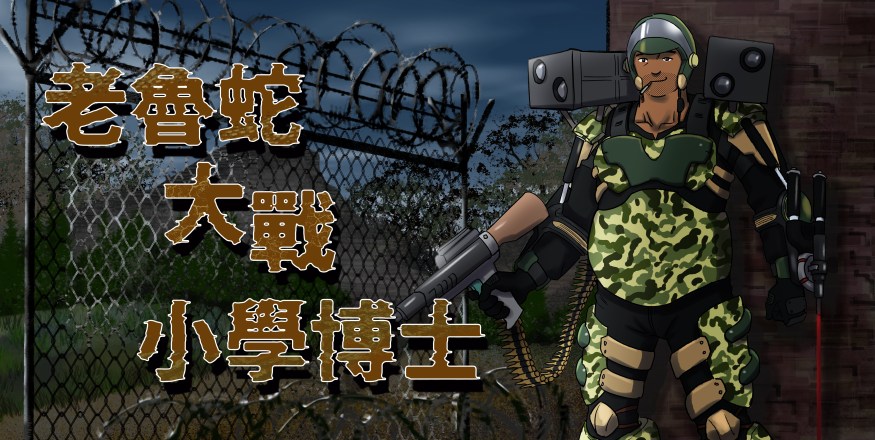5-4
隨松機全場大燈重新點亮,地上一處處的血跡與屍首,是一幕幕殺戮戲碼付出的人命代價。機場開燈不是為了方便共軍派人到貨機附近找東西,而是要看清他們需要尋找的補給,是不是談判時宣稱的醫療藥品。
共軍派出那個和女兵打情罵俏的士官去取協商的藥品。國軍部隊撤出了機場牆內,待在牆頭遙監。士官前進時沒使出彈跳、躍進之類的戰術動作,卻也保持警戒,槍不離手。但幾百條人命抵押在共軍手裡,國軍怎敢輕舉妄動?
士官在貨機傾倒了的後勤物資棧板裡翻找一陣,拎起一罐不鏽鋼保溫瓶樣子的物品再三確認,才給軍官發來「找到了」的確認通訊。士官把「保溫瓶」上肩,踏上返回飛機的路線,牆外的國軍有了動靜。
「停下來!我們要檢查罐子!」國軍用擴音器這麼說。
「立馬回來!」共軍軍官下令。
士官得了指令就像地面通了電,斜竄飛起。他的身後立刻冒出了幾點火星。士官縱躍引起了國軍的射擊,彈著點乒乒乓乓,一路追到了那士官遁進了我們剛才藏身的工事掩體。
我專心看著熱鬧,一面還想共軍為何在死傷慘重的情況下,還要寶貴的戰力去奪取「保溫瓶」?莫非是生化武器?對了,那罐子防護等級很高,就是設計來萬一這架貨機入侵失敗,甚至遭飛彈擊落,都能保護罐子的周全。所以國軍也疑心起罐子裡,是共軍同歸於盡甚或能反敗為勝的武器。
但我直覺又覺得不是,只是一件共軍當寶貝的一件東西。
我看那士官跳出掩體,忽然領子一緊,腳上一輕,已經被人從背後提了起來。跟我們在一起的四個共軍,一人一個,忽然把我與阿豪在內的四人當盾牌一般扛了起來!
共軍扛著我們,以頭上飛機為掩護急往航廈方向推進。當先的小兵當先離開了頭頂飛機掩護,雙腳加速,走到了滑行道上排著隊的下一架飛機。他把背上扛著的阿豪交給他後邊的共軍軍官,自己一躍跳上了下一架飛機的機翼。阿豪像一袋被人提著的菜,還沒從挾持人換手之間的搖擺取得平衡,忽然被用力一丟,像個布玩偶飛了上天。
共軍軍官僅靠擲鉛球的動作,就將一個虎背熊腰的大男人丟上3米多的機翼。機翼上的小兵隨即接住了阿豪,空下了手,又等著接擲上來的第二人。軍官騰出手後,自己也一躍上了機翼。扛著我的小兵走到機翼下,也把我拋擲上去。軍官不像剛才阿豪劫機那麼「秀氣」,直接跳到了機鼻,槍口指著飛機駕駛,要他向機艙空服員打電話打開機翼上的緊急逃生門。
找到物資,背著「保溫瓶」的共軍士官趕上了同伴。他讓女兵先上機翼接人,隨後把我的同伴拋上了半空。忽然遠處砰砰連響,士官身體被大口徑步槍接連貫穿。女兵見狀,哭叫起來,一時忘了接人,我趕忙飛身撲去搶救。幸好士官拋擲力量剛好,同伴在最高點時升力與重力幾乎平衡,利用這瞬間靜止的一秒,同伴亂抓亂扯,搆到了機翼邊緣,被我七手八腳地撈了起來。
共軍士官中彈後只退了一步,扯開「保溫瓶」背帶,甩了幾圈拋上機翼,沒人質在身旁的他,又中了三槍。
國軍一定識破了他們劫機的圖謀,先狙擊了落單的共軍。
不顧長官與士官的阻止,珠淚漣漣的女兵跳下機翼。她舉起士官,正要丟擲上機,遠處的國軍狙擊手看見敵人的生離死別毫不心軟,對女兵接連開了幾槍。
強化人體能再好,終究是血肉之軀,打破了內臟就不再具有戰力。女兵與她的情郎身子一軟,攤成了一團。
機翼上兩個小兵脅迫著機艙裡的空服員,打開機翼上逃生門。阿豪仍打定了主意要投敵,一箭步鑽進了機艙。
我太清楚共產黨怎麼整肅敵人的。飛機裡的乘客都有第二本護照,料想繳了贖金就能各自返回他們的庇護國。而我,是妥妥的臺獨反動份子,踏進這道門,好比步入了強制勞動營,甚或會被免費招待到西藏去——成為中印邊界衝突的砲灰。
兩個小兵,其中一人撿到了士官拋上機翼的保溫瓶。他們忌憚狙擊手,進艙後槍口朝外,一個指著我和差點摔下機翼的同伴,一個迫不及待,動手轉起了保溫瓶的瓶口。
機艙裡的乘客認出共軍,害怕槍,滿艙恐慌的驚呼更顯得機艙外的我們徬徨失措。
扭轉保溫瓶的小兵有點急切。他額頭冒著汗,右手發著抖,嘴裡說:「糙,這瓶兒怕不是摔著了?咋死活扭不開?」
「別急,咱營裡頭給我們練習的瓶,都是一梯一梯用下來的,早扭鬆了。」
我眼前,降下一道鍘刀似的人影,勁風逼得我退了一步。共軍軍官從機鼻起跳,硬是擠進了我和機艙門這狹窄的半步距離。
軍官才落地,就說:「新版本加了栓。起開!你們不會開。」
軍官背著我,站在艙門搶過了保溫瓶。
兩個小兵望著軍官手裡的保溫瓶,我發現,他們雙腳微微顫抖著,像剛跑了百米賽跑那樣喘氣。渴望的眼神,好比盯著主人賞賜肉乾的哈巴狗。
一瞬間,我什麼都懂了。我的心跳驟如急雨,右手慢慢摸到插在後褲腰,阿豪交給我的克拉克手槍。
ns3.145.48.156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