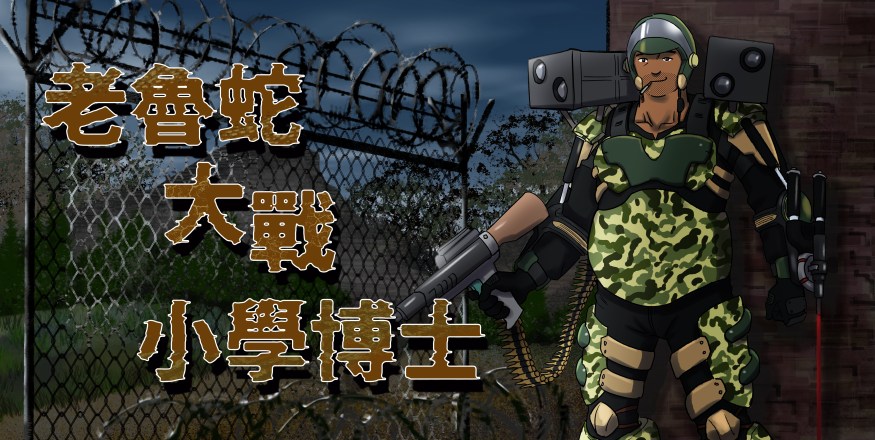8-5
「一、二、三!」
我卸下最後一顆手榴彈,拔除插銷,利用小夥伴舉槍胡亂掃射的空檔站了起身。視線一出陣地的長草的末梢,就目擊了一左一右竄逃的共軍。他們一模一樣肩著輕機槍,子彈掛鏈。該死,手榴彈的插銷保險已經拔除,我只能選一邊扔。
順著右手出力,我直覺地扔向左邊的共軍。手榴彈離手,我根本不敢觀察結果,蹲低身子,在砲架附近召集了所有人。
大家都在早些時候的無人機襲擊時,扔完了手榴彈,現場僅剩的兩顆手榴彈,都在班長身上。
嘉豪問我:「一凡哥,怎麼打啊?」
「打?什麼都沒了,還打個屁?你真想與島共存亡啊?」
「不打,那就是要逃跑囉?那我們能跑哪去?」
「我也不知道,或許島南邊有船或是機場還有飛機。總之,當初他們派我們來,就沒想撤離的事。我們只能靠自己應變了。」
共軍逐漸逼近,我們不及多想。由我揹著班長,嘉豪持槍押後,七人一列撤退。我憑直覺回到剛才觀看灘岸戰況的居民活動中心,帶著眾人翻過了澎湖機場的鐵絲網。
翻進機場的瞬間,眼前飄過了濃濃的既視感。
上回翻進機場的時候,我一言一行都仰仗著阿豪。現在,另一位阿豪,一舉一動都要問我,完全信任我。
不管經歷得再多,我仍對眼前挑戰感到迷茫。我不得不懷疑起來,阿豪當初也是這樣的嗎?今天換成阿豪帶著這批人奪路逃命,他又會怎麼做?
進了機場,一行人沿滑行道奔跑,澎湖島即將陷落,幾架軍用的黑鷹直昇機、救災用的海鷗直昇機無一不擠滿了空軍或機場的地勤。他們就像活屍片裡的活屍,或急著逃離戰亂的人們,塞滿了直昇機艙還不夠,溢出來的人們攀附著座椅,機門,甚或起落架的橫桿,花花綠綠的人堆,把一架架直昇機包成了飛天肉丸。
直昇機的每次搖晃,勉強保持平衡的每次前傾,都惹得機上的人們驚呼連連。那是求生的本能呼喊。我相信,任你見過再多死者,哪怕只聽了兩秒鐘,你也一輩子忘不了。
又是一陣陣慘叫,驚呼。
從天而降的人們不斷從直昇機上摔下,逼得我們得不斷抬頭閃避。我們剛跑到航廈前的停機坪,頭上直昇機人們的驚呼幾乎蓋過了震耳欲聾的螺旋槳音爆,忍不住抬頭一看,正好趕上防空飛彈擊中黑鷹直昇機的瞬間。
直昇機爆開一團火球,順著飛彈衝擊的方向,偏向跑道墜毀而去。
幹,這些雜碎,連逃命的人也打,還是拿高價的防空飛彈打,簡直喪心病狂,不知與徹底拋棄我們的臺灣臨時政府相比,究竟哪方雜碎些?
我們飛奔抵達滑行道盡頭的戰鬥機堡。
機堡是圓拱型,前後相通的掩體。共軍來襲,待命警戒的戰機早已scramble(緊急起飛)去了,剩下裡頭發動戰機的設備與隨時待命的「裝彈車」。空軍的人不是上了C-130,就是搶搭上直昇機,等來了防空飛彈擊落的結局。我真的不了解,島上官兵絕大多數都不是澎湖人,卻用守備家園的名義派我們到這個先進軍備極有限,毫無縱深可言的小島上。當局擺明了就是要捨棄澎湖前線,卻要求軍士官兵與島共存亡。
二戰有場軍民齊心的敦克爾克大撤退,難道法國領土比英倫三島沒資源、無縱深防守嗎?法國當局為何不要求她的官兵與國共存亡,願意讓她的軍隊棄國而去?明鄭時期鄭經派兵抵抗清國的施琅,在澎湖打光了手上的水師,也是與島共存的概念。打光水師以後呢?還不是得開城請降,薙髮留辮?
就在我們奔跑的光景,航廈上的旗竿已經換插了紅旗。幾個「清理完畢」航廈的共軍溢出建築,見到半空中掙扎的直昇機,不由分說,舉起槍就朝上打。他們歡暢的大笑竟能壓過直昇機的噪音傳到這邊來。
費功德,在你看來,這些陣亡的官兵只是棄子,卻是某些人的兒子、丈夫和父親!
機堡外的鐵絲網就是大馬路。希望落空的我們,也只能再翻出機場,到海邊去碰碰運氣。雖然裝備了PS,但我背負了班長,行動終究不太靈活。我高舉起一息尚存的班長,讓跨在鐵絲網的嘉豪替我傳到鐵絲網外。
我們這高調的動靜和身上的軍服,吸引了航廈解放軍的注意。他舉槍瞄射,幾發子彈都落在草地上,揚起的煙塵反倒提醒我們。
「快!」嘉豪伸出手,直接把我揪上鐵絲網。我們順利翻越,不及細想又得拔腿就跑。因為三個強化的共軍邁開大步,像月球漫步那樣向機堡這裡跑來。
「快走!」
馱負班長的阿健一個踉蹌。
「等等。」於是我摘下班長身上的手榴彈,從阿健背上再接過班長,又將手榴彈交給阿健。
「必要時就用!」
阿健點點頭。
眾人讓我走在了最前頭,沒幾步我們跑到通向一條小路的岔口。小路緩坡向下,路的盡頭直指一片海的蔚藍。
不只於此,一方小小卻蘊含「華國美學」的路牌,勾起了我全身的腎上腺素。
斑駁的招牌綠底紅字,標楷體的商號名「發發發」,搭配了底下印著正黑體的「瓦斯分裝場」。
冰友啊,身處戰區,只要看到這種招牌,就是靠譜的保證啦。
109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EXUlG9zLy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