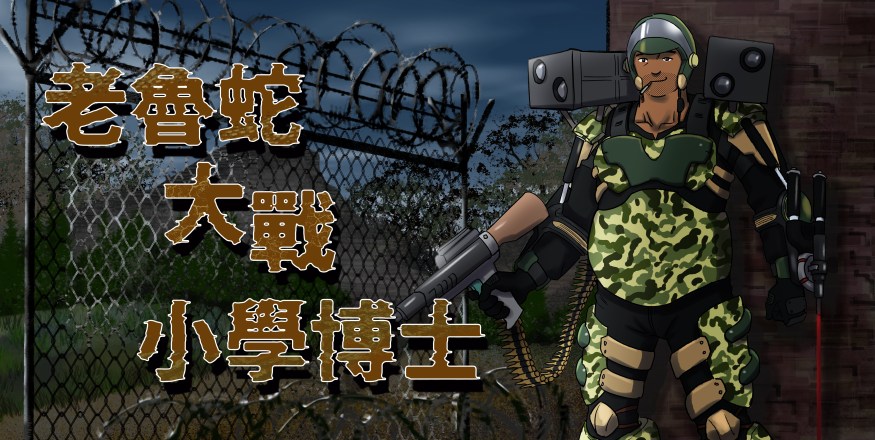5-5
上海拉黃包車的強化腳伕,跟共軍特戰強化空降兵,本質上並無差別。武漢肺炎病毒藉著感染細胞的過程,修改宿主的核醣體,來複製更多肌肉細胞或病毒。當體內抑制劑的濃度降低得無法干擾冠狀病毒的感染機制,體內的免疫細胞就減少到近似貧血的程度。
所以病毒抑制劑,就是共軍迫切需要的醫療品。他們服下醫療品,就會成功劫機,逃出生天。
一眨眼功夫,共軍軍官已揭開了保溫罐的封蓋。如我所料,罐裡裝的不是生化毒素,只是一大把米粒大小的藥丸。共軍官兵們看到藥丸,臉上都露出了久旱逢甘霖的微笑。一個小兵說:「隊長,我們早……早晚都用得到這……這些藥的,可不可以……多……多給我們幾顆?」
軍官說:「那怎麼行?我要清點過後如實上交部隊的。欸,誰的水壺裡還有水?」說著,就去摘小兵腰間的水壺。
我在背後抓穩了手槍,悄悄打開保險,拉動上彈的滑套。手槍啪鏘一聲,三個仰頭吞藥、配水的共軍,一齊停下了動作。
軍官面前的兩個小兵越過軍官,同時望向了我。軍官也緩緩轉頭。
我的手槍近得幾乎抵住軍官的背,砰砰砰開了三槍。對面的小兵嚇一跳,含嘴裡的一口水都噴成水花。我眼睛吃水,彎下腰抹眼睛,聽到了槍栓拉動的金屬聲。飛機裡都是乘客的驚呼聲,我自知命不久矣,別過頭去,連槍口也不敢正視。
共軍的機槍梆梆響了兩聲,我低頭檢查,跟感覺一致,沒有彈孔。一抬眼看見阿豪撲在其中一個小兵身上,阿豪竟然用他僅剩的左手在奪槍!
另一個小兵被阿豪撲上的力量擠偏了,剛剛卸下肩上的槍,一面望向著我,一邊急急地拉槍機進彈。
我舉起手槍,用射擊遊戲學來的射擊姿勢,左掌托柄,把槍口準心與覘口跟小兵的頭對成一直線。餘光看見小兵的槍口抬了起來。
我扣動扳機,後座力出乎我的意料,槍口抬高,兩發子彈都射在小兵頭上的機艙行李箱上。小兵嚇了一跳,他射出的子彈呼嘯而過,我反射性地縮了縮肩膀。
但他並沒移動腳步。我壓低槍口,朝他身體開了五槍。
砰砰砰砰砰。
驚呆了的小兵摀著胸口,身體像被剪斷提線的傀儡癱軟在地。機艙窗上、壁上,拖出了一道血痕。
一聲槍響趕走了我的驚愕。我挪移槍口,指向手裡機槍朝地的另一個小兵。這次我學乖了,朝小兵肺臟附近連開三槍。
他像中彈的魔鬼終結者,我每開一槍,他就被子彈擊退了一步,退到第三步,摔在了安全門對面的經濟艙乘客椅子上。乘客是個大叔,卻像個小女孩厲聲尖叫,喊破了嗓子。
這一喊又喊醒了我。一時間客艙裡的哭鬧、嚎叫如潮水般湧過來。我環顧艙裡,空姐躲在椅子後邊,有的乘客過度換氣,張大了口在椅子上不住喘氣。
他們望向我,望向共軍,最後望向了走道地毯。
順著他們目光望去,總算看到走到上滿口血沫,想咳嗽,卻咳不出氣來的阿豪。阿豪明顯是被自己的出血嗆住了,吸不進氣。
我撲向阿豪,要扶他坐起身,清理呼吸道。但他卻滿臉痛苦,搖手拒絕著我。我順著血跡,扯開阿豪的上衣,才知道阿豪胸口心臟旁被子彈貫穿,子彈在他胸口扯出杯口一般的大洞。
阿豪走了。眼睛裡痛苦裡摻著不捨。但面部肌肉一鬆,他空洞的眼神裡又映出我的手足無措。
組黨以來,阿豪的本事叫我又欽佩,又覺得相見恨晚。我對大環境常有一種忿忿不平,但阿豪他總知道要說什麼,又該做些什麼。
我在他身上學到很多——怎麼演說,怎麼搶佔道德制高點,怎麼道德綁架、情緒勒索。怎麼周密行動,怎麼帶領團隊。眾人總是迷茫,但他總有定見,總能給同伴指明方向。
就當我心中偷偷當他是哥哥,是師父,啪一聲,他變成了共諜。但他把我氣得咬牙切齒沒多久,又替我擋了子彈……人沒了。
寵辱臧否攜手忘,是非成敗轉頭空。
我輕輕放下阿豪,掩蓋了他沒來得及閉上的雙眼,從乘客腿上「借」了一條毛毯,遮掩了阿豪。
「奕帆,下面都是軍隊,下一步該怎麼辦?」一個同伴問我。
「下……下飛機啊,」我嗓子都啞了,險些發不出聲,「你有機票嗎?」
「沒有。」
「對啦。剛剛差點命都沒了,接下來能活多久都是賺的,不是嗎?」
機艙安全門外邊,已被聚光燈打成耀眼的矩形。我放下槍,高舉手,向安全門緩緩走去。
ns 15.158.61.18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