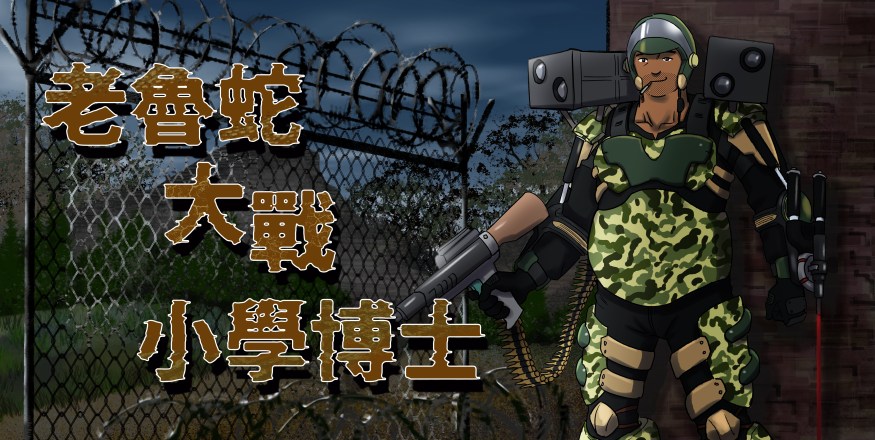9-3
隔海得見稀疏光線與隱約山形,直到勉強登入帳號,網速由慢變快。又過了差不多十分鐘,網速終於跑上了4G,兩隻手機的所有照片都上傳了,開始傳送影片。入港前,在澎湖拍攝的所有畫面都傳到了群組裡。
我也跟組員取得即時聯絡了。
看來「前線生還者」不只我們一組,等候我們下船的除了那些制服官員,還有架著攝影機的記者。
我跟谷霜飛、向封垣商量過了。要傳達勞動公正黨的訴求,現在就是最好時機。雖然我們感染了共軍生化武器的事已經傳回陸地,官方用長長的封鎖帶圈出了我們在碼頭走上救護車後送的路線,但記者依舊伸出長長的麥克風試圖「堵麥」。
「請問澎湖那邊的情況如何?」
「請描述一下前線戰況?」
「國軍死傷慘重嗎?你們怎麼撤退的?」
我深呼吸,一次接一次,我知道我只有一次機會。一定得一擊命中。
我突然大喊:「那一船共軍都是我們俘虜的!」
「什麼?請你詳細說明!」「哪裡有共軍?是後面那艘救濟船嗎?」
我一轉頭,見到了路線盡頭的救護車。它的後車門裡亮敞敞的,裡頭的設備,心臟電擊除顫器、氧氣鋼瓶之類的事物已近得一覽無遺。一個不知是陸地上還是跟我們上岸的軍官顧不得「安全社交距離」,揪住了我,試圖把我往救護車上拖,試圖加快我前進的腳步。
但我臉上罩著防毒面具,他捂不住我嘴。
「我是『勞動公正黨』代理主席,明一凡。我們都是後備軍人,他們把我們運到澎湖上就是當砲灰的,他們不管我們死活,沒有安排撤退計畫!」
「什麼?請跟我們說說澎湖怎麼失守的?」
「你們怎麼俘虜的共軍?你們帶著共軍撤退嗎?」
「你們殺了多少共軍?澎湖到底駐防了多少後備軍人?」
這些守候已久的記者就是在等如此大場面,他們像擁擠海域裡的鯊魚撕扯著鮮血四溢的鮪魚屍塊,不斷推擠封鎖帶,逼得海軍不得不出動小兵阻擋記者。直到我登上救護車,車門關上了,這些嘗到了血腥味的記者們還奮力拍攝救護車上的我。
當然,我也努力地配合拍攝。
讓他們挖掘、打擾吧,任何我待過的地方,接觸過的人,甚至我的祖宗十八代。
這樣他們就不可忽略地知道我加入的這個黨了。
110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kxpoJdUO1P
後備軍人召集為「守備部隊」,好不容易逃了出來,還俘虜了百來號共軍,最後卻失控對記者吐露真相的畫面一下子在各大新聞平台上流竄。就如我們所想,新聞記者對我這個無名小卒一下子感興趣起來。我曾租過的房子,服務過的公司都被挖了出來。我在魯蛇抗議集會裡,趕王南時下台,換了自己上去卻結結巴巴的畫面早就在網上了,這下成了新聞畫面的主要來源。
生活不得意、連棲身之所都買不起的中年男子,遭逢戰爭反對當局加入了地下民粹組織。本來意圖在松山機場搶劫逃往國外的雙重國籍持有者,卻剛好遇到了「松山機場事件」。被捕後,進入軍隊服役,被一腳踹到了澎湖當砲兵。逃過了共軍對全島使用生化武器的攻擊,帶領同袍弟兄逃出澎湖,還擄獲了一百多名解放軍的海軍。
這下阿豪跟王南時都被翻了出來。阿豪原來是滇緬「孤軍」的後代,在中國經商時被中共吸收為第五縱隊,回到臺灣接受中共在臺組織「黑虎」的調度,在臺發展「第五縱隊」。本來大眾看到這裡,是得懷疑我的陰謀,但俘虜解放軍交給海軍,卻又絕非第五縱隊的行徑。
有記者聯繫上了王南時,他又抑揚頓挫地告訴記者,他曾在新訓中心帶過我。他在部隊裡沒有發展組織,只是負責了一部分「心戰」工作,透過陳述共軍在「松山機場事件」的行動,向新兵們宣傳共軍的強化人部隊沒那麼可怕,國軍具備應處共軍入侵的能力。
他還透露,他要請調後備軍人組成的「守備部隊」,跟後備軍人肩並肩前進到灘岸第一線,去瓦解共軍的入侵。
他最後強調:「保家衛國,人人有責。」呼籲大家:「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都該支持全民國防,支持國軍。中共已經打到家門口來了,只有人人拿起武器抵抗,才能捍衛自己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馬的,這個唬爛王真會趁機收割流量,一顆子彈也沒打,就把自己包裝成了為國為民抵抗外敵的國軍先鋒。
ns 15.158.61.20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