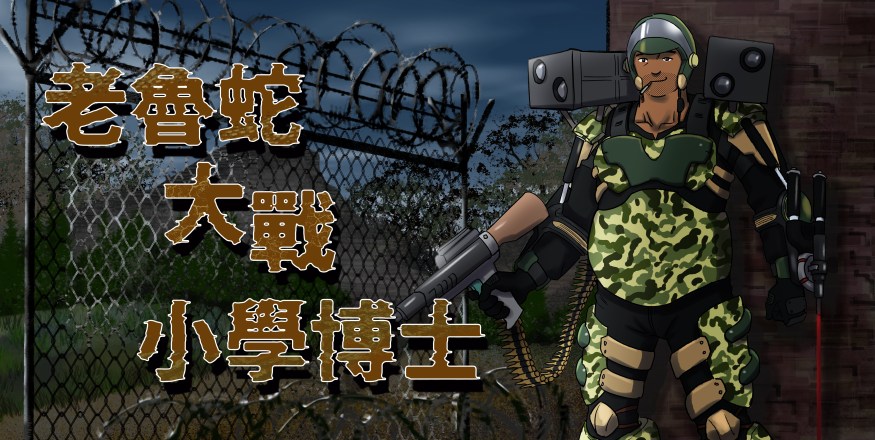9-4
我一下子成了費功德政府的燙手山芋,既不能法辦我,也不能再讓我出現在螢光幕上。當局以防疫、治療名義,把我們隔離在興達港(臺南與高雄交界處)附近的臨時野戰醫院。當局收走了我們所有的通訊設備,甚至將我單獨隔離在另一區,只有放風時間能隔著鐵絲網,遠遠地和其他人有片刻的眼神交會。這種交流方式資訊密度極低,僅能知道對方沒死,還在野戰醫院裡而已。
但透過電視與報紙的傳播,我仍看得出費政府正陷入巨大的輿論風暴中。撤退的國軍俘虜一百多個共軍是鐵一般的事實,所有媒體都拍攝到碼頭上一串穿著共軍制服的人,排長隊魚貫進了警備車。俘虜是真的,過去幾天,乘船自澎湖撤退的國軍加起來甚至沒有一次共軍的俘虜多,那麼,放任駐守澎湖的軍士官兵自生自滅,沒安排任何撤退救援方案的指控,當然也是真的。
戰前鼓吹「疑美論」的「等邊三角形」主和派,這時當然順水推舟大唱「疑費論」。質疑費功德政府甘為美國棋子,一面倒向美國政府,手法以臺灣人民為犧牲,用臺灣人的血肉之軀拖垮中國入侵太平洋的步伐。傳言宣稱,臺灣政府接受美國的指導,就是要複製烏克蘭模式,把臺灣打成一片焦土,來達成消耗中共軍力的目的,甚至,拖垮中共的財政,進而分裂中共政權。
經過臺海戰役,中共就會像俄羅斯一樣,軍力不再是美國的威脅。
我們當然兩不協助。一邊掌握亞太供應鏈和金流霸權的美國,另一邊則是經濟失敗要以戰養戰的中共。身為一個看不到退休未來的無產階級,這兩者都不是我可以認同的方向。
畢竟,人可以窮,千萬不能替財主打兩年工,就開始用的財主角度看世界了,這種打工仔的「優良」品行只是奴性而已。
野戰醫院的醫官終於確定了共軍對我們施放的生化武器,就是武漢肺炎的全新變異株。它在人傳人的場景裡傳染性不強,卻能在吸入煙團的瞬間發病、致死,完全是為了戰爭場景而開發的。治療也不難,感染初期服用了美國藥廠的抗病毒藥物,便能迅速阻斷冠狀病毒感染細胞與複製的機制,幫助免疫系統清除剩餘的病毒。一次療程須服藥三天,還不到染病的五天隔離期滿,我的症狀就減輕到幾乎無感。
就在我的症狀減輕到快篩試劑篩不出陽性,說話呼吸間還時不時誘發乾咳的情況下,一位「老朋友」進到野戰醫院與我會面。
來人雖然戴了口罩,但他把高高髮際線後,灰白卻油亮的頭髮梳成整齊的西裝頭。一看便知是個老人,但一身軍便服穿得筆挺,瞇瞇小眼顧盼生姿。經過澎湖這場慘烈的損失後,來人未發一彈,未打一仗,其聲名已被國內所有人知曉。
來會見我的,正是唬爛王王南時。
我被野戰醫院的「大白」醫護兵帶到會客區域。會客用的折疊桌椅正是我當兵時拿來應付高裝檢、陳列設備,甚至營區開放時讓訪客填寫個資的長、窄桌面,底下附帶了小抽屜的舊貨。
以防萬一,折疊椅擺在了長長桌面的兩頭,中間還象徵性地放了一塊壓克力板。王南時本來坐在一張折疊椅,隔著會客區域的鐵絲網一發現了我,站起了身,擺足了禮遇的態勢。
等我跨進了會客區域,王南時擺手招呼我入座。不僅如此,還除下了口罩,「明一凡,恢復得怎樣?國軍老愛擺這套,假戲真做,矯枉過正了。你知道嗎?院方要我必須和你保持兩公尺以上的距離,離開前還得做快篩,確認陰性才能走,否則我真想跟你這位保家衛國、功勳彪炳的戰爭英雄握一握手。」
「旅長,您太抬舉我了。不知道您這次來找我,是為了什麼?」
王南時帶兵25年,當然秒懂我話裡的不滿與戒備,他站起身,「唉呀,唉呀,我完全能理解你的心情。為國家立下汗馬功勞,卻還被上面懷疑,被晾在一邊。對國軍和國家的不滿,甚至怨懟都很正常。明一凡,我能稱呼你一凡嗎?」
我掙脫椅子,站了起身,「長官,真的不用,不用客套。」
「唉,一凡。臺語有句話說,『做到流汗,乎人嫌到流涎』,我完全可以理解你的感受,國家虧欠你了。不誇張地說,國家也虧欠了你們這一整個世代。你們對國家的不滿致使你們不在乎這些虛名、榮譽,這都是正常的。我今天來,是來帶給你一點小小的幫忙。不為什麼,就是出於我個人對你為國家犧牲奉獻的敬意。」
「哦?請問旅長有什麼提議?」
「一凡,不知你有沒看到報紙或新聞報導?我跟上頭說,這種帶新訓部隊誰都可以做,不用找我,我要效法你上戰場,到第一線去保衛國家。我這次來,就是想邀請你,轉調到我的守備部隊,101步兵旅。」
蛤?我在砲兵部隊打砲,小命都險些打掉了,這傻瓜還以為我會傻到去第一線蹲戰壕,傻傻等著無人機的炸彈掉下來?
ns 15.158.61.18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