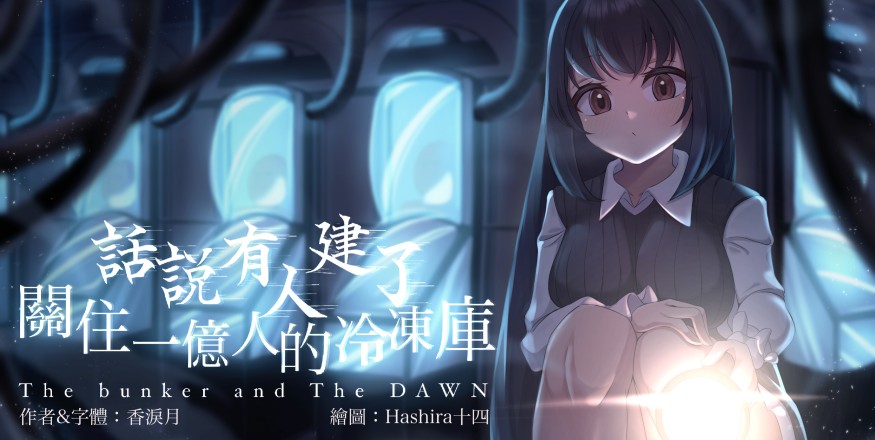是夜。
階梯層疊,林隱山洞,油燈初明,寂風拂地,颼颼的風嘯聲低迴望地。
洞口黃黑相間的警示欄杆被推開,黑壓壓的人頭排在兩三米寬的山洞裡,統一帶著防毒面具和穿著反射著洞穴幽光的防護裝備。
領隊的黑衣人拿著一盞巍巍亮著的油燈,走在排成方格的隊伍之前。他們在路上鴉雀無聲,直至隊伍中間的兩個人情不自禁地打開了話匣子。
「你說,我們都住山洞這麼久了,茹毛飲血的,不是怕外面的輻射,就是怕哪個岩洞有沼氣、劇毒。我們自己幾百個人,待在山洞都快要悶死了,每天都懷疑自己存在的意義,今天終於可以出來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了。」他說著一口流利的阿利伯語,在密密麻麻的人群裡低聲道。聲音穿過厚實的防毒面具濾棉,又變得更加輕柔,走在前面的長官估計絕對沒辦法聽見。
雖說是「新鮮空氣」,但他臉上帶著防毒面罩,包得緊緊的,就連本來他是什麼人種都看不出來,「新鮮空氣」也新鮮得有限。
「是啊,幾個月了,以前去打仗的時候也沒試過日子這麼難過。不是生活困難的那種難過,而是度日如年的那種難過,你懂嗎?我寧可戰死沙場,也不再想要待在那非人的山洞了。記得以前在沙漠打游擊戰,兩天沒喝過水,又忙著避地雷,日子也沒這麼難過。」旁邊的一個士兵也跟著埋怨道。
「不過長官說我們現在要去末日基地了,苦日子該完了,不用過著被全世界遺忘、忽略的日子嘍。」排在後面的士兵補充道。
「不知道那五百個高床軟枕的人見到我們這些本來應該要死的人會怎樣呢?」話裡夾雜著些許輕蔑的恥笑聲。
「會嚇到屁滾尿流吧!他們可以為只有自己是這世界的倖存者呢!」那士兵又接著調侃道,說起狠話來,這群士兵可是走了十里山路,氣也不喘一聲。
「你們也不要掉以輕心吧,老教授的冷凍庫基地聽說是很厲害的,誰嚇誰還不一定呢。」一片雜沓的笑聲和喘息交錯之中,還是有個士兵提出了他的疑慮,「況且我們連門都還不知道要怎進呢……那又不是什麼自動門,你說我們怎進去?」
話還沒講到一半就被走在他旁邊的士兵打斷了。
「你沒聽課的嗎?我們裡面有人……有人會幫我們開門。」他搞怪地故意壓低自己的聲音。
「你說什麼糊塗話呢!老教授派你來打擊我們士氣的嗎?」另外一位士兵又連忙插上一刀,「我們都相處一年了!」
的確,他們這一年多來都朝夕相對,從他們國家的秘密武器庫,躲到冷凍庫基地附近的山洞,這群士兵比平時的紀律部隊還要更有深厚的情誼。正是如此,他們才敢偷偷地在後面討論起今天的行動。但也是如此,他們不容許任何人在這個時候志氣消磨,自己潑自己一身冷水。
「那大門不是守衛森嚴的嗎?紅外線、重量感測器,該有的都裝了,比埃及的金字塔還守得嚴密。開門也不是一兩個人就可以決定的事情。這樣的話,我們應該不可能從大門進去吧。但除了大門,冷凍庫基地應該也沒有其他可以讓我們進去的門啊。聽說周圍還圍了幾米的巨型混凝土圍牆,爬也不是辦法啊。」
「我們自然有我們的辦法,條條大路通羅馬,當然不是只有大門可以走。」那個一開始說話的男人又重新加入了話題,在小孩的前面嘟囔道。
就在此時,走在前面的長官驀然揚起了左手,在山洞口蹲了下來。
他身後的軍隊應聲停下,整齊有致的踏地聲在山洞裡不停迴盪,在靜夜的空中蕩出幾個划破星辰的鼓點。
他的黑皮革手套撫過山洞裡的泥地,接著又把目光投射在那泥地上。
「等一下。」長官向著後面大喊道。
微濕的泥地上隱隱約約印著明顯的鞋印,從山洞的泥地一路印到前面的混凝土路上。
那鞋印實在太過明顯,鞋印上面的泥又未乾,估計不超過一天。
「有人來過。」蹲著的長官別過頭,向還站著的副手說。
但他看著這鞋印的指向,像是回去冷凍庫基地的。他們一路上也沒看見什麼奇怪的東西或者陷阱,說不定還是自己人出來幫忙探路。
不過,這運動鞋鞋印……實在太小,看著不像是男的。他再仔細看著,每一個步距很寬,像是臨急慌忙跑出來的。
會是誰呢?
正當他研究得無微不至之時,茂密叢林的一片青裡,卻突然傳來鳥聲啾啾,喊得呼天搶地般,又如雷聲貫耳,打斷了他仔細分析的思緒。
他抬頭一看,竟是一隻蔚藍色的鳥,比白天的蒼穹要更深一些,但比星夜又要淺一些,像是故意染出來的顏色,身上好像還塗上一層乳漆,光滑而又透著映射繁星的光,美得不像大自然,但又令人不禁讚嘆上帝的天矝。
他從來沒有看過這種鳥,這麼反自然常規的鳥。
這鳥有勾魂攝魄的魅力,讓人不禁凝視著他,把目光都投射在他的身上。
但身經百戰的長官從歷史和戰爭裡知道,漂亮的間諜通常最是要命,美麗的造物也通常都是有毒的,下意識只想到這迷人的鳥可能會有攻擊性。
「小心!」長官對著還在山洞裡的軍隊呼吼道。
「小心頭上的鳥!不要看著牠!不要再說話了!」長官故意對著後面交頭接耳的士兵說。
他可是一路上都聽見了他們的竊竊私語,只是見沒必要掃他們興,便讓他們繼續閒聊。大家這一年間都練就了好感情了,就算是長官,也不想當那個掃興的醜人。
「我們十二點之前要到達冷凍庫基地,大家加快腳步。」長官喊道。
說完這最後一句,他便再也沒有說話了,直至那隻藍鳥完全離開他們的視線範圍,他們的懸著的心才稍稍放了下來。
那藏藍色的鳥也很合作,只是一直站在初綻綠的樹梢,用牠嘹亮的歌聲唱著牠的歌。
大夥繼續在高低起伏的山路上走著,也沒人敢再哼半句聲,只是默默走著自己的路,偶爾抬頭看看那月色如許。
此時,大家卻都不知道,那處處質疑的小伙子某程度也說對了一些話。
ns 15.158.61.15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