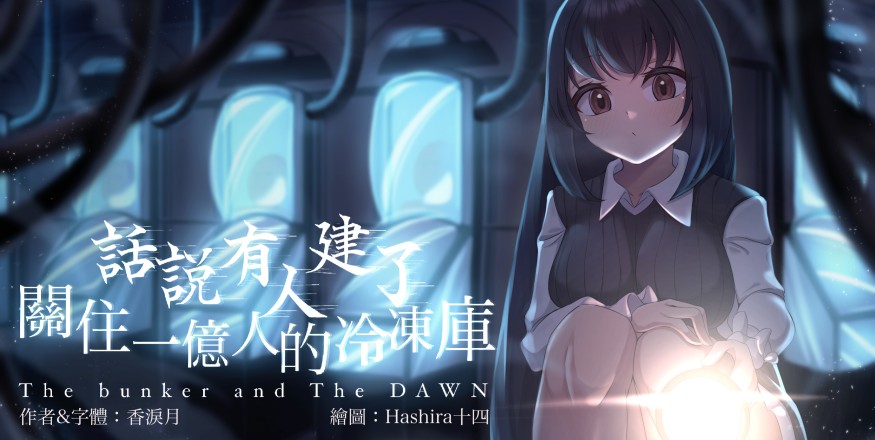K區大堂。
曼陀羅花香瀰漫開來,如織紗網,氤氳繚繞。
冷凍庫除了每層都有一種獨特的花香之外,還有不少建築上的小心思,聽說這都是韓國延世大學那位傳奇教授做的室內設計。例如幾乎每層的電梯大堂都會隨著往下的層數降低一個色差,在A區用的是有些刺眼的亮白色,到了下面樓層便漸漸變成了乳白色、銀鼠色、霧灰色直至N區的藍墨茶色。
從上面數下來,到了K區就已經是相當陰沉的青鈍色。
說時遲,那時快,單憑一道報位訊息就把茉雪給賣了的妲麗婭,不消五分鐘就已經相當諷刺地安然無恙走回了足音從電梯裡像是行屍走肉般走出,拖沓的足音裡絲毫聽不出有任何生機,只聽得出一提腳的遲來懊悔,還有一觸地的茫然失措。
她大抵是後悔的,但撲出去想把茉雪拉回來就已經遲了。
也許是接近地底,K區幾乎已經是不用開任何空調便可以自成一團沁入人心的涼氣,平時大家把這道自來清涼珍之如飴,但此時卻變成她心口上的一條尖冰刺。
只見電梯大堂的花圃傾頹著綠寶石般的羽葉蔓綠絨,因為大家最近的宵禁令,走廊上幾乎空無一人,平時會來幫忙打掃、喜歡園藝的居民也頓然消失無蹤了,於是就那麼毫無生色地倒在花圃旁的大理石磚上。
偏偏那涼風不領情,還沒等大理石磚挽留那將要離去的翠蔓碧草,就已經猛地把那幾棵已經相當孤苦伶仃的零落綠葉又推往另外一側。
她不知道剛才自己做了什麼。
她不知道她該去哪裡。
醫療室?
不、她根本沒臉回去。
或許她就根本只是一時之氣,一口說了一些五六年來都沒有勇氣說出來的話,她以為自己已經築了堤壩,卻在某年某月的今天崩堤,把一個她只見過三四小時的人送到敵人手裡。
她在做什麼,她本來不是這樣的。
她是曾經跟他出生入死的人,從「晨曦」策劃的第一場故宮遊戲她就已經在他身旁,之後他們去了遠東、日本、韓國,所到之處屍橫片野,她不曾背叛、不曾落半點淚,只是全心全意地在仰慕這個她明知她自己不可能接近的男人,現在卻為了一絲女人的嫉妒……
她坐在了電梯大堂的正中心,雙手掩著面,把外面的光、外面的世界都一同封鎖起來,讓她好好在空無一人的世界冷靜,把那些犯過的錯誤灑進深淵,並且想辦法把那個深淵補起來。
「你怎麼了嗎?」一把年輕男子的聲音恍如呼開了那個本來已經深鎖的世界,用英文喚著她。
也許是她恍惚了,她差點以為是林和晨從前線回來了。
「你是……?」剛問了出口,她卻發現這人似乎有點面熟,好像正是茉雪昨天晚上一併帶下來的那個她所稱呼的「小白臉」。金南鎮見妲麗婭似乎沒有任何惡意,便簡單介紹了自己,妲麗婭也順道說了自己是個俄羅斯人。
當晚見他疲憊地抱著一個小女孩,妲麗婭還以為他是個二十多歲,帶著女兒一起進來當五百人守護者的「爸爸」,這也是當時妲麗婭如此生氣的其中一個原因。
也許是韓國人的敬語習慣,他第一句便說了自己的歲數。起初他說自己只是十五歲妲麗婭還不大相信,但後來她好好的睜開了眼睛,看見他臉上剛毅的線條,天花灑下的燈光如金箔一般綴在了他的臉龐,白皙如同玉無瑕的皮膚,幾乎是從未被這世界摧殘損壞,有一種獨特屬於青春、年輕的秀氣,她也就信了。
原來她是茉雪的其中一個學生,因無家可歸故跟著茉雪逃來K區,回想起來,她也好像曾在第一次佔領行動通知教室的時候見過這個男孩,當時跟茉雪在聊天,身後的小女孩拿著一隻玩偶兔。
她再仔細回想,面前的這個男孩,好像與她剛才見過的那個金妍正五官什麼都不像,就唯獨耳朵的輪廓恍似同一個模子裡面倒出來的一樣。
當天冷凍庫緊急召集的尾聲,拿起錄音筆來控訴他姐姐的好像也是他,當時她心裡還暗自讚許後生可畏,竟不畏老教授管治班子的強權,差點跑上台來控訴他姐姐。
不過這男孩,應該還不知道他的老師現在落入了他姐姐的手裡吧。
金南鎮手裡握著一本書,還有三四份文件,看起來就像是從L區那邊的圖書館偷運出來的。
看來……是個小賊啊。
妲麗婭蔑笑一聲,突然坐直了腰板。
ns3.16.75.169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