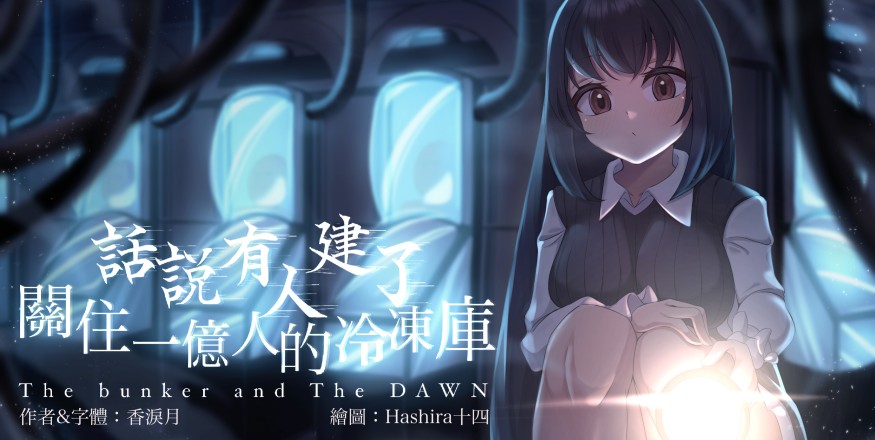K區。
國王的臥室前簇擁了一群侍衛,有本來國王留下戴著鍍金面具的親衛,也有王子留下來的幾十個侍衛,包了整整兩層。
人之多令國王寢室外面的一段走廊人滿為患,空氣也悶熱了起來,門口每個人額頭上積滿了晶瑩的汗珠。但這都是上頭命令,他們便是中暑了也得留在此處,他們也不明白,到底幾十個人圍著一個報稱中毒的病人到底有什麼好處。
「我說你們後退一點,你給我們騰一條路出來吧,我們想去方便一下了。」其中一個被圍在了最內層的國王親衛向後面的王子親衛喊道。他們裡面這群國王親衛,從早上國王抱病就寸步不離國王的寢室門口,在最近門口的那四五寸空間圍成了一個「內圓」,這整齊的陣容維持了大概五六個小時從未改變。
鍍金面具底下的臉都發汗了,褲子都快濕了,打份工、領三條金條,用不著這麼刁難吧。
直至剛才,有人真的撐不住了,外面圍著他們的人起碼是他們的兩三倍,又排得水洩不通,連去洗手間的路都沒有,他們也憋著起碼四五個小時了。18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dxcQbC1tm6
「沒人叫你們守在這裡,是你們自願的,想去洗手間當然歡迎得很,但出了去,我們就不能再讓你們回來了。」離內圈最近的一個王子侍衛費薩爾站出來說。
「我們誓死都要在國王身邊,這是我們的責任,寫到約章裡面。你轉到王子麾下之前也簽過的。」那個國王親衛咬牙切齒地反駁道。
「那你的意思是信不過我們一眾殿下派來的人,所以才找人堵在這裡?——我們也是受王子之命來守在這裡啊。你放心我們的話,現在離去就好了。」
但就是不放心啊,裡面國王說了很多次的,不能讓王子的人太靠近他……
「但我們畢竟同袍一場,你也讓一條活路來吧!各自職責所在而已!」沒辦法離開去上洗手間的國王親衛也開始陸續的加入罵戰。
「我也不明白你們執著些什麼。」這群王子親衛也是搞不懂,驅使他們明知希望渺茫仍還留守此處的是什麼?
「你們難道還沒有看清局勢嗎?我們都快要是一家的人了,王子親衛也會是國王親衛,正如某天我也會蓋過你的頭上,當統領,五塊金條一個月,而你只能乖乖聽我的……」還沒等費薩爾說完,他對面的那個國王親衛便一拳往他的臉打過去。
「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大不逆的話嗎?」那一拳響亮,在空中畫出了一條飛快的軌道。就連走廊遠處的王子也聽見了,但他聽見之後,倒是氣定神閒地繼續看這兩人如何發展。
那個出拳的國王親衛也忽然看見了走廊遠處有個穿金戴銀的人走來,馬上收下了拳頭。
「怎麼了?你……打我的人?」看見這場架無疾而終,王子難掩失望,轉而責難那個出了手的國王親衛。
那倒霉、人贓並獲的親衛也知道自己完蛋了,一時衝動,他主子還在病榻,可沒人來救他。他連忙跪在地上求饒,說自己知錯了,跪著的雙腿都不自覺顫了起來。
燭光搖影都照不亮此刻K區的走廊,焐熱不了這越來越沉的空氣。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這倒霉蛋上,紊亂的視線生出不少歧異,有的是取笑,有的卻是衷心為他禱告。
王子的性子眾人皆知,那動手的人最後還是當場死在了費薩爾槍下,還一次過在他身上掃了三槍,行刑式處決。
每下子彈打入肉裡悶響一聲,血肉就在眾人面前飛濺,最後還被王子殿下踩了幾下,確認人死了才命人拖走,毫不留情面。
這畢竟是國王的寢室前,他竟如此大膽就隔著房門把國王的人處決,還血濺當場,也是絲毫不顧忌國王的顏面。
以前他們或多或少覺得王子與國王父子情深,王子又是國王長子,也是難得在末日裡活下來的一個兒子,兩人關係應該不錯,怎料……一切都只是表面功夫。
如今國王倒下了,那個聽從父親的王子便不復存在了。
「看到後果了吧,開門。」王子在命人處理完那條屍體之後,踩上了地上斑斑的血跡,跟那個還擋在國王寢室門前的侍衛說道。
「我心情好,提醒你一下,我還沒打算殺第二個人。你讓路,一切好辦。」王子帶著威脅的腔調說著,絲毫沒有退讓的意思,說的每一個字還是那麼尖銳。
王子稜角分明的臉龐在那侍衛的面前,就像是染上了剛才飛濺的血色。他實在無法想像自己命喪當場的場面,想就此讓路,但腦海深處的理性又不斷提醒著他約章上面「至死不渝」四字。
「王子這……」他有點遲疑不決地回答道。
「我帶了醫生進來,給我父親看病的。為你們的國王好的話,讓路。」王子這才說明了來意。
「醫生?喔喔喔,醫生的話當……當然是沒有問題。」內圈的國王親衛馬上讓出了一條路來。
只見王子身後的確跟了穿著垂地黑袍、臉上掛著面紗的女人,她一路上不發一言。
從僅僅露出的雙眼可以看到她白皙的皮膚,寬肥的袖卻隱約顯出女子瘦削婀娜的曲線。她一路上雙手還被反綁在背後,到了國王寢室前才放開了她手上的麻繩。
這個女孩已經是整個醫療室團隊裡面反抗得最少的一個,也是他們抓到的唯一一個。被抓的時候,外面風風雨雨,而她恍在另外一個平行時空,蹲在後樓梯畫畫,滿地都是試水彩顏色的廢紙團。
這女生也是奇怪得很,侍衛去抓她的時候,槍都指在她額頭了。她也只是漠然抬眸,放下手上的畫筆和水彩盒,任由人把她五花大綁,連掙扎都沒有。
除了她之外,團隊裡面還剩下幾個力壯的男生還守在了醫療室裡面,架起了鐵板,設了路障,連機關槍都推了出來,沒幾個人敢靠近那條走廊。
於是能找回來的就這個女孩,一路上王子也是對這女孩嚴加看管。
但在這個女孩的眼眸中,他卻是看不到她的任何隱藏、心虛,反而是看到這個女孩,翠藍色的瞳孔中沒有一絲生機,就像是決意想要向世界放逐自己,在這人間任由自生自滅。
那黑袍女子在幾個侍衛的看管下,指節在木房門輕輕敲過之後,推開房門,緩緩的走向國王榻前。
王子則是站在一兩步之遙的地方看著,等待著這黑袍女子給出自己最想要的答案。
一邊看著這黑袍女子跪下翻看著醫療箱,手如白玉不慌不忙地在一堆醫療器材上游走著,那薄如紙的身姿著實是有點令他垂涎。
要是他心情好的話,他倒是不介意多個側王妃……
聽說這還是個俄羅斯美女,來自北方、充滿神秘感的美人,他還是蠻嚮往的。
但另一邊廂,妲麗婭卻差點嚇了一跳,四看了周圍幾十隻眼睛看著她,她才努力把臉上的詫異收起。
就在她拿起抽血的針筒時,國王眼簾缺突然微動了一下,像是把眼眸調到與妲麗婭對視的方向,隔著眼簾,盡可能挪用臉上每一條不顯眼的皺紋,向妲麗婭發出訊號,請求她幫忙保守秘密。
她一時無法組織言語,更不知道自己要如何才能填滿這個謊言。
她嘴角微微抽搐了兩下,忽然想起那遠在公寓區的軍師。
如此深謀遠慮的人,她如此景仰的人。他運籌帷幄,該是把這些都算進去了。
她裝模作樣地把所有器材拿出來曬了一次,又趕緊收起,接著轉身與王子用英文溝通,說是國王中毒的劑量輕微,一時奪不了性命,但還有待觀察,請他放心。
「你是說他暫時沒有生命危險?」王子不服氣地追問道。
妲麗婭也只好含糊地說:「說不定」——她從不能把活人說成死人。
此言一出,王子不忿,不忿他難得找到這麼一個良機下藥。能選的話,最好是神經毒劑馬上起效,難得從老教授姪子那獲得這毒物,仔細查看醫藥書,說是慢性毒也就算了,心想只要能起效就好,他可以等等。現在卻跟他說這毒奪不了性命。他這道怒氣該向誰發?
他心中鬱悶頓時無處宣洩,便逐個逐個踢倒身邊的侍衛。他的侍衛向來很配合這種洩憤方式,都會在王子的腳踢到自己的那剎那配合向後倒。早倒早超生,還能卸走一部分的衝力。
但輪到妲麗婭的時候,她可沒做過任何心理準備。
幾個侍衛紛紛倒下之後,她還佇在了原地,直至王子一腳踢中她腹部,她才因劇痛難受跌倒在地。
她也是在場唯一一個落地之後呱呱叫疼的人。
「真吵。」王子拎起了她的黑袍直接往外面走廊一扔。
「費薩爾,任你們處置了。喜歡玩什麼就玩什麼。」
「謝謝殿下!」費薩爾臉上難掩喜色,心想著這外國美女也是他到了冷凍庫基地才見過,這世界真是地大人博,如此尤物,他竟人到中年才有機會遇見。
但就在此時,費薩爾和他一眾同袍正一心想著今晚要如何料理這女人。
一直睡得安穩、臉上毫無生色的國王,像是意識到眾人快要離開,突然開了口發出像是夢囈的聲音。
「兒子……我想……我想見軍師了,我要見他。」國王虛弱地喚著王子過來,床鋪上的手微微顫著,想要抓著什麼,但看見自己的兒子站得離他遠遠的時候,又洩氣地放開了那隻帶著希望的手。
「見他?」王子卻像是沒聽到一樣,從沙發上站起便逕直往門口走去。
「屍體帶給你看看吧,如果你還沒死的話。」王子臨走前只說了這句話。
無情至極。
ns 18.68.41.148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