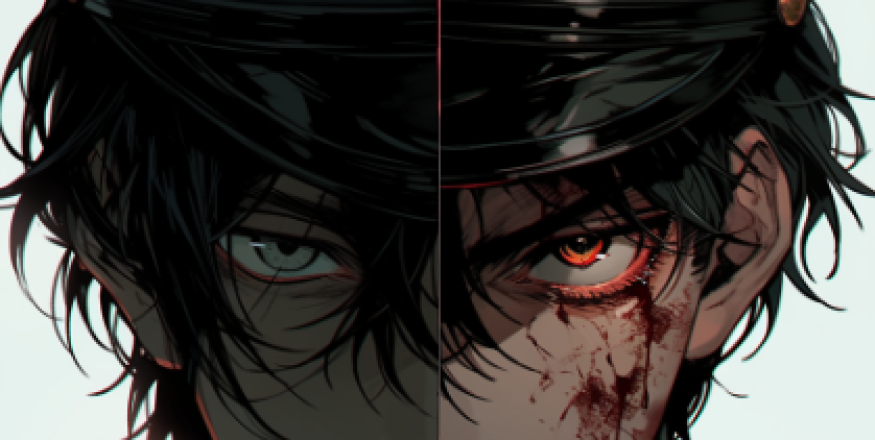鄭正,男,38歲,離異,無業,曾因搶劫傷人、鬥歐、故意傷人等多項暴力事件被刑事拘留,本是一個掙扎在社會最底層的無名之輩,因槍殺了白虎警署的署長趙陽而臭名遠揚。
易雲昭來到鄭正位於南郊的家,這是一間五、六十年代修建的紅磚房,一層樓住了十戶人家,過道擁擠不堪,連衛生間都是公用的。
事發當晚,特警敲鄭正家的門,並報出自己的身份後,就聽到屋裡一陣慌亂,緊接著,兩聲槍響,子彈穿過了門板,擊中了其中一名特警的右臂,隨後特警破門而入,將持槍的鄭正擊斃。
鄭家的門已經破敗,猶如其主人的命運,警方在鄭家門前拉上了一道黃色的警戒線,地上還有些許暗紅色的血跡,似乎在述說著那晚的驚心動魄。
易雲昭穿過警戒線,環顧著這只有十二、三平米的小房子,最裡面有一張髒亂不已的床,衣物散落在床上,連床下也塞滿了臭襪子、髒內褲和破皮鞋,旁邊兩層抽屜的床頭櫃也被拉開,裡面有用的東西都被負責收集證物的協警收集並帶走了;床的左前方有一台老式的電視機,電視機上還放著幾盒已經吃過的杯面,只是現在裡面剩餘的湯料已經發黴;在屋子的中間放著一張小桌子,上面放著幾張很久以前的報紙和一本記事本——因為看起來沒有用,協警才沒有收走。
易雲昭走到桌子旁,翻了翻那幾張廢報紙,沒找到有用的東西,又拿起記事本,翻開一看,裡面竟是小孩子的塗鴉。
「你是誰?幹啥的?」一個蒼老又略帶質疑的聲音從門邊傳來。
「員警。」易雲昭亮出了警員證,見他不是記者,大爺質疑的神情收斂了起來,「大爺,他們家還有什麼人?」
「他家還能有什麼人?老婆帶著孩子跑了,還能有什麼人?」大爺義憤填膺地說,「這孩子,從小就不學好,我們家以前就經常丟東西,肯定都是他偷的,哼,從小就不學好!」大爺住在鄭正家隔壁已經近二十年了,對此人早是厭惡之極。
「他有沒有父母兄弟?」
「不知道,從來也沒見他們來往過,哼,他天天半夜三更才回來,老是在外面鬼混,你們真是為民除害了。」
「大爺,你知道他平時跟什麼人來往嗎?比如有沒有看到可疑的人到他家?」
「這倒還沒有,」大爺想了想,又說,「不過有一天晚上我在拉屎,聽到他回來的聲音,好像在打電話。」
「都說什麼了?!」易雲昭緊張起來。
「我只聽他說‘別廢話,只要把錢給我,我啥事都敢做。’其他的話就聽得不清楚了。」
「你還記得是什麼時候嗎?!」易雲昭激動不已。
「上個月十三還是十四號,不太記得了,可能淩晨一點左右吧?!」老大爺也不是太確定。
易雲昭迅速記下了。大爺離開後,他繼續觀察著鄭正生命中最後出現的地方。
在屋子的角落,還放著一輛光鮮的兒童單車,它恐怕是這間屋子中最乾淨的物品了,也顯得與這間屋子格格不入。兒童單車和記事本上的塗鴉都表明了鄭正有一個孩子,估計他現在跟媽媽在一起。自從鄭正槍殺了白虎警署的署長後,媒體將他一切可以挖掘的東西全都挖掘了出來,但唯獨找不到他的前妻和孩子的去向,同時警方雖然得知鄭正得了五十萬,卻一直沒有查到這筆錢,且種種跡象表明,鄭正從拿到錢直至他被殺,都沒有揮霍過這筆錢,錢的去向已然成迷。
最合理的解釋應該是鄭正把錢給了他的前妻和孩子,可是他們現在在哪?!
易雲昭走到床頭櫃前,看了看裡面的東西,裡面只剩下幾張銀行信用卡中心的催款信以及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嗯?易雲昭的視線被一張白色的信封吸引住了,這個信封是仁愛兒童醫院的專用信封,裡面只有一張皺巴巴的兒童畫,畫著一個孩子左手牽著爸爸,右手牽著媽媽,站在草地上,沐浴在陽光中,開心地笑著,右下方是孩子的名字:鄭光宇。這張畫並沒有什麼特別,只是上面還有幾處水滴狀的東西,應該是眼淚。
仁愛兒童醫院?易雲昭暗忖著將信封放到了包裡,暗忖著,鄭正的孩子生病了嗎?那五十萬是給他治病的?!
在確定屋子裡沒有自己想要的資訊後,易雲昭離開了鄭正家,前往仁愛兒童醫院。
ns 15.158.61.37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