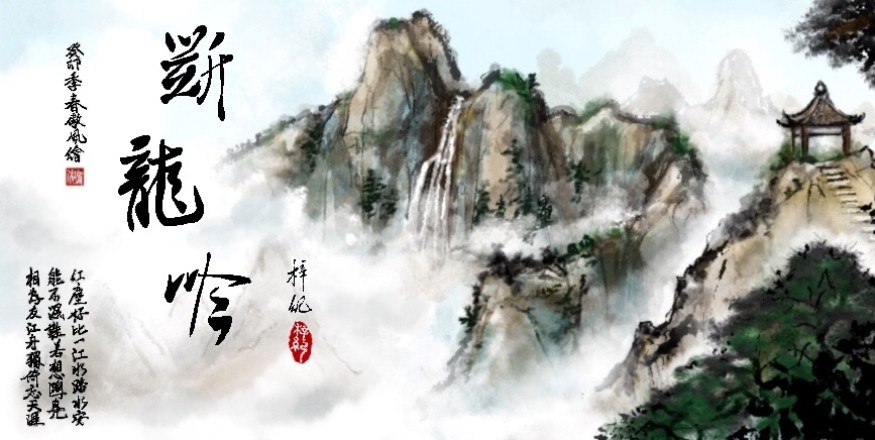夏雲石和高靈既有定奪,甚是歡喜。卻聽白常山冷不防道了句:「那如果朱安不在那呢?此去洛陽百三十里路,就憑這兩頭驢,也得走上個一天半啊!」夏雲石心裡自然也沒個底,一切不過都是猜想。不過轉念一想,此刻事態急迫,也沒其他方向好去,於是道:「就算尋不得朱安。這洛陽也有許多正派之士。再說除京城以外,北方就屬西安和洛陽的鏢行最為興盛。若使其傳出消息,或亦有大用。」
方向已定,三人也不再猶豫。青驢踏著黃泥而走。正月末,平地冰雪消融。時雨時雪,三人的衣著總透著潮氣。一路上,夏雲石只覺得憂慮不已,身心難暢。接連趕路,一行人終於在第二日午後抵達洛陽。
洛陽不愧為歷朝舊都,高靈瞧著路上行旅、眼前聳立的齊雲塔,不禁讚嘆道:「洛陽雖不再為都城,然京之大氣不滅,實在令人開了眼界啊!」白常山聽罷,倒是冷冷道:「曾經再怎麼輝煌,如今依然是沒落。沒看從前的通濟渠,現下也遭遺棄。」
聽聞白常山之言,再看洛陽,高靈心中的驚喜也隨之飛散。但覺偌大一座城池,好似蒙上了一抹哀愁。三人一路尋訪朝元宮,順道也在城內遊歷了一番。直到日暮低垂,行經舊殿遺址,物事人非,萬物蕭條,高靈不禁輕嘆了聲。一時,詩興既起,吟道:「夕彩繞京景,春風上苑巡。龍樓金闕里,御座玉橋濱。千古深宮樂,今朝高廟塵。哀哀朝野事,卻問為誰臣。」
此番吟詠,惹得夏雲石心中甚感悲涼,就連一路冷漠以待,刻薄相對的白常山,此刻也是眉頭低垂,一語不發。寧靜之際,一陣掌聲紛擾了夕幕。一個面目白淨,做書生打扮的中年人,一邊鼓掌說道:「姑娘所言甚是!當今世道,君不君,臣不臣。貪官污吏以百姓為魚肉,關外建州衛那幫蠻族,如今又打到了遼東。咱們還不如就像那毀去了的宮殿,不問塵世喧囂,不再為家國、百姓煩憂。如此倒是快活。」
這人不請自來,毫不在意三人束裝殘破,或是腰間的兵刃。除了高靈為自己的詩作有知己而欣喜外,夏雲石和白常山皆是警惕。要知見得三人這副模樣,一般人怎麼也得和那賣驢的老翁一般反應。尋常百姓面對江湖人士,哪怕是名門正派,亦是戰戰兢兢與之應對,倘若無事,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此刻這中年人,以書生扮相出現,卻從容自若,對三人絲毫不現懼色,甚是怪哉。
白常山上下打量了眼,心道:「這傢伙做儒生裝扮,散江湖豪氣,卻言避世隱者之語。究竟是何來頭?」雖有疑惑,不過這事做主的反正不是自己,白常山也就一語不發。夏雲石則是直接問道:「正如閣下在述。如今朝廷無心治世,百姓如陷泥沼。然而你我皆如滄海一粟,只能隨波逐流,倒不如稍出薄力,但求身邊之人安穩些也是好的。可不是嗎?在下落雁劍夏雲石,尊師方勤益之弟子,還未過問閣下尊名呢!」
那人哈哈一笑道:「世態炎涼啊!世態炎涼!小伙子你還甚是年輕呢!我就一落魄之徒,名號不足掛齒。既然有緣而遇,不如一同吃個晚飯?」夏雲石道:「閣下好意就心領了,我們還得要尋朝元宮去呢!」那中年人道:「這樣吧!我知道朝元宮怎麼走,不如同行,也順道吃頓飯如何?」眼看天色已暗,三人反正也感到腹中空虛,於是便隨著這人一起走了。
路上,高靈忍不住問道:「說起來,先生適才所言,金人犯境卻是何事?」中年人道:「那是這兩日才傳出的消息,看來諸位還未有所聞?說是奴爾哈赤領兵打遼東。更宣言『吾意已決,今歲必征大明!』以七大恨告世,強襲邊關。」聽聞此言,夏雲石忽得想起了什麼,對白常山道:「這事你早便知道了?」白常山點頭道:「知道是知道,不過我兄弟六人可不想淌這渾水,這才來此。」
中年人瞧了眼白常山道:「看來這位兄弟知曉些什麼啊?不如請兄弟來說說,對此事有何見解呢?」白常山道:「也沒什麼高見。只知此戰,明軍必敗。」中年人眼神閃爍,問道:「何出此言?」白常山道:「一是明軍軍紀散亂,明將貪生怕死,貪腐無能。二是情報外洩,金人對明之邊防瞭若指掌。」
ns3.128.226.139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