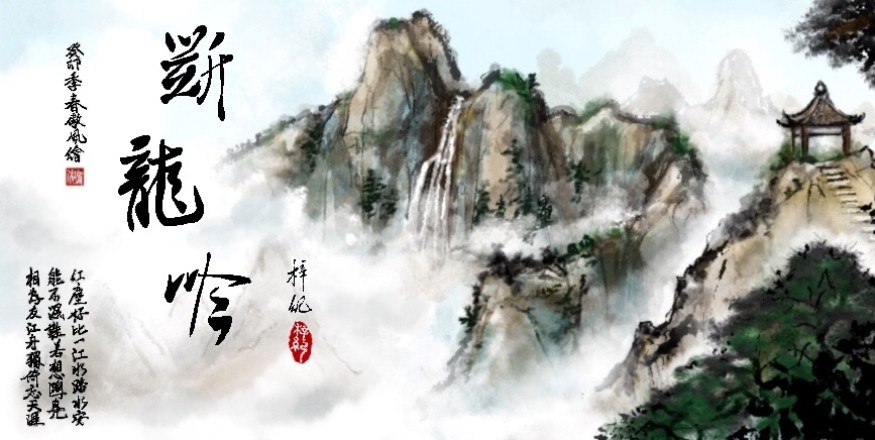齊大海聽了這話,正要開玩笑。卻被高靈一把不知從哪變出來的折扇,打得眼冒金星,一時暈頭轉向無法言語。在座的人心中道了聲「好」,全當作沒看到。
陸斷喝了口酒續道:「想從前,我也不長這樣的。那時我的家境還行,供得起我上私塾,考科舉。那時家裏還替我提了親。是縣城裏張員外的幼女。那女子,我本是沒見過的。那年我中了舉,年二十五。於是進京趕考,想去圖個功名。直到會試失利,回了山西,我才第一次見到那女子。」
「那女子小我五歲,大字不識得幾個。但是天真爛漫,小小的腦袋瓜子裏,總能蹦出許多新奇的問題。她喜歡山林野溪。聽說從前就常常瞞著家裡人,翻出牆去,到山裡溜達。那年夏日,近秋了,天候稍稍轉涼。我第一次和若蘭出遊。若蘭說:『以前還可以偷偷溜出來玩,現下大了,被管得可緊了。整日裡待在院子書房的,好生無聊。還好有你帶我出來走走。』我看她講得楚楚可憐,心中像是銅鼓震震,不斷地敲打。」
「昔有秦少遊『新晴細履平沙。長記誤隨車。』那時的我算是懂得那般情懷。不過我更幸運,若蘭已是我未過門的妻子。我心裡打定主意,要讓她時時露出笑容。因此那年冬天之前,我總會帶著她遊山玩水,賞秋葉星河。說起來,她可真厲害。山裡的樹木花草,她總能說出個名堂來。每每問起,總道是:『山裡採藥的大爺教的。』如此這般,我們之間也就越加緊密。」
「那兩年算得上是我人生中最快活的兩年。後來我又再往京城。可惜天不從人願,這年會試我依然落榜。回程時,更是染上怪疾。好不容易撐著回了鄉,一趟便是大半年。待我轉醒,身形已枯瘦如柴,五官亦歪斜變形。我聽說若蘭曾來看過我。但他家裡人不讓她靠近處看,只能隔著屏風遙遙相對。再後來,張員外等不起了,便將若蘭嫁了人。說是嫁到外頭。」
高靈聽得入迷,怔怔地問道:「那你們後來還有見過面嗎?」
陸斷苦笑道:「造化弄人,造化弄人。我自幼體虛,家裏便讓我習了武。現下生了怪病,莫說考試當官了,就是這副德行,走在路上都要受人冷眼。於是我將自己關在院子裡,足不出戶。只是練著曾經學過的武藝。才不過一年,我們這卻發了瘟疫。張員外死了,我爹娘、兄長也死了。反倒是我,竟全然無事。於是家也沒了,人也沒了。我生無可戀,乾脆就收拾了點行囊,四處流浪。」
「走在路上,總不免遇上些地痞流氓。於是我越來越能打。我漫無目的的走,遇上了不公義的事就打。後來也結了不少仇家。我曾經助過一個少爺,那少爺給人打的慘了。我看再打下去,是要出人命的。於是出手幫了他一把,替他趕走了那幫人。誰知後來有仇家循線追著我的下落,尋到那少爺那,幾十兩銀子就把我給賣了。我被設了圈套,被打個半死。好在那時大哥出現,救下了我。」
「從此我便跟隨著大哥走南闖北。我再也不隨意幫人。本來我倆行走江湖,也多少避著些骯髒事不幹。誰知總有那不分青紅皂白的『俠士』,每每見了咱倆就像見了妖魔鬼怪一般。我就問!這世道難道就沒個道理了嗎?就因為我們兄弟幾人生的怪異,就要我等扮惡人,圓了他們的俠義夢!」
陸斷說到動情處,一掌拍在桌面,弄得茶杯翻到,茶水四溢。他扯著嗓子續道:「既然世人要我們做惡人!我們便做!從此以後,我們就只做那劫鏢的活,專殺那些個強出頭的,虛偽的貨色!」陸斷歇了口氣,稍稍緩和後道:「後來一回,那時我們兄弟六人已然結拜。我們劫了趟鏢。你道那鏢的主人是誰?」
夏雲石聽到此處,小心奕奕的問:「難不成是若蘭娘子?」陸斷沒有什麼動作,只是答道:「他鄉遇故知,本是件教人歡喜的事。怎奈何是在這般情境?我看著他那癡肥臃腫的丈夫,甩著兩坨肥肉驚慌失措。若蘭跪著,替那頭豬求情。一幕幕從前的景象,一時全都湧上心頭。我讓兄弟們拿走錢財便是,不要殺人。然後就這麼站著,直勾勾地看著她。我一句話都說不出啊!我有萬般言語,曾有多少不解,多少怨恨,到頭來卻匯不成一個字啊!」
「直到一個小胖子用他那不堪入耳的哭聲打斷了我,我這才回過神來。要說那小子,臉蛋若瘦一些,還真像她啊。我沒有再多看他們一眼,他們也只是重複說著『大人饒命』話語中像是全不認識我一般,既不套關係,也不提舊情。彷彿我倆就是陌生人一般。於是我轉身便走了。」
ns3.140.192.22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