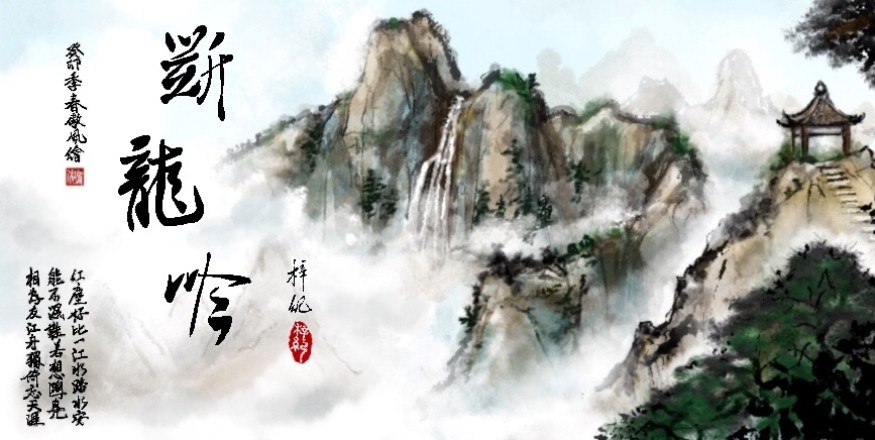有言道:「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江南的春日與北方不同,北方殘雪未消,寒風尚冽;江南春風輕拂,鶯啼千里。二月的江西,寒意已退。碧水映晴天,遊人滿江畔。
江西泰和,舊名廬陵。此處歷來文風鼎盛,名人輩出,更有「江南一等富庶地」之盛名。泰和縣城,近水處,有一院落。庭院深深,高樓相對。庭院中有垂柳隨風而盪,百花含苞欲放。清風起,百花叢中已有暗香隨風,即便在二樓的書齋亦能得其芬芳。
宅院的主人名為郭子章,曾任右副都御史、貴州巡撫。平定播州之亂後,告老還鄉,回到泰和安享晚年。郭子章平日裡,最喜命人砌一壺茶,在書齋中倚著窗外山色,抒其胸臆於案頭。不過今日之閒情,全因一人來訪而斷。
書摘中,與窗櫺遙望的是一對圈椅。圈椅上坐著一人,那人臉上有一道長長的疤痕,從左耳根一路劃到嘴角。在整張佈滿皺紋的老臉上,這道疤已淡去許多,不再顯眼。但若細看,卻依然令人發怵。面對此人,郭子章持杯的手不自覺發顫,上好的普洱都撒出了許多。那人悠悠地擺弄著手中亮晃晃的雙鉤,罕見地咧著嘴笑,笑得令人發毛。若是沐雲楓在,定會詫異,自己的爺爺沐惟之,怎會露出此等面容。
沐惟之自顧自的說著:「『郭外人煙好,行行過北仟。迎船分社肉,汲井種春田。綠樹前村路,黃梅細雨天。客遊鄉土別,景物只同然。』這詩說是在寫廬陵,也就是這。郭尚書,你說這詩寫得貼不貼切啊?說實在的,我是真不知道這兒的春天怎麼樣,不過就最後兩句,我倒是不怎麼認同。這兒跟播州還是差太多了。郭尚書,你說是吧?」
郭子章用發抖的嗓音道:「你⋯⋯你⋯⋯楊應龍!你不是早已伏誅!你⋯⋯」沐惟之淡淡地道:「楊應龍啊?好久沒聽到有人用這個名字叫我了啊!怎麼?很訝異嗎?現在腦中出現的,是不是我在京城,一鞭鞭、一刀刀、一棍棍被戮屍的畫面啊?」郭子章漲紅了臉怒道:「你⋯⋯」
沐惟之,或者該稱楊應龍,不等郭子章說話便搶道:「我也去看了,老實說,還真是精彩啊!若不是知道被架在那兒的人是『我』,還真要教人血脈噴張,同仇敵愾。」看著郭子章又是盛怒又是驚恐的面容,楊應龍又道:「還是很震驚嗎?你想啊!我,楊應龍!怎麼可能自縊?不過替我去死的傢伙是真的挺像我的不錯。」
郭子章道:「你這叛賊!都已過去這許久,如今還想怎地?」楊應龍道:「報仇啊!難不成來喝茶敘舊?嘿,不過你也不用緊張,你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你不孤單啊!」
郭子章深深吸了口氣,嘆道:「罷了!老夫本就行將就木,要殺快殺,少在那激人了。只怨蒼天無眼,禍害遺世!」
楊應龍開懷笑道:「反正你是躲不掉的,別急著找死。倒是做了這許多壯舉,卻沒人聽我訴說,那感覺還真不是一般難受。你說,你就不好奇我是怎麼走到今日,又打算向哪些傢伙報仇嗎?」
郭子章道:「那些話你就自個兒憋著吧!沒人想聽你說。」說著郭子章默默抓住身後駕著的一把雁翎刀,接著猛地一抽,刀尖直對著楊應龍,狠狠瞪著他,口中就要呼喊護院武士。楊應龍卻先開口道:「要叫人可以,不過醜話說在前頭,只要多一人出現,我就滅了你全家。」
郭子章只道了聲:「你⋯⋯」楊應龍便又道:「你可知道李化龍怎麼死的?他們全家上下,百餘口人,含護院、奴婢、丫鬟又是怎麼死的?」郭子章剛要說出口的話一時又吞了回去,怔怔地看著楊應龍。
楊應龍昂首道:「沒錯都是我一人殺的。就憑你們這些拿著令旗躲在後方的傢伙,還真以為頂了個兵部尚書的頭銜,拿了把尚方寶劍,真就天下無敵了?」
楊應龍起身,走到郭子章面前,用銀鉤勾住雁翎刀,接著一發勁,便從郭子章手中奪過了刀來。跟著說道:「萬曆二十八年,京城戮屍後。我本就要找李化龍報仇。結果自不用說,不但仇沒報成,還被官兵追捕了兩年,險些在山東廟子鎮喪命。不過也好在廟子鎮慘遭屠村,我才得以脫離官府的追緝。不過那時我身受重傷,眼看就要不活,你可知發生了何事?」
ns3.140.197.62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