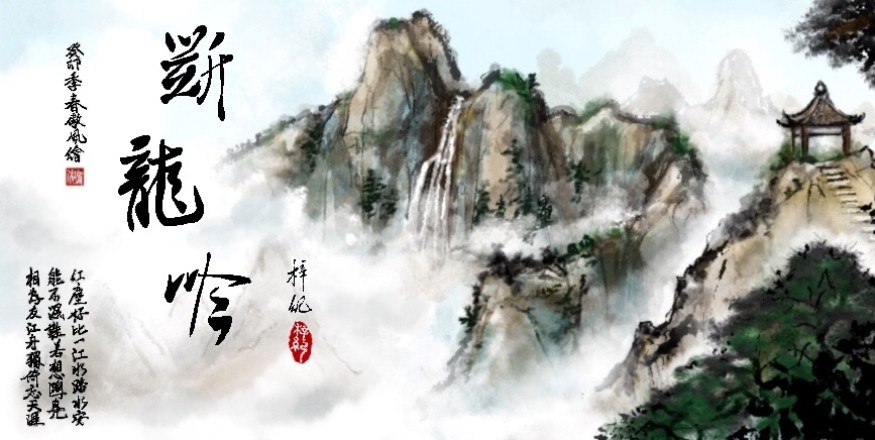鱘龍幫的幾人,臉上更添異色。強硬的外表下,一股哀傷、不甘、憤恨隱隱流瀉於眉目之間。金乘風在江湖走跳久了,知道不合人性者必然反常,而反常必有妖,暗想:「這幫人興許有什麼軟肋給人掐住了,那可是吃軟不吃硬的。若繼續這般強硬逼問,怕要壞事。」
於是不待方勤益再次開口,金乘風語氣隨即一轉,緩和地問道:「看各位神色間透著無奈,想必此行並非出於己意?」
鱘龍幫眾各個唇齒緊閉,默不做聲,眼神比之先前又更加狠戾。表情多了,也就有那麼點不自然。金乘風一下便篤定了自個兒的猜測,接著又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輩中人都是知曉的。不過若為奸人所迫,專行不義,卻有違俠義。今日見諸位來此,既非出於本意,有何難言之隱不如說給老夫知道。以我金乘風的名頭,行於江湖,怕還沒什麼事情解決不了的!」
聽聞此言,老者嘆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此話不假。咱們鱘龍幫與金掌門、落雁劍素無交集,然而我為箭矢,人為弓弦,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實在由不得我作主啊。」
金乘風道:「那麼便讓老夫來助你如何?你們背後究竟是何人?又是以何種手段相逼?這些事可得好好說與老夫知道。」
那老者低頭,沉默良久。其餘成員或趴或坐,卻也只是癡癡地看著老者,眼神混濁,好似將死之人,慘淡而無奈。察覺到這些人的神色,方勤益眉頭微皺,與金乘風兩人都感到一股不協調。心頭異樣之感,使得兩人好生難受,暗暗挪移至溫愈和沐雲楓身側。
這時老者又道:「唉⋯⋯即便說了出來,也是無益。只能說咱們誤入歧途,連累了夥伴、妻小。今日橫豎都是個死,就是天王老爺來了,也救不得咱們啊!」這句話出自肺腑,聽得金乘風老臉微動。活到了這般年紀,少有一句話如此深入金乘風心坎,令人悵然。鱘龍幫一夥人黯然之際,眼中更現決絕。
金乘風正要開口,老者卻又續道:「金掌門獨步武林,難逢敵手。我等自然不敢小覷。然而這件事金掌門卻也做不了主的。咱們生死受人操控,命懸一線,他們要咱死,咱遲一刻也不行。如今莫說叛逃,就是失敗,無功而返,咱們兄弟、妻小都將受盡折磨而死。金掌門可莫要怪我不知變通,不願回頭。實在是騎虎難下,回頭無岸啊!」
金乘風道:「白蓮教手段難道就這般強硬,一線生機都尋不得?」
「白蓮教?」老者搖頭慘笑道:「金掌門,在下雖然不是什麼高手、豪俠,不過到了這把年紀,聽聞的事多了,對您其實好生景仰。只能說句對不住了,若有來生,切讓我等生做牛馬,償君之命!」說罷,眼神忽地放光,迥然之間,參雜無奈、不甘、愧疚、堅毅。抬手之際,一夥人各個動作一致,火石作響,星火閃爍。
金乘風心道不妙,和方勤益一手拉著一人向後急退。電光火石之際,團團火球平地而起。「轟」地一聲巨響,熱浪將破廟的門窗盡數掀飛,就連為數不多的屋瓦也紛紛落了下來。鱘龍幫眾竟是引爆了早已藏在懷裡的火藥。十餘人一同自爆,其狀之慘烈、其勢之威猛,令人毛骨悚然。綜觀武林,皆屬罕見。
小小一間破廟,此刻四處焦黑。好在金乘風等人及時躲至樑柱之後,各自運行內力與之相抵,方才逃過一死。此刻就連金乘風的鬍鬚也都蜷曲成球。至於阿古達木則在爆炸之時閃身柱後,手上鐵棍舞成圓圈,硬是破開熱浪。除了衣角焦黑之外,並無大礙。不過待到塵埃落定,內傷反噬,阿古達木頓感喉頭一陣清甜,一口鮮血便從嘴裡一吐而出。
看著地上一排焦屍,身首異處,面目難斷,就連金乘風都覺得怵目驚心。心神初凝,陣陣疑惑頓上心頭。方勤益默默問了聲:「金掌門,要有這股魄力以身為引,爆體而終,那可需要多大的恐懼、脅迫,方能促成啊!」
金乘風沉默良久,吁了口氣道:「且莫說脅迫不脅迫的。就是火藥這等邪物,放眼江湖,哪是這般容易取得?況且還如此量大。老夫以為,此事定有蹊蹺!」
方勤益點頭道:「鱘龍幫身在長江,倘若是受白蓮教指數,那這白蓮教的規模、手段⋯⋯」
ns3.137.210.13d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