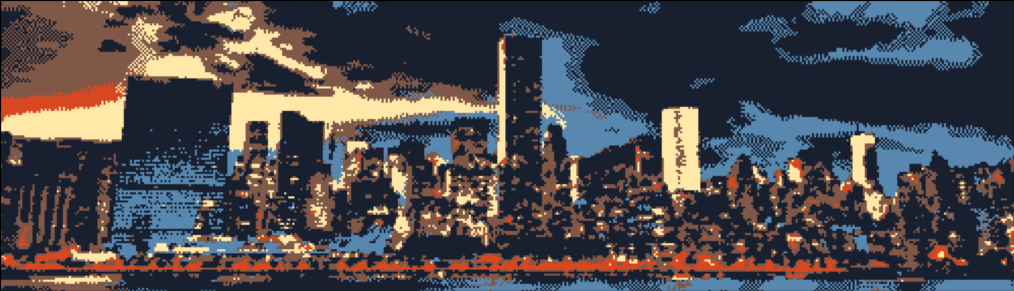 x
x
「蛇蜷所做的事不能怪到我們身上。」戰慄告訴我。
「我們確實促成它發生。」
「我們不可能知道他到底幹了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洋洋得意,沒把事放在心上。因為如此,也因為我們以干擾假面協助蛇蜷,黛娜就被綁架多久了,三週?幾乎一個月?」
「幾乎一個月。」媘蜜重複我的話。
我看向媘蜜,注意到她在抗拒與任何人對視,我對此有一個不快的想法。「妳之前就知道了嗎?」
「我……」她頓了一下,嘆了聲息,簡短地與我的視線連接之後,繼續瞪地面。「我算是,有些概念。我沒想到會這麼醜惡。很難解釋。」
「試說看看啊。」我說道,嗓音有些僵硬。
「她在我們搶那間銀行的同一天,從阿爾卡迪亞高校附近的中學消失。顯然是,蛇蜷想要確保監護者沒有足夠近到干預,八成也是為什麼他在我提議之後,這麼熱心要我們接那個工作。我之後,也連結起了這件事。我只是沒想到……他所說或所作的,都沒讓我想到會是這麼嚴重的綁架案。」
「那還能是什麼呢?」戰慄問她。
「她的叔叔是這夏天選舉的市長候選人其中一位,你知道吧?我認為蛇蜷把很多投資放在捉到她這件事上,我想到,也許他綁架黛娜是要用她勒索那位叔叔的競選資金,或者以更直接的方式,讓她叔叔退出競選。我有懷疑他會使用某種激勵法讓她合作。他搞清楚她在家裡不開心,給了她一個地方待,再加上某些賄賂。不管怎樣,這都和他一直以來的方法都很相近,作風也會更偏短期或更親切。不怎麼壞呢。」
「妳猜的有些誤差。」我苦澀地,說道。
「我也有意識到啊。」媘蜜回答,她嗓音中充滿著情緒。「我也不喜歡那麼幹。他在我身邊夠久,也和我夠多交流,讓我產生自己不必知道或思考細節的想法。我甚至連她有超能力或蛇蜷發現這件事、發現她,全都不知道。這對他來說很出格。無情,對權力飢渴。」
「假使這事讓妳那麼心煩,就叫他滾蛋啊。」母狗插話,聽起來很煩躁。
「這比那樣複雜。」我說「我們不能直接離開,然後讓她像那樣待著。」
「而且我們也有人在要緊事上有點依賴蛇蜷。」戰慄說。「我們一些人,有著不能拋棄的人。」
我看向他,相當驚訝:「我不想說妳的妹妹不重要,可是……你真的願意只為了愛紗,就讓黛娜被綁架?」
「假使我要決定?是啊。」
我瞪向他。
「我很實際,泰勒。」戰慄失語,說出我的真名:「全世界到處都有人在受苦。我們每一天每一秒鐘都無視別處發生的事情,只專注於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城市,我們的社區,或者是我們每天會見到的人。我們只會真心在意我們所愛之人、朋友和家人的痛苦與不愉快,因為我們沒辦法在試圖支援、拯救所有人時維持理智。沒有人能做出這種事情,可能賽陽是例外。我也把這個概念運用在更小規模。我的家人和我的隊伍會優先,也按照順序分配優先次序。假如我一定得在兩個之中選一個,我會選擇包含愛紗和你們的選項。」
「這和無視第三世界的飢餓孩童,或者是無視街上無家可歸的人,都不一樣。」我對他說:「你親自見過黛娜,你也直接看進她的雙眼。你已經參與在其中,你在她的狀況裡扮演了一個角色。」
「我不是說我喜歡這件事,我現在,肯定更不確定自己要與蛇蜷工作,但我說,這是我們應該討論並獲得共識的事。」
我看向其他人:「你們也有一樣的感覺嗎?」
母狗氣惱地看了我一眼。好吧,我不期待有她的支援。
攝政聳了肩:「我告訴過妳我的家庭、我長大的方式。我之前看過類似的東西,不過是我爸的超能力,而不是毒品。我對這種鳥事容忍度很高。」
我試圖說服他:「你離開碎心漢不正是因為這種事情嗎?你和蛇蜷,不就是回到同樣的狀況嗎?」
「我離開我父親是因為他在試圖控制我,然後強迫我成為某個我不是的人和東西。那樣連一丁點有趣或樂趣都沒有。當蛇蜷做出那種事的一天,我就會離開他。以現在來說,還滿好玩的啊。」
我和這種人有關係嗎?我看向我最後的備胎和支援。媘蜜。
她將雙手拇指勾住腰帶,她的雙肩往前駝背了一點,將背抵住牆壁。看起來不怎麼開心。
當她與我雙眼相對,她細微搖了下頭。
「蛇蜷並不愚笨。」媘蜜對我說:「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有任何理由懷疑我們隊上的一兩個人認為他的辦事方法很令人不愉快。他計算過這種事了。他在測試我們,確定我們在要做出艱難抉擇時,會留下來。」
「假如這是場策略。」我說,感覺心一沉:「我認為我失敗了。」
「別這麼說啦。」媘蜜說。「戰慄是對的,我們需要作為一個團隊討論這件事。」
「討論什麼?要不要留在蛇蜷那?」
「對。」這個詞和半聲嘆息一起從她嘴中吐出。
「你們甚至認為那是可以商談的事,這真的滿糟糕的。」我回應。我感覺到的憤怒和背叛,讓我的語調變得更加、更加苛薄。
我不知道自己期望什麼,可是我站在那了幾秒鐘。也許我在等待一份道歉,或某種藉口,或是從他們口中坦承說我是正確的。
他們沒有人再次開口說任何,這些話語。
我轉身離去,將艙門推開,踏上環繞大廈建築工程周圍的碎石地。
「泰勒別這樣。」戰慄在我身後喊了出聲。我沒有聽從。
「喂!」他拉高了聲音。
我沒有回應。我太憤怒,也和這話聽起來一樣智障的是,我不想要我們離別語是我在咒罵他。
我走出艙門三步時,我聽到身後有踩上碎石的聲音。我轉過身看到戰慄走近,一隻手伸了出來,就好像要抓住我。
我的脾氣和蟲子同時爆發,蟲子從我假面裝底下噴出來。在我的指示下,它們掃過戰慄和我之間,創造出某種屏障。
我已經在想自己該怎樣處理可能爆發的戰鬥--他假面裝覆蓋了皮膚,可是我記得他面具邊緣的通風孔,那東西將他的黑暗從他臉上,重導出面具邊緣,所以那個骷髏圖像便脫穎而出。在緊要關頭中,我的蟲子能穿過那個裡爬進去。他的超能力不會真的影響我,可是蟲群細流跑進他的面具,可以抵銷他明顯的近身戰鬥優勢嗎?
我聽到母狗的狗兒們在低嚎。他們並沒在最大尺寸,可是他們比普通的狗更大,被鎖定在牠們變身的起始階段。在微光照耀的施工區域裡,我能透過朦朧蟲群看見牠們的影子。如果處理掉牠們並非可能,也會相當困難。
「別。」戰慄在蟲群的另一側,說道。「幹。讓她走吧。」
我轉身逃跑。
■
閣樓很空蕩,只有安潔力卡在這。她身後,電視沒被關上,低吟的背景噪音和活動讓那隻狗放下心,也許是這樣,不然就是艾力克手懶沒把所有東西關好。
安潔力卡從沙發爬下的動作十分緩慢,她接近我,調查我的狀態。不管她過去經驗是什麼,她從未學過要喜歡母狗以外的任何人類,所以我只得到了個粗略的嗅聞,她便蹣跚回到沙發。不管她花非多少能量接近我、調查我,然後回到她剛才休息的位置,這沒給她留下足夠的力氣跳上沙發。她安頓在咖啡桌底下,用她那隻無傷的眼睛看著我,永遠都在眨眼,就好像眨眼能變得讓她機警或威脅人。
迷霧人對她造成不少傷害。這很難讓人相信,可是她已經比幾天之前更好了。母狗希望把她的能力用在這隻狗上,可是莉莎提出反對建議,警告了心肺功能靜止的威脅。結果,安潔力卡花費了大半星期昏睡、虛弱、完全沒動,讓我好幾次看向她時,都懷疑她是否停止呼吸。我沒有太與她親近到她死去會讓我傷心的地步,但知道失去一隻狗讓母狗有多沈痛,令我有足夠理由擔心那牲畜。
想著自己要離開這一切,感覺真奇怪--這間閣樓,狗兒們,還有其他人。
我不知道該如何解析自己的感覺或思緒。我感覺很生氣、被背叛。站在閣樓的客廳裡,迷失感也特別激烈。我沒了計畫,而現在有一陣子我都還有計畫。我高中第一年半一直都是過一天算一天,過一週算一週。當到了週末,也都是在恢復,重建我的精神、情緒力量來面對下一週。
然後我有了超能力。我接觸了最終極限,那就是我可能崩潰的時候,而超能力也給了我某個奮鬥的目標--成為超能英雄。那時還有好多事情要做,有好多計畫、預備和研究,給了我生活的理由。我之前猶豫是否要將其定義為希望,不過這確實給了我一些集中注意力超過二十四小時的東西。
每個東西都從那個點開始流動。遇見暗地黨,幹下一份作為間諜特務的新計畫,還有要得到他們的情報、知曉他們當時不知名的老闆,這些新目標。當我不能抱著良心執行計畫時,我換了計畫要認識他們,成為母狗的朋友,與布萊恩交流感情。我承認,我有好幾次某種程度上的成功,短時間內我也穿過了那條界線,但對現在來說,也足夠多了。
現在我正漂流。
我是,以某種方式,回到原點。我必須撐過今天,然後撐過這週。我會搞清楚從這之後要到哪去。我前往了我自己的房間。
我的後背包座落在床頭桌旁,迅速調查就能發現桌上依然有很多我一週前堆放的東西,也是在我預計要留在布萊恩家幾天時的物品。有衣服,盥洗用品,紙鈔,和一個沒用過的即可拋手機。我加上了更多錢,和留著我的超能反派銀行帳號訊息的卡片,以及一些其他東西。我確認自己認為可能需要的空間,發現我正在看著梳妝櫃。在桌面最上方的是一把我其中一場戰鬥的武士刀戰利品,還有那片布萊恩給我的琥珀。
我將琥珀塞進背包裡,用衣服墊著包裹起來,接著再把背包拉鍊拉上。
鬧鈴顯示出,現在時間是早晨六點四十分。假使蛇蜷沒在這個奇怪的時間打電話要開會,假使我沒有打包行李,這就會是我出門晨跑的時間了。
我就這樣,趕緊在其他人趕上之前離開,我會留下很多東西。衣服、家具、照片。而我完全沒想到,自己有點開始將這裡當作屬於我自己的空間,開始裝飾、個人化。我以一種,在自己仍計畫要背叛這隊伍時所沒有過的方式,住了進來。
我在假面裝上面穿了衣服時,莉莎的嗓音從走廊上傳來:「妳要去那?」
我轉身看向她,她表情變了。那是我臉上的神情嗎?我不確定自己正傳達的情感。憤怒?沮喪?懊悔?
「也許,住旅館吧。」我說。「幹嘛?你們要捕獵我嗎?收拾掉未了之事?」
「妳知道我們不會那麼做。」
「當然。我確定他如果選擇那條路線,就會派行旅人追殺我。」我將面具扯下,把它放進後背包裡。
「這讓我感覺很不好,泰勒。妳真的得走嗎?」
「我現在在鏡子裡連自己都不想看見。就算我們有某種協議,一起計畫把她救出來,對付蛇蜷……」我偏題,試著找到一些詞彙:「我沒辦法面對所有其他人,他們假裝世界很普通。即使我們努力要拯救她……這感覺還是很不尊重人。黛娜值得更好的。」
「不管妳相不相信,布萊恩都和妳一樣驚慌。如果他表現得很奇怪或是很不像他自己,那只是他回歸到自己的核心處理方式,妳懂我的意思嗎?就像母狗變得生氣,或者妳變得安靜又擔憂。」
我聳了下肩膀,把汗衫綁在我的腰間,對她說:「回頭來看,我不認為那不會不像他。那也是一部分我要離開的原因。」
「是要永遠還是暫時離開?」
「不知道。」
「妳會做某些蠢事,像自己跑去救黛娜嗎?」
「不知道。」我重複了自己的話。
「妳知道有個不太可能發生的機會,假使妳這樣嘗試,我們可能得試著阻止妳。要看我們其他人在現今狀態下,同意了什麼。」
「就做你們得做的吧,我也會一樣。」
「那就,好啦。」
我把背包甩過我的肩膀,面對房門。
媘蜜說:「我不會說再見,因為這不是別離。如果是為了我們能在可見未來中,可以有一場文明交談,必須的話我會自己解決和蛇蜷的,還有他的肉票問題。活下去,別太衝動,然後以後也放開心,聽聽我們的想法吧?我們的友誼至少值得這些吧?」
在一段時間後,我朝她點了一次頭。
莉莎從門口移開,讓我通過。當我轉身朝向客廳和階梯走去,莉莎幾乎刻意轉開臉,走向廚房。就好像,跟著我走到出口就會變成某種模糊意義的別離,她則堅持那個拒絕道別的點子。
我在前往一樓樓梯的半路時,就聽見了。一聲哭號噪響--就像你可能在特大號的嬰兒準備尖叫時會聽到的那種聲音。鼻音的「哇」音被拉長,響亮得光聽都讓人痛苦。警鈴?是空襲警鈴。
我折返跑回上樓梯。媘蜜已經在客廳裡。電視正展示輪轉圖樣的疏散指示:請離開你的家裡。找到最近的避難處。遵守當局指示。請離開你的家……
「炸彈。」我問道,把聲音提高過於警鈴:「爆彈留下了東西嗎?」
莉莎搖了搖頭。
我看到過她在竜面前,在榮耀女孩、爆彈、純潔、深夜和迷霧人周圍。我現在看著她,卻見到她臉上的表情,我在這些狀況中從來未見過。沒有絲毫她那詭計多端的微笑,也沒有她那有個性的幽默或魯莽狂放。
「那麼又是什麼?」我問她,不過我已經猜到了一個灰暗的想法。就連爆彈對付這城的恐怖主義活動也沒有讓警鈴響起,這樣就只剩下了少數幾個可能性。
她的回應只有一個詞,結語道。「終結召喚者。」
「什……但……」我轉向階梯,接著右轉面對媘蜜:「我爸。我得……」
媘蜜打斷我:「他會跟其他人一樣疏散或是去到一個避難所。泰勒,看著我。」
我照做了。
「其他人還有我,我們聊過這個可能性。這話題是在我們遇到妳之前。妳有聽到我說話嗎?妳知道會發生什麼,有通常的反應措施。」
我點了頭。
「我們全都決定了我們會出動。我們會試圖幫忙,做我們能做的。可是妳不是那談話的一部分,而且隊上的緊繃。妳現在差不多不在隊上了,所以如果妳不想要……」
「我會出動。」我甚至想都不用想。如果我此時離開,知道有自己能幫上忙的事,我絕對不會原諒自己。
#母狗 #布魯圖斯 #戰慄 #猶大 #攝政 #媘蜜 #泰勒 (#安潔力卡)
ns 15.158.61.11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