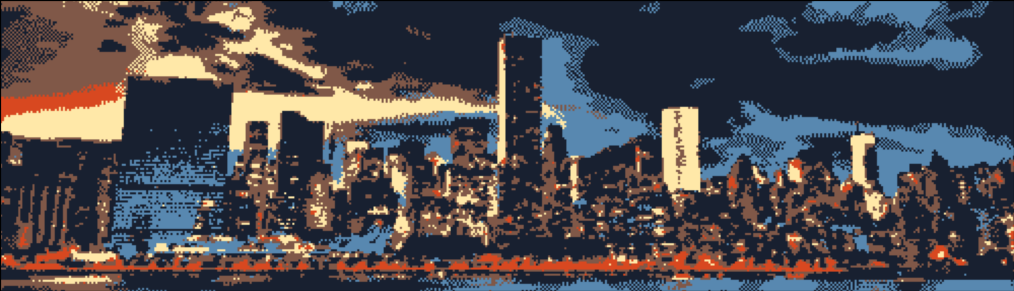 x
x
攪亂 3.1
星期二早晨第一件事,我又去跑步。我在平常的時間起床,因為沒辦法和我爸吃早餐而道歉,然後出門,拉起汗衫的兜帽藏住我沒梳理好的頭髮。
城市還未清醒前出門,有某些吸引人的地方。我通常沒這麼早出門,所以這是個滿新奇的轉變。我輕快慢跑跑向東側時,街上沒有行人也沒有車。時間是早上六點半,太陽才剛升起,將影子拉長。空氣以涼到讓我的呼吸化為霧氣。彷彿布拉克頓灣成了鬼城,但是是好的那種。
我的訓練制度是每天早上跑步,午後則在跑步和其他運動之間間接穿插,要看當天是星期幾。主要的目標是建立體能。在二月時有一次索菲亞唆使了一些男孩來試著抓住我,我想她目的是要把我用膠帶綁在電話線杆上。我逃了出來。事實上大部分男孩們沒在意她到要認真追上我,這幫了我不少忙,不過我發現自己只跑了一個街區後便氣喘如牛。這響起了警鐘,在我開始想穿假面服外出時提醒了我。不久後,我開始訓練。間間斷斷地,我在這一個日常慣例中安頓了下來。
現在,我更健康了。之前我沒辦法說自己很重,還有著輕微的凸小腹、平胸和竹竿瘦的手臂雙腿的不幸組合。這加總起來讓我看似隻被強迫用雙腿站起來的青蛙。三個半月燒掉了體脂肪,讓我非常精瘦,還給了我穩步慢跑也不會大喘的耐力。
不過,我沒只想慢跑。朝向海,每跑過一個街區,就穩定地加快步伐。到了第五個街區,我已全力奔跑了起來。
我大致的方法是不要太在意里程或測量計數。那樣會讓我感覺,從我自己身體的意識和身體極限轉移了注意力。如果感覺太簡單,我會強迫自己比前一天跑更遠一點。
我跑的路線每天都有變化--正如我父親所堅持的--但我通常都會跑到同樣的地方。在布拉克頓灣,一直走向東會領你到一兩處。不是碼頭,就是到百行大道。因為大部分碼頭區域不是能單純輕鬆通過的地方,考慮到遊民、幫派成員們和普通的罪犯,我維持在大路上通過碼頭到百行大道。通常我跑到過羅德街的橋時,時間接近七點。從那裏開始,就是到百行大道的街區。
我在人行道末端、木頭平台開始的地方慢了下來。雖然我雙腿正痠痛又喘不過氣,我強迫自己維持著緩慢穩定的步伐而不是直接停下來。
百行大道上,人們正開始他們的一天。大部分的地方還沒開店,有著最頂級保安系統,鋼鐵百葉門和金屬大門保護著所有昂貴的店家,但咖啡店和餐廳仍開著。其他店有貨車停在前面,忙著裝卸他們的貨物。只有一些人在外頭,所以我很容易就能發現布萊恩。
布萊恩靠著木質扶手,遼望著海灘。有包紙袋和裝著四杯咖啡的卡紙板杯盤在木扶手上平衡擺著。我在他身旁停了下來,他帶著大大的微笑和我打招呼。
「嗨,妳真準時。」布萊恩說道。他看起來比起我在星期一看到他時不太一樣。在毛氈夾克底下穿著汗衫,他的牛仔褲上沒有任何破口,還有他那雙靴子擦得閃亮。星期一時,他給我一種普通生活在碼頭的人的印象。今天,他穿的時尚、合身衣服讓他看起來像,屬於在百行大道低消一百元的店購物的消費者身邊的人。這樣的反差和他表現出的輕鬆,讓這轉變令人吃驚。我對布萊恩的評價又升了一級。
「嗨。」我說,因為花這麼長的時間回應而感覺一抹尷尬,然後又因為在他身旁穿得不夠好而心裡隱隱作痛。我沒預想他會穿得這麼好看。我希望自己喘不過氣能是個夠好的延遲回應的藉口。而對於感到自己穿得不夠時髦,什麼都沒辦法作。
他指著紙袋:「我從在那裡的咖啡店買了甜甜圈和可頌,還有咖啡,如果妳想吃的話。」
「要吃。」我說,馬上覺得這退化成山頂洞人的尷尬對話很蠢。都是因為早晨的錯。為了挽救面子,我補充道:「謝啦。」
我拎出一個糖粉甜甜圈,咬了一口。我馬上能分辨出這不是,在某個中央廚房工廠大量製造,隔夜運送到商店在早上烘焙的,那種甜甜圈。這很新鮮,大概是一個街區外的那家店,剛出爐拿來賣的。
「好吃。」我說,吸吮指頭上的糖粉後伸手拿了杯咖啡。看到杯子上的商標,我抬頭看向咖啡店然後問:「那裡的咖啡不是賣,大概,一杯五十元?」
布萊恩輕聲笑了下:「泰勒,我們付得起的。」
我花費了一秒鐘理解這概念之後才連起線索,覺得自己像個白癡。這些人每個差事都坐擁數千元,而且他們還直接給我兩千。知道那筆錢是怎麼來的,我便不願意花那個錢,所以它就留在擺著我的假面服的小空間中,如芒刺在背。我也沒辦法在承擔必須解釋原因的前提下,告訴布萊恩我沒花那筆錢。
「是啊,我猜是吧。」我最後如此說。我手肘靠著木頭欄杆,在布萊恩身邊,開始凝望著海水。那裡有幾個死忠的風帆衝浪手正準備開始他們的一天。我想這滿合理的,因為等下偶爾會有船出海。
「妳的手怎麼樣了?」他問。
我伸展我的手臂,握拳,然後放鬆:「只有在我彎曲時才會痛。」我沒告訴他,昨晚我手痛到沒睡好。
「我想,在我們把縫線拿出來之前,會讓它留個差不多一週。」布萊恩說:「妳可以去找妳的醫生然後讓他來做,或者來我的地方讓我來處理。」
我點了頭。一陣鹹水和海草味的風將我的兜帽吹到背後,我花了一秒將頭髮從臉上撥開又戴回兜帽。
「我很抱歉瑞秋還有昨天晚上那整件事。」布萊恩說:「我想更早些和妳道歉,但又想到,在她能聽見我們時提起這事,會是個壞點子。」
「還好啦。」我說。不確定是否真的還好,可是那真的不是他的錯。我試著將自己的想法換成言詞:「我想……好吧,我猜我從穿上那套假面服的時候起,就預想人們會攻擊我,所以我不應該感到驚訝,對吧?」
布萊恩點頭,但沒有說任何東西,所以我補充:「那個攻擊來自於應該是我的團隊的某人,有點讓我來不及招架,但我還能接受。」
「就讓妳知道下。」布萊恩告訴我:「只從妳昨晚離開後,今天大家早上起床,我看瑞秋貌似沒再像之前那樣大聲抗議或質疑新成員加入了。她仍然很不高興,但我想如果那種事重複發生的話,我會很驚訝。」
我笑了,有一點太突然也比我想要的音調還高:「天吶,我希望不會。」
「她是有點特殊的案例。」布萊恩說:「我想在她那種環境下成長,把她毀了。沒有家,年紀太大,呃,作為一個領養候補又不夠吸引人。這麼說有點不好,但那就是那種事情運作的方式,妳懂嗎?」他轉頭看了我一眼。
我點頭。
「所以她花了足有十年在寄養家庭裡,沒有固定地方生活,甚至和其他寄養兒童為了最基本的奢侈和所有物又抓又咬地打架。我的猜想?是她在她得到能力之前就壞掉了,然後還有事情那樣發生,她的能力逼迫她進入反社會水窪的最深處。」
「很合理。」我說,然後我補充:「我在維基上讀了她的頁面。」
「那樣妳就大概瞭解了。」布萊恩說:「她的事情很難處理,就算對我來說也是如此,而且我想她真的將我看作個朋友……或者,不管怎麼說,至少是個她能有的朋友。但如果妳能最低限度容忍她,妳應該能看出我們隊伍的默契還不錯。」
「當然了。」我說:「不管怎樣,都會試試看。」
他對我微微一笑,然後我低下視線,有些尷尬。
我發現一隻螃蟹急跑過差不多在我們正下方的海灘。我延展我的能力把它半路停了下來。雖然我覺得不需要,還是伸出的手指指向它,慵懶地來回擺動讓螃蟹跟著我的食指所指的位置跑。因為布萊恩和我兩人都靠在欄杆上,然後周圍實際上全沒有人在百行大道上不忙著工作或準備開店,我十分確定沒有其他人會發現我正在做的事。
布萊恩看到螃蟹繞圈和八字跳舞,微笑了起來。就像密謀一樣,他傾身靠近我低語道:「妳也能控制螃蟹?」
我點頭,這樣緊靠在一起的方式讓我感覺有點刺激,人們圍繞我們,卻又毫不知情我們之間共享著秘密。我告訴他:「我曾經以為我能控制任何有外骨骼或殼的東西。但我也能控制蚯蚓,還有其他東西,都沒有殼。我想這需要的應該是具備非常簡單的腦袋。」
我讓它繞圈和數字八一段時間,然後把它放走做它的事。
「我該在其他人開始找我之前帶早晨咖啡去。想要一起來嗎?」布萊恩問。
我搖了搖頭:「我得回家之後要準備去學校。」
「啊,對。」布萊恩說:「我忘了還有那種東西。」
「你們不去上學嗎?」
「我有線上課程。」布萊恩說:「我家人以為我有個能付的起公寓的工作……這方面是真的。艾利克輟學了,瑞秋從來沒去過,還有莉莎已經申請然後測試過了她的GED【普通教育開發,學力等同高中】。用她的能力作弊,但她通過了。」
「啊。」我說,我的注意力多少集中在布萊恩有個公寓的想法。不是作為戰慄,一個成功的超能反派有一個公寓--莉莎曾經對我提過了--而是作為有父母和學校作業青少年來想。他不斷改變我的參考架構來瞭解他。
「這,是個禮物。」在他伸手從他口袋裡拿出東西遞給我時說道。
我對另一個得接受禮物的想法感到一陣恐慌。他們給我的那兩千塊對我良心來說已經夠重了。不過,如果我不接受的話依然不怎麼好看。我逼自己伸出手在他的手下方接受禮物,他將一把掛在串珠鏈的鑰匙放在我手掌上。
「這是我們的地方。」他和我說:「而且我是認真的。我們的也是妳的。妳任何時候想來都行,就算沒人在也一樣。躺沙發看電視,吃我們的東西,在我們的地板上留下腳印,對其他弄髒地板的人吼,什麼都可以。」
「謝謝你。」我說,對自己的誠心說詞感到驚訝。
「妳要在放學後過來,或者我明天在這裡和妳見面?」
我想了一秒。昨晚在我離開前,布萊恩和我聊了我們的訓練。當我提起我晨跑時,他建議我定時見面。這是為了讓我隨時更新消息,因為我不像莉莎、艾利克和瑞秋那樣住在團隊的安全屋。這很合理,我同意了。在團隊中的所有人裡面我最喜歡布萊克也完全不妨礙。不知為何,他很容易相處。這不是說我不喜歡莉莎,但在她週圍讓我感覺如坐針氈【原文在這裡用了比較接近「如大難將臨」的典故】。
「我之後會過去。」我大聲地決定道,知道如果我不用某些方法做出保證,我可能會被嚇溜走。在我們能又開始聊另一個話題前,我很快地和他揮手然後開始往回頭跑,拳頭緊握住他們的地方的鑰匙。
往回家之後,得準備去學校使我逐漸感到憂懼,彷彿鉛塊坐落在胸口。我試著不去想艾瑪的嘲笑,還有我從學校臉上帶淚逃了出來。我早上花了一、兩個小時在床上打滾,那天的事件在我腦海裡重複播放,同時在每次我開始朦朧入睡手腕的震動疼動便將我拉回來。除此之外,我相當成功不去想那件事了。雖然現在那個必定發生的事隱約逼近,準備搭上公車回家時,沒可能老是在想那件事。
我沒辦法讓自己不整天思索。我仍必須面對翹掉兩個下午的後果。那倒是滿嚴重的,尤其是因為我錯過繳交美術作業的最後期限。我想到那份美術作業還在我的背包裡,而上次我見到自己的背包是在索菲亞踩著它,得意地對我笑著時。
還有蓋德利老師課堂的問題。那通常就已經夠糟了,麥迪森在班上,而我和史巴奇、葛列格這樣的人同組。知道我必須坐著聽蓋德利老師教書,還是在我曾看到他在我被霸凌時,露骨地轉身丟下我……這更糟糕了。
這不是我第一次必須鼓舞激勵自己去學校。欺騙自己出門然後留在學校裡。最糟的日子是在我高中第一年時,艾瑪背叛給我的傷害仍然新鮮,而我仍未有足夠經驗預測她們想出的各式各樣的東西。那時,回到一月中,她們徹底把我嚇慘了,因為我還不知道得怎樣預期。我花了一週在醫院,受到精神病觀察,而我也知道其他所有人都聽過這故事。
我從窗戶注視巴士外,看著人們和車流。像這樣的一天,在被公然侮辱後,讓我自己到願意走出門,和自己做約定,然後展望在學校結束之後的日子。我告訴自己,我會去到納特老師的電腦課,那三人組不會在那,通常來說比較輕鬆,然後我也能花時間上網。從這開始,就只是說服我自己走過走廊到蓋德利老師的課堂。
只要我這樣做--我承諾自己--會給自己獎勵。午休時讀本我留下來要看的書,或在放學後去店裡買一份罕見的點心。為了午後的課程,我無可避免想到其他某些能期待的東西,像看個我喜歡的電視劇或繼續做我的假面裝。我想,或者,也許我能期待和莉莎、艾利克和布萊恩一起出去玩。撇開我幾乎被母狗的狗抓傷的部分,昨晚還不錯。吃泰國菜,我們五人懶洋洋靠坐在沙發上,用個帶有環繞音效的巨大娛樂影音系統看了部動作電影。我沒忘記他們是誰,但我沒理由對只是--不管從任何意義上說--一群聚在一起的青少年的我們有罪惡感,我這樣對將自己的決定合理化。此外,這是為了正當原因,如果這讓他們在我週圍放鬆,然後也許會吐露更多祕密。對吧?
在我下公車時,兩本舊筆記拿在一隻手裡,我剛才將所有事情記住。我能在納特女士的課堂上放鬆,然後就只是必須坐過九十分鐘的課程。我突然想起,也許,我能試著找我的美術老師在午餐休息時間談談。這代表要避開那三人組,然後我也許能讓她接受另一份作業或至少不要得鴨蛋。我的成績好到我大概能在期中零分的前提下成功通過,不過,這依然會有幫助。我想做得比及格更好,特別是考慮到我必須面對的這些爛事。
納特女士和我差不多同時到教室,開門讓我們魚貫而入。
五十個學生的最後一人抵達時,我在人群的最後面。在我等著有足夠的空間進門的時候,我看到索菲亞在和三個課堂上的女孩說話。看起來像她剛結束田徑訓練。索菲亞有著黑皮膚和長及背部的黑髮,不過她現在綁著馬尾。我沒辦法不去怨恨,她就算滿身大汗、沾著灰塵,是個惡名昭彰的婊子,大概每個學校的男生依舊會選她而不是我。
她說了些東西,然後她們三人都笑了。我知道,就算理性上而言,我大概不是她們會聊的話題的前五項,而她們很可能沒在講我的事,我感覺自己的心沈了下來。我跟著擁擠的同學們等待進門,斷開我自己和她們之間的視線。這沒什麼作用。在一些學生進了房間後,我看到索菲亞正看著我。她做出了個誇張的噘嘴生氣的表情,以她指尖從眼角劃下她的臉頰做出一滴嘲笑的淚。其中一個女孩注意到便笑了出來,在索菲亞對她耳邊低語時靠近她,然後她們倆都笑了出來。我的臉頰因為羞辱而脹紅。索菲亞最後給我得意一笑,然後轉身從容離去,同時其他女孩跟著排隊進教室。
就算像我已如此自責,我轉身通過走廊朝學校前門去。我知道明天會更難回來。一又四分之三年以來,我一直要面對這鳥事。我逆流而上這麼久,而即使我雖理解了,如果不斷像這樣蹺課會有我必須面對,的後果停止逆流對抗,單單朝其他方向走,會簡單得多。
我的雙手插在口袋裡,已經有一種矛盾的放鬆感,我搭上巴士前往碼頭。
ns3.129.206.232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