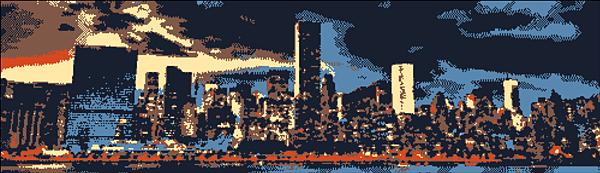 x
x
Disclaimer2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SfU2sYcsNN
【原作者贊助連結】
媘蜜站在地板最邊緣上,她面對著二十五層樓的高空。大風吹甩著她的頭髮,而她完全沒有一個扶手處能抓。碎歌鳥很久以前就已經清除掉所有窗戶。
她放下自己的望遠鏡。「他走了。如果他要幹出某些事情,他就會想來看,確保所有所有事情都毫無差錯。」
「我可以跟他們一起走。」淘氣鬼說。「偷聽他們說話。」
「在我們不知道他們每一個超能力時,就不準那麼做。」媘蜜說。
淘氣鬼交疊起雙臂,嘟著嘴。「我還以為妳會比較酷欸。」
「奧賽羅是隱陌型能力者。」媘蜜說。「我認為他有一個想像朋友能亂搞我們,但我沒看到任何隱形的人四處走動的跡象。」
「那不就是隱身的重點嗎?」攝政問。
「沒有塵埃或玻璃被擾動,什麼都沒有。我認為,他的『朋友』可能會隱身,卻沒有實體,但那就很沒意義啊?和議人通常都有很強的超能力者。檸水晶,我能搞清楚的少部分是,她具備攻擊性的能力,某些跟物質相關的東西,她的焦點都擺在很奇怪的地方。她比較關注房間裡最強的力量聚集的每一個地方,除此之外就相當毫無章法地專注在所有地方了。她的超能力,若不是這裡任何人都無法抵抗的類型——像剪彈的箭,或某種能被控制的擦除者光波——就是制能型。」
「制能型是啥?」攝政問。
「官方分類是,可以臨場獲得新超能力的假面。」媘蜜指著戰慄:「可以跟其他無法被分類的超能力互動,或是將超能力無效化。」
「那麼,她就很強了吧。」攝政說。
「她表現得像是自己很強。」媘蜜說:「她八成是很強。但我們拿到的PRT資料庫沒有他們任何一人的資料。我不知道他怎麼找到他們,但和議人都有收集到一些超強的打手。」
瓷偶打破了自己的沈默。「妳說得一直像是,我們會跟他們戰鬥。」
「威脅評估。」媘蜜說。她回到自己的座位旁,坐在長桌上。「不知道我們會遇到什麼樣的人,特別是在他那種人跟我們對立時,就會很蠢呢。」
「更不用說,我們幾乎要跟所有想住在灣城裡裡的人打架呢。」攝政評論。
「沒什麼緊迫的威脅。」戰慄說。「先專注在更近期的問題上。」
他將注意力轉向我這邊。
「我?」我問?
「他說得對。我們一直忙著預備處理可能的事後餘波,都沒時間討論這件事了。」媘蜜說。
「我不會有所影響了。損傷已經造成,問題只有塵埃什麼時候落定。」我說,盯著手套。我做了些假面服的改動,但真正的調整得等我有時間後才能開始。我特別在地盤裡分出一片空地來織額外的衣服,但我今晚沒有時間將其做成可以穿的東西。面具的某些部分、裝甲跟手套的背後部分都改得更有流線形——在不同的角度下,也可以說是更沒有流線感了——線條更銳利,凸面裝甲板會更向外展開,手套有更多銳緣,讓我在必須肉搏時能造成更多損傷。
我只改了一些裝甲,假面服好幾處都已經破爛不堪。手套、面具跟裝甲後背,通常都會承受最大的傷害。我之後才會更新其他部分。
「我不確定事情有那麼簡單。」戰慄說,嗓音沈靜。他伸手越過桌面,抓住我的手,緊緊握著我的手。「得再三確認他們有燒掉我們哪些退路吧?我父母周圍還沒出現任何干涉的跡象。」
「媽不可能更不在意啦。」愛紗說。「她若能弄到錢,就會想利用這些焦點上電視吧。」
「是啊。」戰慄同意。
「我家人不會在意的。」媘蜜說。「如果他們沒已經知情的話,我會很驚訝呢。我敢賭他們選擇忽略事實。瓷偶?妳已經照顧好妳那一邊了吧。」
「我大部分親人都死人。那些還沒死的人也都已經知情了。」瓷偶說。她看向窗戶,看著那在夜空下的城市亮光。
媘蜜點頭:「來看看⋯⋯瑞秋不成問題,沒什麼區別。從來都沒有秘密身分。」
瑞秋聳肩。她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狗群上。他們正在縮小,額外的質量被蛻下。她已經讓雜種坐在自己身旁,他的皮毛刺起,在轉變過程中變得潮濕。
「他們想透過我的家人來搞我,他們就會自食惡果。」攝政說。
「為什麼?」瓷偶問。
「他爸是碎心漢。」媘蜜說。
「喔。喔哇噢。」
「好笑的事情是,」攝政說:「如果妳認真想一想,我們現在可能比碎心漢強喔。全美的人都知道我們是誰,我卻不確定南部或西部的人會不會知道碎心漢。」
「先專注於現在。」戰慄說,壓一下我的手。「我們開始談保險跟損傷控制,這樣很好,但美國其他反派的話題可以暫緩。他們是在掠翅沒穿假面服的時候,來攻擊她。」
「妳感覺怎麼樣?」媘蜜問,向前靠在桌面上。「妳今晚出手滿重的。我們確實是有討論過了,但我以為,妳至少會假裝跟他們玩玩啊。」
「我不需要超能力直覺也能理解,不論我說什麼他們都不會合作。」我回答。
「但妳是在刺激他們啊。特別是華利弗。妳會分心的話,還要這麼做嗎?」
「我就只剩這個了,不是嗎?好人決定打出他們最強的牌。他們無法擊敗掠翅,就要擊敗泰勒。就我所想,沒理由不將我自己擺上牌桌,全心處理英雄跟反派那兩邊。我會設下法律,因為現在我有時間可以執法了。我會對當地反派更嚴厲,如果他們開始找碴,我就會支援你們,我剩餘的時間則會花在我的地盤上。」
「這條路很危險喔。」媘蜜說。「妳會需要休息、修養啊。」
「然後呢?去看電影?我不確定有沒有電影月開張⋯⋯」
「已經有開張了喔。」媘蜜說。
「⋯⋯而就算有開,我也沒辦法去啊。我的臉被貼在新聞各處上,還有個巧匠可能在看著城裡每台電腦的系統、監視攝影機,因為她不願意反對自己的老闆。我不能去血拼,也沒辦法離開我的地盤,除非我有穿上假面服、預備要戰鬥。」
「也有更多時間打回去啊。」攝政說。「妳不能放過這件事的。」
「我也沒計畫放過他們。」我說,從座位上起身。
「等等。」戰慄在我將手抽回時,說。
「跟我走走。」我說。「大家一起來。這座城市也許有在改善,但這棟建築裡應該沒有燈光——其中一位當地英雄決定來一探究竟,就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我們可以帶他們一起走。」瑞秋從隊伍後方,說。
「當然可以,我也會想帶上他們。」我說,走到樓梯上。「我們自己來決定,不由他們決定交戰的時間。」
「已經有夠多敵人了吧。」瓷偶說。她得加緊腳步,繞過桌子趕過來。「我們不需要更多敵人啊。」
「我也同意。」戰慄說。「不是說我不理解某些回應的必要性,但妳這是在要挑釁他們啊。」
「我感覺是很挑釁呢。」我說。「我是這麼想。我不知道。感覺很難描述敵人。」
「最好等到妳可以更理解妳的感覺之後,再來決定吧。」戰慄說。
「那不重要。」我說,走下階梯。「邏輯上來說,行動以外就沒有其他選擇了。你聽見華利弗說的。在我們回應PRT以前,反派社群就不會尊重我們,而所謂的好人,也不會有理由認為他們不能再做一次這種事情。」
「我們其他人都沒有妳那麼脆弱啊。」攝政說。「我不想表現得太不尊重人之類的,但我們沒有那一種平民生活需要保護。」
「還有其他人。」我說。「我們會遵守這些規則的部分原因,是因為這會創立先例。其他反派遵守規則,我們都能獲利,而相反來說也是正確。」
「反過來說,」媘蜜說:「我們就是在冒險讓衝突升級。」
「我看不出怎麼會升級呢。」我說。「依我看,他們已經打出做後一張牌了。我們現在更沈重打擊他們,外部人士就更能清楚看到PRT沒有答案。我可以展現出,這並沒有讓我心煩,而效果也一樣。」
「不過,真的沒有嗎?」媘蜜問。「這真的沒讓妳心煩?」
「是啊。」我說。「就我來說,我不知道。我沒辦法確定這種做法是否有正當理由。但他們還是弄了我爸。」
「我懂的。」戰慄說:「如果他們去搞愛紗,我也會很不爽。老天,妳懂的,在我被愛剋妲娜吞下去的時候,她就在我腦袋裡塞滿了所有我能想到的,最糟糕的東西、被剪接的記憶,那都⋯⋯」
他住了口,我頓止腳步,回頭仰望階梯上的他。
「哥?」愛紗問。
他花一秒鐘冷靜下來,然後說:「泰勒,我理解妳的意思。相信我。我有被埋在其中。假如這裡有人知道想要保護人的感覺⋯⋯」
「不是那樣的。」我打斷他。
「不是嗎?」
「這不是我想要保護我爸不被波及到。傷害已被造成,現在是在我媽去世以來,他最痛苦的時候。有些責任是在我身上,有些是在那些把目空大師跟理龍派到火線裡的人。傷害已經造成了。」
「然後妳想攻擊那些下決策的非假面人員?」
「是啊。」我說。「我厭倦了防守。我討厭等著無法避免的事態發生,因為總是會有那種事情發生,也總是有更大的威脅。而說起威脅,媘蜜,妳對今晚出席的人有什麼樣的解讀?你認為他們會怎麼出牌?」
「就我能從使節團的方向來看,他們是蒸蒸日上。和議人很難以預測,而這是有點諷刺呢。我會說,他們在優先次序上比較低。」
「他們會遵守約定?」
「直到和議人的神經過敏逼他打破約定啊。」媘蜜說。
「那麼高優先事項呢?爪牙?」
「劊子手有很多攻擊能力。她也會處於戰線的最前端。歡狂是快速分身能力者;薇撕【原文Vex】的能力可以在空間中填滿小巧、銳利的力場;出血女【原文Hemorrhagia】具備有限的血液、個人性操體能力,阿尼瑪斯【原文Animos】,會在有限時間裡能變身,然後他另一個形態則有著,能將超能力無效化的遠距離攻擊。還有另外兩、三個人。」
「我是在問他們的目標。」我說。「有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的線索嗎?他們會來攻擊我們?」
「八成是吧。我們現在看起來很弱、很不平衡,特別是瓷偶在保護她的地盤時,沒做到徹底呢。」
「我有在努力了。」瓷偶說。
「妳假如有接受幫助的話,就能做得更好啊。」媘蜜回嘴。「然而妳不想要那麼做,因為妳不想全心致力於這條道路。」
「我是會接受的。我還在弄清楚你們好久以前就知道的基礎啊。」
「小瓷,這是心態等級的事情啊。不只是要出席會議。妳不必喜歡我們,但尊重我們、認識我們、信任我們,也許偶爾允許妳自己有點親密的時刻吧。」
瓷偶猛然轉過頭,瞪著媘蜜——比較像是做出戲劇效果,而非是想表達異議。
「不是那種親密啦。抱歉啦甜心。我說這裡大家都很寬容時,妳絕對能相信我,也沒理由說謊呢——我們這裡的女孩兒們都會支持櫃子裡的女孩兒喔。」
「我沒有說任何東西啊。」
「當然了。」媘蜜微笑著說。「但我是在說,讓我們更常看看那張面具底下的女孩子吧。分享那些脆弱,讓我們借肩膀給妳哭泣啊。」
「我不需要一個肩膀啊。」瓷偶說:「這跟我保護地盤也沒有任何關係。」
「比妳以為的還更有關係喔。」媘蜜說。她瞥向我:「他們都是會針對弱點攻擊的類型,而瓷偶只能保護她地盤的一小段邊界。」
「雇人呢?」我問。「找部下、傭兵。」
「我不想將無辜的人放到火線上。」瓷偶說。
「假如爪牙襲擊妳想保護的人,妳也不會想讓其他人受苦吧。」我說。
「我不知道你們要我做什麼。如果我叫來幫手,他們就會撤退,然後我們最後就會浪費你們的時間,我看起來、感覺卻會很無助。」
「也有其他選項。」我說。
「什麼選項?」
「就是我之前在談的話題。主動出擊。不過,不只攻擊好人。我是在說要瞄準我們的敵人,在他們傷害我們、給我們藉口以前,就先抹除他們。」
「那很危險啊。」戰慄說。
「你們一直在說著那種台詞。」我回應道。「我不應該對我的敵人這麼嚴苛,我不應該逐步增加自己在這些事情上的參與度,我不該主動出擊。放他們亂跑、一直讓我們的敵人有戰鬥先機,那才會比較危險啊。」
「而反過來說,那也會讓我們要面對的所有其他人,更不願意配合。如果我們要認真保住這片地盤,就需要其他反派來談判。使節團只是第一步。」戰慄說。「而如果有其他隊伍進城,他們就會考慮要加入我們,然後在看到我們去拜訪終徒時讓他們被難堪地擊敗,新人直接攻擊我們,對他們來說不是比較好嗎?」
「衝突升級。」瓷偶應和著媘蜜先前的說法。
我嘆了口氣。阿特力士從他在建築頂端的至高點降落,飛到我旁邊的地面。我手撫過他的長角。
「泰勒,我們不是⋯⋯我們在這裡的想法不是要攻擊妳。」媘蜜說。「該死的,他們的做法是很低劣。妳自己在那個餐廳裡也說了。但妳談到要改變我們的互動形式,那卻也是一直以來都能成功的形式啊。我們已經度過了好幾個高緊繃、高衝突的事態。我們也好幾次,好幾天都沒有喘息的機會。妳還想將那種形式升級?」
「不完全是升級。」我說。「如果我們作法正確,我們夠聰明的話,這會減少衝突量。我也需要知道你們願不願意一起來。」
「好啊。」瑞秋說。
「讓我加一腳。」攝政回答。淘氣鬼點了頭。
「我⋯⋯我的票不算數。」瓷偶說。「我只想展現武力,看看我們能不能嚇走爪牙。只是,我認為那會有反效果,因為你們說的劊子手的東西,都讓我很害怕啊。如果你們想幫我處理他們,好吧。但我不想付出任何重要的東西;我也沒辦法告訴你們要怎麼行動,因為我在這件事上是新手。跳過我的票吧。」
「好。」我說。「媘蜜?戰慄?」
「我已經說過我的想法了。」媘蜜說。「妳可以在戰場上下決定,作為隊伍的顏面,我則做幕後。我們就是這樣分工。我很適合幕後啊。」
戰慄說:「我有件事想說。思考一下,或別忘記了。我們撐得比大部分隊伍還要久。有些反派目標高遠,然後他們就會墜落。其他人想消滅自己的敵人,然後就被消滅了。還有其他人已經設立好目標,努力達標,卻只累倒在路上。」
他頓了下,轉開視線。我沒有打斷他。他是想挑出正確的詞彙嗎?思考著他自己是一位被環境所拖累的人?或許,他是在思考著處於那種狀態裡的我。
「也許我們能撐這麼久,部分原因是妳沒想要那些東西。在我們當反派的時候,妳暗地裡是想當好人。在我們想解決掉幾個頗像惡夢的對手,妳的焦點比較近似於生存,而非進攻。我沒感覺妳渴望當上隊長,或渴望統管這座城市,但妳接受這份工作,因為妳知道另一個選項會是一場災難。」
我點頭。就算我想說些話語來回應他,我也不確定自己想要說什麼。
「也許我這一次感覺沒那樣自在,是因為這不是妳通常的行動模式。我感覺妳想要主動出擊,是因為妳受了傷,也很生氣。對此確實應該發脾氣的。想一想吧,好嗎?我不會叫妳不要這麼做。就算我剛說了這所有東西,我還是相信妳的本能,而我這些日子裡,也不怎麼相信我自己的本能了。」
「戰慄⋯⋯」
「我不信啊。我是真心這麼說。妳就做妳必須做的事,但要睜大雙眼。」
「好的。」我說。「我會努力的。」
我忽然想擁抱他,在我們假面服能允許的限度下,緊緊抱住他,讓我雙手緊緊繞住他寬廣的背脊,讓他壯碩的手臂同樣緊抱著我。
光是這個想法,就讓我感到自己可能忽然哭出來,我也發現這種感覺無法解釋地,嚇了我一跳。
我沒有擁抱戰慄;我不確定定自己的感覺跟原因,不確定到自己會想做出任何不像領袖的舉動。我可以帶領這個隊伍。這是個實際、有真實被除數的框架。
我為什麼把阿特力士引過來呢?我已經在想著要逃跑了?避免跟這些傢伙有更多接觸?避開戰慄?思考這件事就很令人感到挫敗。
媘蜜正在盯著我。她可以讀出我正在感到的東西,或能感知出我裡面相互征伐的情感嗎?
「好吧。」我說,我很驚訝於自己感覺有多麽普通。「我們在對付屠宰場時就玩過火,只不過我們現在行動時沒要等著更好的藉口出現。三人一組,一次只有一組在活動,一次只針對一個目標。」
「我們要跟誰打?」瑞秋問。
「終徒,PRT,還有爪牙。」
「妳會加入今晚任務的三人組嗎?」媘蜜問。
「是啊。」我需要一個出口,要做一些事情。
她瞥向戰慄,我猜他倆是有某些沈默的意見一致吧。她看著我雙眼,或是那遮住我雙眼的不透光黃色鏡片。「我會過去。」
「妳要當操作員。」我說。「我以為妳待在幕後的所有意義,就是不要捲進紛爭裡頭啊。」
「我會過去。」她又說了一次。沒有爭論,沒有操縱。只有陳述。
我嘆了一聲。
「我也要去。」瑞秋說。
「我不確定那個點子會很好呢。」媘蜜說。「也許要個比較幽微的人吧。」
「不。」我說。「沒關係的。」
幽微並非我想要的目標。
■
班特利撞入一輛PRT貨車側邊。車身震晃,但它的設計能駛入那些有超能力量、能如字面意義上粉碎大地的反派的地盤。它不會被撞倒的。
另外兩隻狗也撞上貨車側邊,那東西才倒下。穿著防彈背心的PRT警官們也從車頂塔台掉出來,他的裝甲正巧吸收了夠多衝擊,讓他不會受重傷。
強抑泡沫噴灑器肯能會有問題,但沒有制服人員會處於能用那東西的位置。我是有備而來,而每台噴灑器都徹底被裝甲卡車頂的蜘蛛絲勾住,而那些有可攜式PRT泡沫缸的探員們,都被綁住、套上眼罩,也被聚集的狗兒圍住。
鳩尾飛向阿特力士與我,一條光曳落在她身後。她很擅長以如此飛動,不讓光點落在PRT制服人員跟底下的英雄身上——就算我的蟲群爬在她頭部、肩膀跟她雙手上,她仍能精準飛行。在那銀光碰觸實體時,它們會膨脹成,被媘蜜描述成軟力場的東西、裹住那些物體。即使有好幾層力場疊上物體,任何人都能穿入、打破力場光墻,但它會阻礙行動,她就能懸浮在目標上方,不斷強化力場直到那位受害者被淹在大量、較有持久性的強抑泡沫裡面。
那可能會是個很微不足道的能力,但她速度很快。如果她可以在甩出雙手時,將那些會製造出力場的銀光扔到更遠處,她就很可能會逮到我們了。
我的優勢就是,甩開追擊,會比準確追逐其他人的軌跡還要輕鬆。
她鼻子、耳朵與嘴巴裡有蟲,身體也被絲線給綑住,她每一秒鐘的活動範圍都被逐步限制,這也不壞呢。她已經無法使用她假面服內建的小型強抑泡沫噴灑器。我沒辦法阻止她飛行,但只要她無法視物、無法使用雙手,我就看不出她能造成多少威脅。
她進攻時沒多少用處,但她若要撤退,也不會改變景況。我依然有用絲線捆著她,給她綁上眼罩、嗆阻她的呼吸道。她假面服有個外展的衣領,我的蟲子就爬入她衣服內,鑽入皮膚跟衣服之間。這道攻擊只有心理效果,還有要在更大面積的皮膚上施加咬嚙。
我不確定是不是只有我這麼認為,但她的行動,現在就近乎狂躁。
毫無放水。我只有這麼多隻螞蜂跟大黃蜂可以用,但我還是用上我能用的東西。蚊子就很好用。它們能留下腫疤。來留個記號吧。
瑞秋的狗撞倒另一輛PRT總部周圍的貨車。那貨車被撞入建築牆面,撞彎那本該保護窗戶的鐵桿。每扇窗戶都有裂開,蜘蛛絲般的線條延伸於六角形玻璃之間,但窗戶都沒被打破。
石固跟那隻狗近身戰鬥,以裝甲的些許部位斬出、擊開那條野獸。
瑞秋吹了聲尖銳口哨,兩條狗就擒抱住他。他大力甩開一條狗後,卻被另一條狗突襲。他那樣形塑出全身甲的劣勢,就是會限制他自己的外圍視覺呢。
她沒有兩秒鐘沒下達指令。戰場上有五隻狗——或說四條狗跟一隻幼狼——許多狗都缺乏認真的訓練,所以她得用班特利跟他們項圈之間的鐵鍊來管理他們,也下達夠多指令到他們不會有時間亂想,或去追趕其中一位PRT制服人員。
枯焦在室內,跟威揚在一起。最優先事項是要捆住枯焦,而我也以同樣的方式做到那一點。他盡自己所能地瞄準控制絲線的蟲子,然後解開束縛,但他那樣運用時間,就不能前往室外、攻擊我或其中一條狗。至於鳩尾,我也成功讓她逐漸、或多或少無法戰鬥。她無法視物,也無法行動。
其他英雄很快就會趕過來。我重新確認鳩尾沒能追擊,然後大步走到室內,穿過一扇最高樓層敞開的窗戶。
我感覺很冷靜,而考量到這個場面,這就很奇怪呢。蟲子湧上每一位員工——覆蓋住官方英雄,也裹住那些可能是實習的孩子們。有些人痛苦嚎叫,其他人則比較像因為恐懼而尖叫,或在蟲子間間斷斷咬他們時尖叫。
那些蟲子讓我感知出,我需要走哪條路線才能抵達目的地。在房間後角那裡有警官,但我也能感知自己前往的地方。皮戈特仍擔任主任時,我有來過這裡。
我看到門上的標籤。督導。副主任。主任。
我打開最後一扇門。拓閣主任。
他拿著一把槍,但他沒指向我。他身後有個女人,將他當作盾牌。
我已經預備好了聲明的內容、憤怒評論,而我能對他說的許多事情,都會強化我的蟲群對他大群員工所施加的傷的效果。也許,那些可以使他驚訝的聲明,就會讓他清醒理解到他對我所做的事。
然後我看到他眼中的剛硬,還有他站在那女人前方的純粹自信⋯⋯他們有著彼此相配的婚戒。他的妻子。我瞬間就知道,我那麼做就不會有任何滿足了。
流出我嘴巴的言詞,反而很是安靜:「為什麼呢?」
他雙眼仔細觀察我,就像他正在估我的價值。他的言詞粗啞,有著長期吸煙後的沙啞粗氣。他非常刻意地將槍放到桌面上,回答:「妳就是我們敵人。」
我頓了下,拿下面具。我正些微流汗,髮際線周圍的頭髮很潮濕。世界對比著我鏡片的顏色,些微染上了藍色。「沒那麼簡單的。」
「必須這麼簡化。頂頭的人會去妥協。他們會評估哪些界線需要被打破,哪項威脅得被打倒,哪些威脅足夠嚴重。而我的工作是要清除掉城裡街上的罪犯。」
「從學校開始下手呢。」
「在假面著陸前我都不知道行動地點是一間學校。」他回答。「必須做出選擇,我們不是放妳走,妳從此之後都會小心行事,不然我們就得抓緊良機。」
「還讓孩子承受風險?」
「理龍跟目空大師兩人都跟我保證,妳不會傷害學生。」
我嘆了口氣。那個預測八成是對的。
我身後的某人,在一群大黃蜂飛到他身上、螫咬他滿臉時,尖叫出聲。
「真野蠻啊。」拓閣主任說。
「施加痛楚並非重點。」
「而妳似乎施加了不少痛苦呢。」他評論。
「有英雄們會從巡邏回來,是你們叫回來的。但到這裡的路上也會有新聞記者。是我們叫來的。他們會發現你們員工滿身瘡痍,每台PRT貨車不是損壞,就是被報廢。你們的員工就無法將車子從停車場移出去,他們就得走路,就讓記者有機會拍幾張照片。好幾位英雄都有些已經精疲力竭。你們可以試著做損傷控制,但有些東西鐵定會出現在新聞上。」
「嗯哼。」他說。
「我沒辦法讓你們在沒有報應的情況下開溜呢。」
「沒預期妳會那麼做的。」
「我這麼做已經盡可能溫柔了。」我說。「我不認為你有理解這一點。我沒想跟你硬碰硬或結下世仇。我是做我必須做的事,配合這場遊戲。」
「遊戲?小女孩兒,這是場戰爭啊。」他的嗓音堅硬銳利。
我停頓下來沈思這一句話。瑞秋正在摧毀最後一台強抑泡沫車,媘蜜正在對她說一些英雄正在趕來。我時間很緊張呢。
「假如這是場戰爭的話,我這一邊正在獲勝。」我說。
「這個世界因此而變得更糟糕。妳也沒辦法永遠獲勝。」他說。
我對此沒有回應。
他肯定感覺自己在那之後取得了某些優勢。「所有這些措施都有其他意義。妳真以為妳可以再撐五年,而不被殺掉或關進監獄裡嗎?」
「我還真的沒有想過這件事呢。」
「我早已經想到了。壞名聲會隨時間消退。瘡傷也是如此。現在之後的五年十年,假使世界會撐到那麼久,就沒有人會記得我們反擊以外的任何事情了。好名聲會壓過壞名聲,而小心選擇的言語跟一些媒體裡頭的人情,就能幫忙洗白我們的錯誤。我們可是公共制度啊。」
「所以你就以為自己自動就會獲勝?還是你們在長久以來,肯定會贏?」
「不對。泰勒小姐,他們選我作為PRT這個分部的領頭,不是因為我是個贏家。他們挑上我,是因為我是好事者。我是倖存者。我是那種只要我能把對手揍到鼻破血流,就自願被打趴的人。我就是個固執的混帳王八蛋,我不會被嚇到,而我也更不會言棄。布拉克頓灣前幾任的主任都是都走上了死路,而我在這裡,就是要留在這裡。」
「你可以隨意期待呢。」
「不是期待,我是知道結果就是如此。妳想跟這個系統戰鬥?我就會確保它會反擊妳。」
「就算聽到了我之前說的東西?你還想讓衝突升級?」
「那不是我的風格。我的思考大多是施壓。比如說,我能在每次妳搞出事情時就質問妳。事發地點不重要,攻擊對象也不重要。妳或是妳的隊伍做出會任何引來丁點注意的事,我就會把那個男人拖到這棟大樓,每次都他盤問好幾個小時。」
我感到胃緊緊打結。「那是騷擾呢。」
我感知到媘蜜從我身後走過來。她靠在門框上,雙臂交疊著。
「這是場消耗戰。」拓閣說。「我會找出縫隙,我會打破你們每一個人。妳若幸運的話,現在的五年後他們還會記得妳的名字——在他們討論起兒童反派時,就會講起那個竟然蠢到自己佔領整座城市的女孩呢。」
「他在耍妳。」媘蜜低語。「他知道妳今天過得很糟糕。最好直接離開。記著,捍衛者還沒過上壓過我們的好日子。」
我想問他關於黛娜的事,但那沒有意義。那是他能用來對付我的問題,而我也已經知道答案了。
我走向桌子,翻過照片相框。第二張照片上,是拓閣跟她的妻子還有兩位年輕女性。家庭照。
「你有女兒。」我說。
「兩個女兒,都去了半顆地球外的大學。」
「你用一位父親來傷害一的女兒,就沒感到一絲一毫的自責嗎?」
「一點都沒有。」他瞪是我的雙眼,回答。「我看著妳,我可沒看到一個孩子,我也沒看到一個眾人都誤解的英雄、一個女孩、女兒或任何那種東西。泰勒.赫本,妳就是個混混。」
混混。
他的思想框架全都是「我們對抗他們」。好人對抗壞蛋。
這沒多少成果,但也證實了我已經取得的結論。黛娜是自願供出情報。不論拓閣主任為人如何,他都不會虐待那已經是受害者的黛娜。
「我們該走了。」媘蜜說。「瑞秋跟她所有的狗都在樓下,我們可以在援軍聚集過來以前開跑。」
「是啊。」我說。「差不多要結束了。妳,在後面的。妳就是拓閣太太?」
那個女人稍稍站到一旁,走出他丈夫的後方。「我就是。」
「今晚來探訪他?」
「給他跟他的部下帶了甜甜圈跟咖啡。他們工作很努力呢。」
「好吧。」我說。「妳會支持妳的丈夫?認可這種話術?」
她繃緊下巴。「是的。絕對支持。」
我沒浪費一瞬的時間。我讓空閒的每隻蟲子都湧入房間裡,完全不碰拓閣主任,而是讓蟲子大群流爬過那女人全身。她尖叫了。
他伸手要拿桌上的手槍,我將手往後一扯。我綁在扳機護環跟我手指上的絲線,將手槍拉向我。我手壓在那把武器上,防止它掉下桌面。
拓閣已經要抽出他腳踝上的左輪。
「停。」我說。
他停了下來。也緩緩,直起身。
「我是以行動闡明重點。」我說。
我的蟲子飄離拓閣太太。她沒有受傷,身上沒有傷痕或污點。她在蟲子陰森懸浮於她跟她丈夫之間,就退入角落。
「不確定為何還要闡明。這不會絲毫改變我的想法。」拓閣說。
我沒有回應。蟲群轉換位置、撲到他身上。就算他宣稱自己很頑強,也很快就開始尖叫呢。
我從桌面邊緣撿起那把手槍,跟上了媘蜜。我們一起大步走向出口,約以步行與慢跑間的速度移動,經過了二十多位PRT員工,他們每個人都覆蓋著蟲子,並在看不到的時候踉蹌、毫無意義地想趕跑蟲子,也對整個世界吼叫、尖叫出他們的痛楚與恐懼。
沒有任何毒液,螞蜂跟大黃蜂都沒擠壓身體裡的毒囊。沒有什麼會讓他們性命垂危的要素。那也足夠有戲劇效果了。
「他說的對。」媘蜜評論。
「是說什麼?」
「妳那樣的作法,饒他妻子一命,不會改變他的想法的。」
「好吧。」我回答。我拉開一個抽屜,將拓閣主任的配槍放到抽屜裡,而阿特力士將媘蜜載下到地面層。
阿特力士回到我身邊,我就升空,在我們逃離現場時,飛在莉莎、瑞秋跟狗兒們正上方。我刻意將每一隻蟲子都留在PRT總部裡頭,在他們根絕那裡的害蟲,蟲子就會一直騷擾他們,而且這也會讓媒體有其他拍照的機會,或在清除蟲子的數週數月中,以此不斷提醒他們。
新聞記者們已經幾達現場。那裡無疑有攝影機在追蹤著我們。我想起拓閣主任,要羈押起我父親的威脅。那只是一道威脅,也只有他的空口白話,但這讓我思考起我在公眾面前做過的每一次活動與每一件事,那都會成為我捅入我爸背後的刀子。
這感覺並不好。
也許我用拓閣妻子所做的小小證明。那也很可能是,我在試著對自己證明出某些東西吧。
#石固 #雜種 #班特利 #母狗 #鳩尾 #戰慄 #淘氣鬼 #瓷偶 #攝政 #枯焦 #拓閣 #媘蜜 #泰勒28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PLOSChA5f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