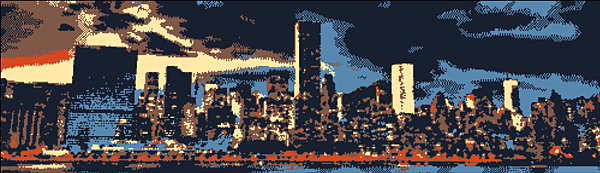 x
x
Disclaimer5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82Hz115xwa
【原作者贊助連結】
我無法從周圍的英雄臉上觀察到怒目神情。媘蜜剛突然高聲說話,會讓我們現在,必須在此付出代價,我也不確定這在長期下來是否有任何好處呢。再說,我們這夥人也是我所能注意到的、唯一真正的反派,周圍則都是不信任我們的人群——以為我們會試著幹出某些事情的人。
我也敏銳察覺到,芝加哥監護者跟替身羊都能聽到我對媘蜜說的任何東西,而我最想對媘蜜說的,會是在許多層級上最為糟糕的話題:喊她白痴,會讓我們看起來很沒有團隊凝聚力,而且她對這種辱罵從來都沒有好反應。
我不想要構工、優雅跟雲手聽見,我就將手放到媘蜜肩膀上、阻擋了她,說話的音量幾乎沒超過低語。「時機太差了。」
「他們所有人都聚到一起了,就是我唯一能有的機會啦。」她說。她看起來根本沒想降低音量。「知道了這一點,就能取得一大塊拼圖,讓我能開始搞清楚所有情報是怎樣吻合在一起的。」
「我知道啊。」我低語著:「但這時機還是很差。我們不需要對三巨頭樹敵,我們頭上也不需要有擊殺令。」
「民軍小姐不會認真下令的。」媘蜜說。
「是那樣嗎?」我問。「或者這是妳那種,有根據的猜測?」
「是有根據的猜測。」媘蜜說。
「別忘了其他假面很有理由恨我們,刺激他們的老闆,就可能會讓他們有動機逼民軍小姐發布擊殺令、把布拉克頓灣清理乾淨。假使是從上頭來的命令,她願不願意殺我們就不重要了。我們要確保避開明顯的危險性。」
「當然啦。」她說。「我也取得我想要的東西了。」
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對這個結果感到高興。她沒有說自己不會再犯。「也要考量到我們已經累了。很容易犯錯的。」
「我懂啦。沒關係的。」媘蜜說。「但就像妳需要時間才能集起蟲子,我在戰鬥開始前,也需要能用的背景情報啊。」
「那不是我們現在會想開始著手的戰鬥啊。」我說。「也許永遠都不會想著手吧。」
「我有概念的。稍微相信我一下啦。」她微笑著,說道。
我在面具底下皺起眉頭,接著前往監護者們那裡。我假使我沒辦法挑選正確的戰鬥時機的話,就無法拿件事唸她了,而且現在跟媘蜜吵這事也沒有幫助。之後在其他日子裡,我再來解決這件事吧。
「發生什麼事了?」構工問。
「討論策略。」我說。「你們還好嗎?雲手?」
「梅爾丁有找到我,清掉所有無涉物質。」雲手說。「我的另一個形態會有點弱。可能是因為我的真身感覺沒力,也可能是我另一個身體的能量源沒力了吧。」
「電光法師呢?」我問。
雲手瞥向構工,但他沒回應。我可以從他們的肢體語言看到跡象了。
「我很抱歉。」我說。
「作嘔感、嘔吐、頭痛、虛弱⋯⋯假使他有撐過今天,八成也會在之後病死吧。」構工說。
「還有治癒能力者的。」我說。「或輻射專業的巧匠。我相信他們現在會找到好醫生去照顧他的。假使你們會願意接受我這種說法的話,我會說,你們的優先次序是在這裡的現在,這個情況。」
構工換了姿勢,打直背脊、站得更挺。他穿著動力裝甲,使他的頭部、雙肩跟胸膛都比我高。
我非常欣賞那套動力裝甲。而對我來說,光是動力裝甲的概念就很可怕了——組裝起一整套能扳彎鋼骨、打穿水泥的機械,這本身就很令人刮目相看,但這種功能以外還加上了爬進這套機械裡,用其走路,也知道一處故障就可能造成災難性的疏失?被困在那套裝甲裡,或者是更慘的可能性:裝甲意外將那股可怕力量轉回作用於身著裝甲的人身上?
我仍像眼盲時那樣運作著超能力。一條蜈蚣爬過我面具的鏡片、遮住了我的視線,我就用意志力移開它。
構工很適合穿裝甲。他就像一台自走坦克,身寬與身高一樣龐大,裝甲上還帶著亮眼的鏽棕銅亮眼設計。他的雙眼幾乎沒辦法被發現,但我可以看到他面具後方的眼睛,他正在仔細觀察著我。他沒開口回應。
我太直接了?太專橫?
「你是可以擔心她。」我說,而戰慄在那面牆底部的景象閃過了我心中:「但你最能位光電法師做的事情活著撐過這個事件,然後在完工時,你就可以當個好隊長、去找其他能幫助他的人。」
「梅爾丁會那麼做的。」
「也許吧。」我說。「但你真的願意將你隊友的安危交給監督的人嗎?你自己來處理不會比較好?」
「我感覺他比我更擅長處理這種事,就會在這件事上仰賴梅爾丁,除非我沒理由信賴他。」構工回應。「這整件事、整個情況,還有整個作戰的組織,若沒建立在信用之上,就不會成功了。」
「好的。」我說。他的回答讓我猝不及防。我沒預期到構工對他的督導會有這種信心,而我也不確定是我自己的偏見或他的天真才造成了理解上的差異。不過,就算我是對的,我也沒立場「糾正」他。「你就以你自己的方式帶隊吧。抱歉我妄加臆測。」
「沒關係。」構工說。「妳有沒有臆測都沒差。我會確保妳跟妳的隊伍不會惹出麻煩。」
「在我們丟掉臂帶、帶他們去昹奪羅那裡時,也沒確保他們不惹出麻煩啊。」優雅指出。
「我會承擔那一次的罪責。」構工說。
「我在跟民軍小姐談話時有提起那件事。」我說:「你最好說實話,然後說是我們逼的。就怪我吧。」
「不對。」攝政說。「要怪我啊。」
我看了他一眼,他聳聳肩。「只是想參與一下這場樂事啊。」他說。
「就算會讓你們承擔擊殺令,妳還是想要我怪罪妳?」構工問。
「我寧可不要被掛上擊殺令的名單。」我說。
「而我也寧可不要承擔妳被殺的間接責任。」構工說。「我想這就是結論了。」
也許這才是最好的,我想著。「那我們就來談談策略跟優先次序吧。構工,你需要任何東西嗎?裝備?準備時間?」
他搖了頭。「不。我需要時間清理裝甲,確保所有東西都可以運作,就這樣而已。」
「母狗。」我說。「狗兒們還好嗎?」
「很不好,但他們在漲大的時候就會好轉的。」
我看向狗兒們。他們各自都漲到了普通體型的兩倍大,內部跟外部肌肉波漣鼓動,層層覆蓋著鈣化的皮膚跟尖刺骨鉤。他們正在走動,每隻狗看起來都很好。我看著剩下的那夥人,試著考量所有變因。「攝政,你能影響到碎歌鳥嗎?」
「算是可以吧,金屬小子把我踹出來之後,感覺太差,就什麼事都幹不了了。而在我好轉時,她也消失了。」
「那是什麼意思?」
「她不是跑出我的範圍外,就是死了,或是進到了諾埃爾體內。」
「在愛剋妲娜體內。那就糟糕了。」我說。
「而且也很可能就是那樣噢。」媘蜜說。「她純粹為了要搞我們,就會那麼做。」
「我們對她的超能力變種,有任何預想的概念嗎?」我問。
媘蜜梳著頭髮、用手指跟指甲清理掉黏稠物。「沒。有些東西一直都是穩定的影響因素,變種會依據這些因素來運作。就遠璟來說,就是空間扭曲。就戰慄,就是黑暗。就碎歌鳥,則有三個強烈的可能性:玻璃、聲音或是某種大規模念動能力。」
「去我的。」構工說。「除了玻璃之外的,全城規模的攻擊?」
「是木頭?金屬?或是路材?」媘蜜提議著。「她原本能力的作用方式,她的念動能力會協調著其他物體,用那些物體來延伸影響範圍。她會盡可能擴張範圍,然後設置出一場廣範圍爆炸。瞬間引爆混沌。」
「我們在爆炸時就會有所反應得。」我說。「我也許能用蟲子,在她要影響玻璃以外的任何東西時反應過來,給我們爭取時間反擊,或找出閃避的方法。但我們時間有限,應該好好運用時間。我想回到地盤裡拿取物資,也許還要回到蛇蜷擺放阿特力士的北邊。」
「阿特力士?」構工問。
「掠翅的超大甲蟲寵物。」攝政提供了一份解答。
「有它的話我就能飛了。」我說:「我也想在替身羊的超能力穩定下來前,避免被人找麻煩。要做到這一點的最簡單方法,就是待在地上一百呎。現在那不重要,我想知道的是有沒有其他任何人需要跑腿呢。」
「有喔。」媘蜜說。「我想跟其他行旅人見面,跟擦除者談談。」
「擦除者?」構工問。
「擦除者。之後我也需要回來這裡,在客人抵達時跟他們會面——我有邀請斷層線她們一夥人。」
這讓我頓一下,但我也沒法在英雄們也在這裡時講出那停頓的原因。「我們先找個車子吧。」
PRT一半的強抑貨車頂部都有能噴灑泡沫的砲台,而每輛貨車都在繞著這棟建築跟工地的坍塌處、掩埋到諾埃爾頭上的區域周圍,朝殘骸噴灑出泡沫。
另一半的貨車,只能被描述為可移動式的路障——它們的部署在擋住小路、小巷的位置,只留下幾條大路能被假面掩護。
讓芝加哥監護者跟著我們的好處,是我們可以請求這種東西。構工去找了梅爾丁,梅爾丁朝他的臂帶說了話,就有位PRT探員給我們帶來一輛卡車。
構工有談起組織,還有對他人的仰賴。我不認為這些事情有他說的那種重要性。從我對三巨頭的牽連關係的跡象來看,PRT就不值得人仰賴。不過,有車就是有車,而我也沒想抱怨呢。
■
行旅人正被拘捕著,魔閃師則不在場。創使正處於怪物型態,被強抑泡沫固定到地面上。我們沒看到她的真身的任何跡象,這表示,她不是在裝假,就是在配合拘捕。她使用了粗略的女性型態,腰間以下有著蛇尾,她突出的額頭骨向外展開,就像三角龍的褶邊骨頭般急遽向後延伸。她沒有眼睛,嘴巴寬大無唇,牙齒尖銳細小,雙手很修長,還帶著尖爪指甲。
烈陽舞者跟軌彈天人都被黏到她兩旁,肩膀以下都沒入泡沫。擦除者在一段距離外的馬路上,腰間以下的身體都被埋起來。他的頭髮發出微弱的紅色光輝,而他雙眼跟嘴裡也散發出微光。
軌彈天人跟烈陽舞者盯著走過去的我們。英雄們正遠遠站在他們周圍,八成是出於安全性預防措施,才如此部署。我沒認出那三位正在盯哨的人——有一個男孩跟一個女孩,各自帶著短弓與帶有公牛、公羊角的頭巾,還有一位八呎高、體型壯碩的女孩,拿著一個肯定是超能力所影響著的、比我還要更寬大的鐵鍬。她正彎下腰,幾乎駝著背,她還有一道左側上排牙齒的嚴重過度咬合,使牙齒露出她臉前方。她的頭髮綁成一個濃厚、黑暗的辮子,辮子長到幾乎垂及腳趾,近乎遮擋了臉。她跟鐵焊一樣,沒有戴面具。
「西部監護者!呦!」構工喊道。
那身形巨大的女孩轉過身。她說話時的嗓音比戰慄還更低沈:「芝加哥監護者。真不是我想說,但你們少了幾個成員。他們沒⋯⋯」
「還沒有人死啦。」構工說,伸出手。她握了那隻手。他說:「有兩三人撐過來了。釣熊【原文Bearach】放假,我想他在利魔維坦攻擊之後壓力很大,他也希望有個好理由,來翹掉下一次終結召喚者的攻擊吧。我跟他說,他不該強迫自己參加這些任務,但是⋯⋯」
「他感覺自己必須保護其他人。」她說。
「是啊。榴石【原文Garnett】也想跳過這次任務。光電法師是有來,但他被攻擊得很嚴重。」
「受傷了?」
「輻射中毒。」
「有多嚴重?」她問。
「嚴重到,不會直接毒死。」構工回答。「像我說的,還沒有人死掉。」
她重重一點頭,頭髮垂到前方。她伸出手,將一隻大手放到他的裝甲肩膀上。她說話時,嗓音出奇地溫柔:「我很抱歉。」
構工沒立刻回答。考量到人們的性格跟他們對自身處境的接受程度,給予他們的同情,就很可能成為十分糟糕的做法。我感到我雙眼裡的濕潤,但我是想到了戰慄。
有其他事情可以讓我分心的話,我就可以處理感情。我會分開情感,重新專注起來——專心做完工作。但假使有人跟我說幾句簡單的話語,像那女孩現在在此安慰構工的動人姿態,我就猜想我會無法繼續抵抗、保持鎮定了。
也許,這是件好事——我隊上沒有人是那種類型。
「我想跟行旅人聊聊。」媘蜜說。
大女孩看向構工,她是對他說話,沒回應媘蜜:「構,這褓姆差事也太強了吧。這些人可是新聞上的傢伙啊。」
「只有妳這麼說。」構工說,指向她的俘虜們。「長釣男孩【原文Fisherboy】在哪?」
「隊長這次沒來。我接手帶隊。」
構工說話時,嗓音裡帶著真誠的振奮之情:「妳已經好一陣子想帶隊了。」
她微笑著,只使她暴露出更多上排牙齒。「我不會真正升官的。他們絕不會給我這種人一個隊伍啊。」
「是我的話就不會擔心這一點。妳會贏得他們的心的。」構工說。
同袍情誼。假使我加入監護者,我就會有這種同袍情誼嗎?那樣的事態,會如何發展呢?
「媘蜜、暗地黨,這位是谷麗【原文Gully】。我這麼強的唯一原因,就是因為我有她的超能力的研究資料。她曾經照顧我兩個先前部署到聖地亞哥的隊友。雲手就是其中一個。假使你們對她沒表現出最高敬意,我就絕對不會配合你們了。瞭了嗎?」
「沒問題。」媘蜜說。我點頭同意。
我們一群人,一齊走近行旅人,谷麗也隨我們而來。
「就知道會這樣。」軌彈天人在我們可以聽見他時,說道。「我跑來救援,卻是一場空,我還被逮捕。你們都沒幫手,魔閃師也搞了我們所有人。然後在所有事情都定下來時,你們能自由活動,而我他媽的就得坐在這團黏泡泡裡。至少,告訴我魔閃師有了報應?」
「就我所知並沒有。」媘蜜說。
軌彈天人嘆了口氣。
烈陽舞者沒有移動。她駝著背,坐在那裡。
「她沒事吧?」我問。
「當然有事。肏他媽的魔閃師把我們兩個傳送到空中,讓我們墜落。我爬起來時,他就傳送了第二次。我的手腕雙腳八成都有骨折,她的腿也不會比較好。她昏倒了。我們他媽的超需要醫療照護啊,他們卻給我們這些泡沫。」
我轉過身。「構工,谷麗,我們能給這兩人安排些照護嗎?」
「我會用臂帶傳達訊息。」谷麗說。「看看上層的人怎麼說。」
「可能需要提到這兩人都是重擊手,攻擊力都很高。烈陽舞者若有機會,八成就能了結諾埃爾,而軌彈天人八成能拖慢她。」
「我會轉達的。」
她走了開來,從口袋裡拿出手機、端到耳邊。
「真以為她是在戴面具。」攝政低語。我派了一群飛蟲撲到他臉上,同時也惡狠狠地看了他一眼。他就只能急著噴口水。
軌彈天人抬起頭看向我。我沒辦法在他面具鏡片底下看到他的雙眼,但我很敏銳地意識到他此時的沈默。他沒想對我道謝的。
「哎呀呀。」媘蜜說:「我們就來看看我的猜測對不對吧。假使不對的話,我就浪費了一大堆錢,還有一大堆用來思考這個問題的時間呢。」
「猜測?」構工問。
「猜測。」媘蜜輕巧走向擦除者。那位前商團,是以坐姿被埋入帽沒,四分之三的身體都沈入一個,約略有兩呎半直徑的地表洞穴裡頭。他沒辦法將雙手舉出洞口、拉出或推出自己身體,而洞口的狹窄拘束也讓他無法活動雙腿。
一道閃光顯現在附近,只擊中空氣。
「擦除者。」媘蜜說。
擦除者沒回應。
「所以你就不說話呢。」她說:「那會讓這更難以進行欸。」
她盤腿坐了下來,讓自己更能與他對視。一閃光在她兩呎開外爆發,距離地面有好幾呎高,撥動了媘蜜的金髮。她用手將頭髮梳回原位。
「妳的推測是什麼?」我問。
「他的超能力。妳認為那個能力是什麼呢?」
又有另一道閃光。閃光又一次,只擊中空氣。
「我以為那是不受控的摧毀光線,但妳想告訴我說,那是其他東西。」我說。
「是的。」
又一道閃光。媘蜜在膝蓋上敲打著指尖,看著、等著閃光。
「我們的時間有點趕。」我說。「所以,也許妳該加緊解釋?」
「我只是在等著。在我能不能確認理論就只是時間性的問題——假使那個理論可以被確認呢。」
「假使那能被確認?」
「妳不能就配合一下嗎?我超愛這種《女作家與謀殺案》的經典橋段,讓我把大家叫過來,之後大放送情報。所有事情就會合理,拼圖會組合到一起,事件就會被解決。假使我太早解答的話,就會失去所有戲劇效果了。」
「假使妳坐太靠近那個超能力不受控制——那個超能力不是能量光束——的傢伙,妳的臉被削掉一半然後死掉的話,我們就會喪失獲得解答的機會了。」我說。「我知道妳知道自己很安全,但先額外小心點吧。」
我伸出了手,但媘蜜沒接下我的手。對了,替身羊的能力。她不靠著我的協助就站起身,後退幾步。
「我在證實這部分後就會解釋的。」媘蜜說。「剩下的東西要等斷層線的人飛過來。」
「而那要還要多久呢?」我問。
「距離我打通電話,差不多過了一個半小時。也就是九十分鐘以前了⋯⋯」
媘蜜在另一道閃光擊出時頓了下。閃光橫越地面,但地面依然毫髮無損。
「那裡!」她說。她手伸到腰帶上,一秒就拿出雷射筆。她圈起那道光束打中的區域。「你們可以移除那怪地板,然後也不要打破中間部分嗎?」
構工向前踏了一步,但谷麗擋住了他。她輕輕將鏟子敲上地面,那片區域就從地面浮空,切成完美的三呎高圓柱體。
擦除者另一波炸光出擊,那根柱子底部就被挖掉了一塊球型體積。媘蜜向下彎腰,抓住那根倒塌的柱子,然後趕緊退出擦除者的能力範圍,將柱子拖在身後。
「小心!」我對她說。「假使妳被擊中⋯⋯」
「沒關係了。」她說。她放下圓柱體,稍微將底部百到地面上,以手指碰觸頂部——那曾經是路面之處。「瞧。」
我探得更近。
那個差異細微到我幾乎沒看出來。路面的質地毫無間斷,每分鐘就轉換到不同質地,也有著些微不同的深淺色。而那片區域形成了片整齊的圓形。
我在其他人過來看時退開。只有瑞秋沒跑過來觀察。她比較專注在自己的狗兒上,用一把金屬梳子梳掉他們毛髮上的黏糊塊。班特利撞了下我的手掌,我就抓起他的頭頂。
「我不懂。」構工說。「是光波改變質地?」
「那個光波移植了質地。」媘蜜微笑著,說道。
「妳他媽是怎麼注意到這種事情啊?」雲手說,碰了碰那片平面。
「那不重要。現在,假使大家願意聽我解釋的話,我希望現在能表現一下了。我們都知道超能力有內建的限制。這些限制顯然是為了我們好——就算我們可能不總會喜歡這些限制,它一樣會保護我們。曼頓效應就是其中一項限制。我們獲得了超能力,而在超能力穩定時,我們就會獲得某些硬體侷限,讓超能力不會傷到我們。目前的理論會說那些限制保護過頭,將人類或不是人類的活物全等同視之。另一個說法是,那只是我們的同理心在作用——我們有內建的限制,是因為我們會在意人類同胞,而我們超能力會認同同理心。還有跟著我吧?」
「我有在聽著。」我說。
「隨超能力而來的還有其他限制跟優勢。那位烈陽舞者就不會被燒傷。在離她身體特定範圍內的氣溫,會變成百分之百普通溫度。我們的老夥伴暗影潛行者可以穿過牆面,但永遠不會沉入地面、墜落到地球中心。而這位擦除者,他那種不種控制的超能力,永遠都不會打中他腳下的地面,他就更不可能意外打坍一棟會倒在他頭上的大樓的關鍵支撐點。為什麼呢?」
沒有人提出解答。媘蜜就微笑了。
她解釋道:「看看這個,我認為這是因為給我們超能力個那些行者,會將我們連接到其他平行宇宙的地球。也許還會為我們每個人,連接到各組地球,讓兩個超能力在相會時,不會互動得太過糟糕。這位擦除者會將物質轉入結構跟我們約略一致的地球,卻不會扯爛自己的立足點,就是因為他在將物質打出去時才能將更永久的要素轉進來。暗影潛行者會取代自身的質量,移入另一顆地球,會將質量跟立足點分散到兩個世界上。她仍全然位處原地,只不過,她也不全然在這裡。烈陽舞者會過度加溫自身周圍的區域她就會做出擦除者所做的事,將大部分人體空間的過熱空氣轉到平行地球,將室溫空氣轉入身體周遭。」
「那不就表示,行者會在某個運氣不好的世界裡造成損傷嗎?」雲手問。
「好問題。」媘蜜微笑。「那八成是沒錯。也可能是烈陽舞者每次用超能力保護自己,她就會在其他地球的她的約略位置上放火。沒有人能說其他地球有人居住,但是可能有人居住呢。」
我顫抖了一下。這話題太過沈重。「這也會適用其他超能力嗎?我的超能力不會真的能保護我啊。」
「啊。」媘蜜微笑。她舉起一根手指:「而這就是我想給妳的問題了:妳的能量源是什麼呢?妳是從哪獲得能量,讓妳即時發出或接受蟲子的資訊?要想想,目前唯一能攔截、理解跟複製妳的信號的人,只有黑客文喔。」
「妳是說,在我獲得超能力的時候,我的行者有選出合用的地球,然後我⋯⋯就做了什麼?從那顆地球榨取力量?」
「很可能喔。不然就是從兩顆或兩億顆地球汲取力量吧。也許是空氣中的光能或輻射能,然後將那些能量壓縮成某個妳可以利用的東西。」
「我有在弄傷,或殺人嗎?」我問。
「誰知道呢?」媘蜜聳了肩膀。朝我一閃出微笑。「也許妳的行者挑出好幾顆荒蕪、完全沒有人的地球——生命從未進化,或是人類早已滅絕的地球。也許妳是從上百萬個世界抽取一點點、丁點能量,細微到沒有人會注意吧。」
「或許妳是在把另一顆地球的布拉克頓灣變成一片冰冷、荒蕪的廢地呢。」攝政評論道。
我不想思考這件事,我想著。這也不是說我可以將自己的超能力關閉——要那麼做就只能殺掉我,或是移除我周遭的每一隻蟲子呢。
「那是⋯⋯有點無厘頭。」構工說:「那可是從一片路材,跳到平行宇宙等級的思路啊。」
「這只是個理論,但我想了很多關於超能力的事情,我的隊友也知道我滿擅長這種東西。現在,我要你們想像一下。想想所有複雜的處理過程,會被用來控制超能力。天殺的,掠翅能單獨控制她蟲群裡的每一隻蟲子,同時又給其他蟲子下達完全不同的指令。我的超能力也有類似的功能。構工的腦力,在他思考工程、建築時的處理機制⋯⋯那些思考過程是在哪發生的?我們的腦子肯定做不到這種事情啊。」
「那是在其他世界嗎?」我問。
「但怎麼能接觸其他世界?又是接觸誰呢?」她問。
「告訴我吧。」我說。
「在我們可以思考行者的時候,我們有點傾向將它們想成相當微小的事物。畢竟,以骨鋸談的方式來看,它們是某個擠進我們腦袋的東西,連結上我們的腦子,之後就會在重組我們腦袋的運作方式時自我燃燒。對吧?但像她描述的那種任何微小事物,都不可能管理好我們的力量。所以我要問的是⋯⋯假使它們很巨大呢?是超級龐大喔。假使每一個、所有的行者都因為某個理由,在挑選我們,它們找到我們之後就會跟我們連結起來——它們藉由重寫我們的小腦袋的每一個細節部位來連接上我們的身體,然後透過額外的腦葉,它們就會將我們連接到其他所有平行地球,也包含了它們所在的空間?也許它們有著實體,也許它們更虛無飄渺,我都不知喔;他們也可能是植物或動物,但它們依舊存在著。它們可能是無比巨大的生命體——有城市、大陸或月亮那樣的體型,隱藏在某顆平行地球上,像用線條連接上我們,用細絲橫跨宇宙次元、連上我們的腦葉,發送、接收所有必要的資料。然後那東西就會連接著我們每一個超能力者,也連接上沒有超能力的我們,把沒能力的我們只用來處理我們的能力的資訊,吸收、引導那些必要的能量、訊號跟情報,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變成⋯⋯」
她頓一下,稍稍輕笑著。
「變成超能英雄跟反派,還有將超能力用來賺錢或打發時間的無名小卒。」
我顫抖了下。
「這太沒道理可言了。」構工說。
「也許吧。這只是個理論。」媘蜜說。「但假使你感覺這八成是正確的話,我就會非常想聽到更好的解釋。」
「為什麼?」谷麗問。「它們為什麼這麼做?假使它們那樣強大,假使它們那麼巨大,為什麼會在意我們呢?」
「問得非常好。」媘蜜回答。她也微笑著。「我沒概念呢。」
「我沒想說這個理論並不有趣。」我插話道:「但這跟愛剋妲娜的情形有什麼關聯?她是終結召喚者嗎,而且終結召喚者跟行者有關係嗎?」
「喔。我是滿確定她跟終結召喚者之間沒有真正的關聯性呢。我有看到她的運作方式。就我看過的終結召喚者來說,沒什麼跟她吻合的特質。不對,她是其他種類的東西。」
「那麼這跟她有什麼關係?因為這個實驗肯定可以延後。」
「哎,是有兩個重要影響因素啦。」媘蜜說。「有兩個計劃。妙策其一是愛剋妲娜很可能取得了壞掉的行者。有些事情被弄錯了,行者就受到損傷、錯亂狂亂,或者是某些通常會有的限制不再存在了。老天,行者對她的掌控力可能比較強,讓她把更多行者拉入這個世界來操作自己的身體,然後通常會有的、保持行者處於被動或睡眠狀態的處理程序,就不存在於她身體裡了。不然就可能是,她的行者正想要擠進我們的世界。」
「而行者跟城市一樣大?」雲手問。「或是月亮那麼大?」
媘蜜聳肩。「也不是說她不能變得那麼大。我之前是想把瑞秋的狗扔到她身上,直到她撐不起自己的體重,但她還是能使用超能力跟嘔吐,而她的複製人似乎也在她長大時,變得更脆弱、虛弱,數量也增加了,我就無法確定那個計畫有成功呢。」
「我他媽的絕不再讓妳那樣拿我的狗冒險。」瑞秋說
「當然了。」媘蜜補充。「也有那個要素。我真的沒辦法在不找出更多大鼎給人超能力的過程時,直接確定愛剋妲娜的相關情報,我也真的很想從行旅人身上拷問出那些事情。但了解這整件事,就是我們最能理解愛剋妲娜的機會,也能讓我們阻止她。或甚至是治好她呢。」
我瞥向其他人。「但是⋯⋯有些強大的人不會願意讓我們挖掘更多關於大鼎的情報呢。」
「是有那種人呢。」媘蜜說。她瞥向跟著我們的英雄們:構工、雲手、優雅、谷麗、替身羊還有雙子。「這也就表示,我們需要在缺少其他來這裡阻擋愛剋妲娜的英雄們的幫助時,才能動手。這樣才八成會合理吧,因為他們可能不會願意接受我接下來要提出的民主投票選項。這就是我想執行這一個研究計畫的,第二個理由了。」
「我感覺我不會喜歡這個點子欸。」優雅說。
媘蜜微笑了:「我認為,我們可以在宇宙次元之間開個洞。」
#軌彈天人 #雜種 #班特利 #母狗 #優雅 #谷麗 #攝政 #替身羊 #擦除者 #烈陽舞者 #媘蜜 #泰勒 #構工 #雲手53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SN8MJszpm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