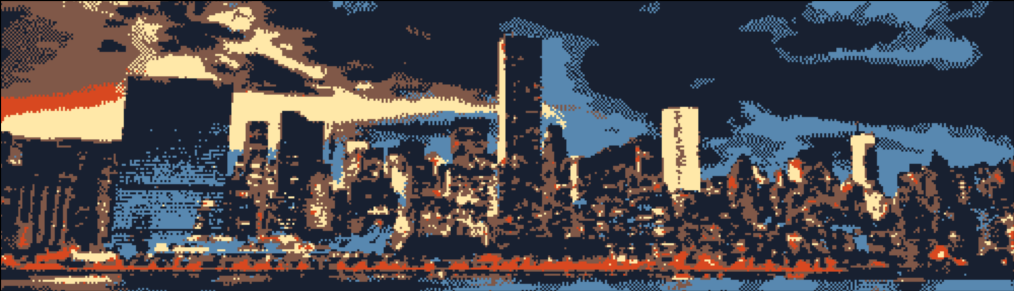 x
x
夕陽總是在輪替壞天氣過之後最美。今天也不例外。承受了持續一天半的大雨,天空正轉為鮮活的深橘腥紅暗影,強風中清滑的薄雲上有著顯眼紫輝。在我們接近港灣的水面時,這景色看起來特別棒,可是我們沒有一人真的有心情欣賞風景。
我們彷彿成為,和那群從市場走到閣樓的朋友們完全不同的一伙人。沒有交談,沒講笑話,沒想連結關係。我們全在想同一件事:某件事出了差錯,而那件事已經發生。不過,沒有人說出他們的猜疑,就像有個不成文的默契--我們只有在大聲說出來後,事情才會成為現實。
沈默中,我們搭上在渡輪那裡的巴士,前往火車維修場【原文Trainyard】,那個座落於與百行大道正相反方向的碼頭區塊。
我們一群人從公車站牌走了半個街區,繞過一個被遺棄的建築物背後,在那脫下平民衣服。儲藏設施在距離火車維修場正好一個街區的地方。經過一道鐵鍊鎖著的圍籬後,我立刻能看到長條、被遺棄的塑膠頂貨車,像個過大、破碎的墓碑般野草蔓生,周圍盡是垃圾瓶罐和臨時帳棚。整個區域荒涼無人,空空蕩蕩。很難說明為什麼巴士還會來這種地方。我猜,大概是還有一隊維護著火車車軌,以免有列車經過的基本工作人員吧。
我們進入了迷宮裡。每個儲藏貨櫃橫向相隔約十呎,直向十呎,可是卻有數百個貨櫃,每一個都和隔壁的連在一起,就像一堆毫無組織的十、二十個磚屋組織在一起。這景象滿常見的;這樣的地方在布拉克頓灣裡四處散播。幾十年前失業率高漲,人們開始把儲藏貨櫃當住處。某些進取向上的人跟進潮流,儲藏櫃街區也更常出現在荒廢的倉庫和停車場。這裡是--以某種記錄外的方式--你能找到的最低生活預算住所的地方,也是讓有自己的公寓或房子的人能保存他們最珍貴的財產,並能在晚上安心睡覺的地方。
可是事情不斷惡化。儲藏設施變成毒品窩、幫派的聚集地,是瘋子聚會的場所。流感傳播和喉嚨炎在這個緊密連結、住著沒洗澡又營養不良的人們的「社區」裡廣泛傳播,讓人們因此死去。某些不想病死的人,因為他們的所有財物而被刀子捅死,或是餓死,屍體就留在租來的儲藏貨櫃的緊閉的門後方。在最後,城市崩毀,再也沒有人要貨櫃了。到那時候,當地企業崩毀,足以讓街友和窮人能夠移民到被拋棄的倉庫、工廠和公寓區,非法佔據著那裡。當然,大略同樣的問題仍然存在,但至少事情沒有那麼緊密到隨時都會爆炸的狀態。
就剩下不規則延伸的儲藏貨櫃散在城市各處,特別在碼頭內散佈。現在,它們大多數都沒被使用,只是一列又一列,完全相同的小屋,門上掛著已經褪去,或辨認不出的號碼,每個安全地釘有一頂鏽蝕鋼鐵屋頂,斜度正好足以讓人們沒辦法舒服地走在上面,或睡在屋頂上。
「我們要找十三點六號。」戰慄打破籠罩住我們一個半小時的沈默。我們花了幾分鐘才找到。貨櫃或號碼的分布沒有實際的任何韻律或合理理由。我猜,貨櫃大概是設立在有空間的地方,然後給它第一個能用上的號碼。我們這麼快就能找到那個貨櫃的唯一原因是,布萊恩曾和瑞秋一起來這裡。當然,空間之廣和缺乏組織,是我們將錢存放在這裡的主要原因。如果我們甚至對知道自己在哪、朝哪裡去時都有困難的話,從我們這知道號碼、也從我們這拿了鑰匙的某個人,會花更多時間才找到它吧。
正在戰慄亂翻著鎖時,我朝我們所在的巷弄兩端瞥了一眼。除了一個叉架起貨機車停在不遠處,這裡寧靜得詭異。這就是個鬼城吧,我想。如果鬼魂存在,他們就會住在這種地方,這有太多悲慘、暴力和曾經發生過的死亡。
「該死。」戰慄打開門時說。我的心往下一沈。
我踮起腳尖往室內看了眼。貨櫃屋裡只有一塊寬闊髒污,在地板厚厚一層灰塵之中,角落裡還有塊深色污點。沒有錢。
「我投殺了她一票。」攝政說。
我的眉毛挑了起來:「你認為是母狗做的?她會就這樣拿錢跑路嗎?」
「如果妳在五個小時前問我,我會說不對。」攝政回答道:「我會告訴妳,當然,她是台自走砲,她很魯莽、瘋狂,她很容易被惹火而且還把那些惹火她的人都送進醫院……可是我曾說過她很忠心,就算她不一定喜歡我們……」
「她不喜歡任何人。」我插話說。
「對啦,她不喜歡任何人,這也包括我們,可是我們是她最接近朋友或家人的東西,排除她的狗的話。我不會認為她就這樣拋下這些。」
「她沒有。」媘蜜說:「這不是她做的。」
「是誰做的?」戰慄問道。他那空洞迴盪的聲音透露出一點憤怒的刃緣。
「一個假面。」媘蜜幾乎什麼都不想地回答,就好像她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地方:「某個人撬開了那些鎖。門沒被強迫打開。」
「一個反派?」我問。
「一個反派。」媘蜜重複我的話。我沒辦法分辨她是在澄清我所說的話,還是她只是在專注於其他事情,同時重複我所說的。「不只一人。而且他們還在這裡。」
一道柔軟掌聲回應了她。他拍掌,拍得很慢,毫無熱忱到諷刺的地步。
「真是傑出的推理。」那個拍掌的人如此大聲說道。媘蜜猛然轉頭,我從貨櫃退開幾步,來看得更清楚,是誰站在屋頂上。
他們一隻腳彎起來斜斜地站著,避免從屋頂滑下來,而他們倆穿著一模一樣的假面服。那些假面是在藍色男性緊身衣上誇示著寬腰帶緊束著腰間,有著緊貼皮膚的白色手套和靴子。他們的兜帽可以靈活伸縮,連接在他們頭上,僅讓他們臉露出來,他們各自還有裝備顯眼的白色單根天線。他們全身的顏色、他們的手套、靴子,還有天線上的球,都是泡泡糖粉紅色。他們的臉則是被過大的黑鏡片護目鏡遮住。
不過,除了他們的假面,他們也沒多少不同。其中一個身形骨瘦如柴,下巴纖弱而且還駝背。另一個人有著雕塑般的體格,高大且雙肩寬闊,他的肌肉的線條明顯在他的緊身衣下清晰可見。
「上人與黑客文。」媘蜜問候他們:「我沒辦法告訴你們我有多麼放心。好些時刻,我以為我們得有些擔憂呢。」
「放心吧,媘蜜,妳確實該擔心。」上人宣布道。他是那種宣揚、公佈、發表廣播演說和大聲斷言的人。就像戰慄的能力把他的嗓音扭轉成繚繞又非人類,上人的能力讓他的聲音聽起來像是動作電影預告片或深夜廣告的旁白男人一樣。不管有多瑣碎,每個他所說的話都被強化、過度戲劇化。彷彿某個在兒童電影裡的人過渡詮釋一個華麗騎士的角色。
我看向四周找著我認為會是抓耙子的東西。我最後發現一個天空的夕陽紅輝下的小小圓形陰影,正在太陽的強烈銀光上方。那是個攝影機,裝設在一個網球大小的金色球體上面。它能如一隻蜂鳥般移動,保護著自己,也不斷地攝影著。上人和黑客文把他們所有的假面活動都在網路上實況播出,所以人們能收看他們在做的事。我很確定他們有延遲時間,讓攝影機記錄的事件在一個半小時到一小時之後播出。
我能承認自己曾有兩次看了他們的直播,這也正是我知道「抓耙子」的方式。每次我收看時,總是驚訝那裡已經有幾千個觀眾。我停了下來,因為那不是讓人感覺良好的節目。他們是真正的落水狗,掙扎著想成功,這會令你對他們感到抱歉,直到他們做了些卑鄙的事。然後你會發現自己以一種負面的眼光看他們,鄙視他們,在他們失敗的時候慶賀。我感覺到自己像艾瑪、麥德森和索菲亞輕視我一樣輕視他們時,有點太超過了,這就是我放棄的最主要原因。
發現那毫無疑問捕捉了我們仰視那兩個反派的視野的攝影機後,我轉頭背對他們倆,我們的影子在身後拉長。不過,以我的能力我派了一群蒼蠅聚集在攝影機周圍。沒花多久時間攝影機就開始在我視角邊緣抽搐,就好像它試著甩開它們一樣。我在面具之後微笑。
黑客文皺眉後轉向攝影機:「這真的有必要嗎?」
「你搞了我們。」我回答:「我就搞你們的訂閱客群。」
媘蜜和攝政,各自微笑和咯咯笑了起來。只有戰慄保持安靜。他一動也不動,可是黑暗在他周圍就像添滿木柴的火焰翻攪著。
「今晚主題是什麼?」攝政喊了道:「你們的假面裝太糟糕了,我沒辦法直視太久到試著猜出來。」
黑客文和上人瞪向他。他們整個重點特色就是電玩主題。每個越軌的惡作劇中,他們都會選擇一個不同的電玩或系列,來以此設計他們的假面裝和犯罪行動。有一天是黑客文裝扮成瑪利歐丟火球,而上人穿成庫巴,他們倆闖進一個造壁廠來收集「金幣」。然後一週之後,他們又換成了俠盜獵車手主題,然後他們會開車一台馬力強化過的車子在城裡跑來跑去,搶劫ABB也揍了幾個妓女。
就像我說的。卑鄙小人。
上人走近屋頂的邊緣,用力伸出手指朝攝政指著:「你……」
他沒法說完話。攝政手臂朝旁邊一揮,然後上人便跌了跤。我加入其他人,在他臉著地,跌在貨櫃屋地基的地磚上時,往後退給出空間。
「太可惜妳已經搞爛了攝影機。」攝政評論著,朝我傾了頭:「我想看看這個變斷會在YouTube上得到多少點擊數。」
「下次先提醒我吧。」我和他說:「也許打個手勢?」
我們在上人掉下來時退離了貨櫃屋,在他站起來時又撤退了幾步。黑客文跳了下來,站在他旁邊。
「錢。」戰慄說:「在哪裡?你們怎麼找到的?」
「你們第五個隊員直接帶我們找到的。偶然幸運罷了,真的。」黑客文微笑:「至於我們如何找到她的……」他漸漸不再說了。
戰慄說話的音量低到不會傳到那兩個反派耳中:「他們對母狗做了些事情,他們拿到了錢。如果我們沒在這裡得到一個決定性的勝利,我們的名聲就完了。」
「沒設限?」媘蜜喃喃道。
「把他們留下來一個來審問。就決定是黑客文吧,因為上人的能力讓他即使被捆住還是很煩人。給他個機會,他就能想出該如何在任何事情上成為天殺的專業人士,而且這恐怕能延伸到,從繩索和手銬中逃脫。行嗎?」
「我要玩這個。」我答道。我驚訝於於自己的興奮程度。這是我穿上假面裝就想做的事情。當然,情況並不是我會選則的,可是要對付壞人們?
我在面具背後微笑,然後伸出意識碰觸蟲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