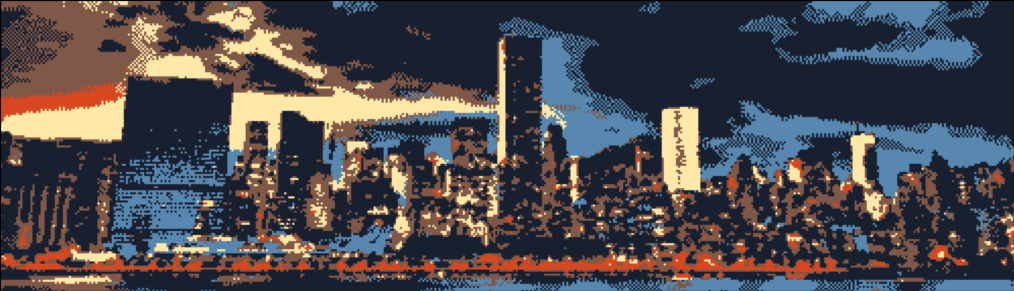 x
x
我逐漸瞭解,自己能睜開雙眼,不過好像忘了該怎樣睜開眼。我嘗試了下,立刻後悔這個決定。我其中一隻眼睛什麼都看不見,甚至在張開時,另一隻眼失了焦,我看見的圖像在能認別出來之後依然沒能搞懂。當我緊緊閉起雙眼,那穿過眼皮的粉紅光芒,宛若煙火在我的視網膜上爆炸。
當我試著拼湊出之前發生了什麼事時,我的想法像糖漿一樣移動。
「如果你們這小混漲有任何常識,你們會以為有那麼一刻,佔過我的上風?這是某個你們應該幹他娘地恐懼的東西。」一道嗓音絲絲。我花了幾秒理解那個聲音,遠比我應耗費的時間還要久。爆彈。
我開始感到疼痛。像被紙割傷,但爆炸成兩百倍規模,而且我每一條肌肉都有條割傷。我的皮膚有如針扎,逐漸感覺更多向是燒傷。我的每一個關節就好像從每一個的槽臼脫離出來似地跳動,人們在地板上踩出的無情韻律不斷打擊我那仍活生生的四肢末端。
我再次睜開雙眼,不成功地試圖調整視差。有三條紅染緞帶……不對。我看到三個重疊的景象。一條紅緞帶延伸過我面具側邊,蓋住我的鼻子,從面具邊緣滴落,筆直地碰觸地板。接觸到地板上的地方,已經有穩定擴張的一攤液體。我發覺這是自己在流血。流很多血。
「讓我手中拿著榴彈發射器躺著,街上還他媽的到處都有彈藥,你們根本就是活該。我肏,就在那邊抱抱安安心,就好像你們真的打敗我了?你們根本就是求被打嘛。」
我沒要這樣被解決。不想不打一場就結束。不過,我幾乎沒法移動,更別說行動了。我想做一些事情的渴望快要比穿過我整個身體顫抖輕敲的疼痛,還要更讓人難以忍受。我能做什麼呢?我的思想沒像之前那樣令人痛苦難耐地緩慢,但是我的想法仍陷入泥沼又太支離破碎。應該不用想就能知道的事情,都變得模糊、不確定又毫無條理。太多想法被遺棄,無法連接至其他所有東西。如果我移動時可以不弄痛自己,我會因為這份沮喪而揍了些東西。我結果握緊了雙拳。
學校。在學校有困難?我?那三人組?不是。我為什麼想著學校?在我這樣不爽之前自己在想什麼?我不知怎樣,想要反擊。爆彈,學校,反擊。我在試著連接起各個點子時差點因為挫敗而呻吟出來,而我就是沒法完成那個想法。最後我只怒噴了一口氣,對著這樣做所引起的痛苦皺眉。
「喔?穿蟲假面裝、沒什麼用的小女孩醒了。」爆彈嗓音在夜風中呼嘯宣告著。
戰慄在很近的距離,說了些什麼,我卻沒辦法辨認出來。
爆彈心不在焉回答道:「住嘴,無需擔心。我等下就會到你那了。」
我聽見了某些東西,然後看見一雙粉紅色的靴子出現在我面前,我眼前景象慵懶地飄移游動。
「今天過得太糟糕了?」她彎下腰俯視我:「很好。瞧,我其中一個新小兵是在捍衛者本部的員工。一個竜關著的地方的守衛,懂嗎?不是能釋放他的職位,但她從他那瞭解了完整的故事。我知道妳就是那位導致他被被送到那裡的小怪胎。所以妳今晚就有了特別待遇。妳能看看我要對妳朋友們做什麼事。我會從那個黑衣男孩開始,然後接著就是妳那位那邊失去意識的伙伴。我把他們黏在地上以策安全。一當妳的朋友們和死了差不多,我就把妳交給李鬼。政權交換的時候,他成了個非常乖的男孩,而且還一直煩我,要給他一些東西玩。妳有什麼話想說嗎?」
我僅是隨便聽著她。像祈禱文一樣,我腦子裡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的相同的東西。爆彈、學校、反擊。
「爆彈,學校。」我含糊說著。聽見我自己的聲音尖銳細微,比任何我之前幾分鐘見到的任何東西還要更令我恐懼。
「什麼?小蟲女想說什麼?」她彎下腰抓住我掛在胸前的裝假。用力一扯,她將我拉到半坐起的姿勢。被這樣扯來扯去根本就是折磨,但是這引起的痛苦將我的思想削得更接近清晰。
「學校。爆彈被當。」我回答她,我的聲音只比方才嘗試時更強壯一丁點而已。她護目鏡的黑紅色鏡片在我重組起想法,再次張口說話,試著聽起來更有連慣性時,深深瞪著我:「妳以為妳很聰明,還那樣被當?或是什麼?得第二名?連第二都沒有?」我成功咳出接近輕笑的聲音。
她就像我燒了起來似地把我甩開。當我的頭撞上地板,我差點昏了過去。我得爭鬥著昏炫的那拉引。包容痛楚吧。這會讓妳清醒。
隔了我一段距離,戰慄的聲音迴盪著。我只能聽出第一個字。是「她是」或「起司」。他笑了。我沒辦法瞭解他的意思,使我感到恐怖,而我也沒辦法瞭解為何我沒辦法瞭解他。我的聽力沒有應該有的那樣好,我已經知道了。但是這並非所有原因。還有什麼其他因素?
是扭曲。也許,那一個或數個爆炸傷到了我的聽覺,我沒法在他能力對嗓音的影響下認出他的言詞。光是想出這一點,瞭解我能夠思考,就讓我感覺一百倍更放鬆了。
「你是這麼認為?」爆彈對戰慄絲絲聲道。她的言詞比較簡單辨認出來,因為她的面具將聲音重組,好讓它們全然完美地清晰發音和單音調化,就算風聲絲聲模糊了也依然清楚。
她其中一隻粉紅靴踹在我臉上。讓我的頭移動幾乎比牙齒被狠擊還要更痛。她抓住我的假面裝,把我拖到幾呎外。被移動讓我全身所有疼痛提升了一個等級。從一到十,這足足有九點五。我做什麼都不會更痛,我便因此找到力量和意志力,向上伸手抓住她的手腕,這就是我能做到的全部了。她讓我落下,推了我讓我倒在身側。這個動作令我想吐出來。
看到戰慄,在我與暈眩和痛苦中細微呼吸喘息時,讓我更有紮實感。他被綁成半坐直的姿勢,靠著一個看起來像橫條黏逆金色絲帶的貨櫃。媘蜜跑哪去了?
「來看看在我給這黑暗神秘高個子盛情款待之後,你倆能有多聰明。」爆彈要脅著:「來看看……這個。這是個真實的寶鑽呢。二二七號。現在你坐好了。如果你想用你的能力,我會直接把這個塞到小蟲屁孩的喉嚨,然後引爆。我又聾又瞎,你也別想處於一個能阻止我把事情搞定的位置。」
她脫下她的粉紅手套扔到一旁。然後她從她袖子李抽出一把,看起來又長又細的剪刀。不過那把剪刀很鈍,並不鋒利。幾乎就像鉗子。當她把剪刀刀刃合起來時,咖擦一聲,尖端有個看起來就像一吋長的金屬藥丸。
「不需要手術,因為這不會是長期的。我要做的事是把這個塞進你的鼻孔,然後進入你的鼻腔…」她伸手進那陣從他全身露出來黑暗裡,摸索著他的臉周圍:「我只是需要把你的面具……頭盔……拿下來。好了。」
如果戰慄的面具備拿下來,也很難辨認出來。他的頭就只是一團大略是人形的影子。
她一隻手伸進那層黑暗中,另一隻手將那個膠囊推進黑雲中央。「就這樣進去……慢曼來,不想要過早啟動,只有放到深處它的效果才真的會很酷。看吧,我的二二七號是個令人歡欣的意外。我讀過一點遠璟的能力,想說也許自己能做個空間扭曲手榴彈。純粹意外地,我打碎了曼頓效應。或說,至少在我將這個手榴彈組裝起來時,不管自己做了些什麼,都越過了曼頓效應。你白癡們知道那是什麼嗎?」
她靜了下來,響亮地折了折手指,將看起來像剪刀的工具直接從戰慄的臉上抽出來。「那就是保護操火能力不煮沸你的血的小規則,限制大部分的能力影響人們的身體。或者說,不管你想依從哪個理論,這就是你的超能力只作用於有機、活物,或任何其他東西的法則。
「所以想想看吧。只作用於活生生的物質的空間扭曲效果。我引爆這東西,距離那膠囊三呎內的所有活物就會被重新塑形、扭轉、縮小、爆開、伸展然後彎曲。這不會真的殺死你。除了無視曼頓效應之外--那是第二個最棒的特色。所有東西都仍連接著其他東西。完全不致命,可是會讓你希望,在自己所剩所有悲慘日子的每一秒鐘,還不如死了更好。」
別光躺在那邊看啊,我想道。做點什麼啊!
「咖擦一下,嘶嘶,你就會醜得夠令象人也感到羞愧。結果有了四倍大的腦袋,全身有像腫瘤的凸塊,五官每一個都會畸形怪狀。這也會重新塑形你的腦袋,可是這通常只有些輕微到中等的腦傷害,因為我將它校准,專注在外部特徵上。」她笑了出來。那是種,乾巴巴的、重複的、非人類聲響。當她再次開口說話,她清楚地將每一個詞分開來發音:「無法回復。而且。他媽的。好笑。」
我意識延伸觸及我的蟲子,可是沒辦法將自己的想法匯集起來,足以給它們任何複雜命令。我只把它們叫來我身邊。我還得去幫忙戰慄。
我的多功能緊身鞘。我緩慢地,同時兼顧不想引起她注意的需求和無法快速移動又不引起那難以置信的劇痛的無能為力,我將手移到身後提醒自己那裡還有什麼。
防狼噴霧--沒用。這能辣燙她的皮膚,但是護目鏡和面具能保護她的臉的安全。她有被抓傷流血,所以也許我能噴她的皮膚……這不會對她的傷口來說很有趣,但這能拯救我們嗎?
紙和筆。手機。零錢。不行,不行,還是不行。
甩棒。我沒有力氣,或需要的槓桿作用、空間來延展揮動甩棒了。
艾比筆。沒多少用處,而且我不信任自己的力量或手眼協調,來同時能幫她注射還要按下注射器。
我的多用途空間裡的東西就這樣了。我撐起自己移動時,讓手癱軟地吊在我背後,也讓我的手指撥開些東西。
刀鞘仍在我背後一小處。我之前把它綁在我背部最下方,同時能被我的裝甲蓋住,也很容易拿取。
刀子能行。
爆彈調整的剪刀鉗東西時發出輕微的喀擦聲,然後從戰慄的鼻子將它抽出來。它沒再夾著那膠囊了。
「這應該會很不錯看喔。」她心滿意足地看著他,在我能決定好要捅或割她身體何處時直直地站著。我不想殺人,但是我必須阻止她。為了戰慄。
我的手仍在我身後,以刀刃尖端指向我掌底的姿勢抓住刀把。我微微轉變身體姿勢,好讓我取得更好的角度。
「嘿,小蟲女。妳在那邊做什麼呢?模仿在乾地上的魚亂跳嗎?注意一點吧,當他的臉的好幾部分開始腫起陰影疙瘩時,看起來真的會很酷喔。」
我試著組織起一個回覆--一些會讓我將要做的事更為刺痛的話語--可是一陣虛弱感掃過了我。黑暗開始再次,蔓延進我的視野邊緣。我打直雙腿試著讓自己有更多疼痛,逼迫自己再次警醒,而這卻無法將黑暗褪去。戰慄在用他的能力?我看向他。什麼都沒有。我就只是正在昏過去而已。
我現在不能暈倒。
腳指戒。
沒說出詼諧的回嗆,沒有譏諷或甚至一道憤怒吼叫,我將刀下插在她的腳尖端。我同時有了兩個想法。
我打重某個堅硬的東西。她的腳或靴子有護甲嗎?
我有打中正確的那隻腳嗎?媘蜜從沒說她哪隻腳有腳指戒。或者兩隻腳都有。
一波黑暗沖過我的視野,也如它襲向我時迅速消逝,讓我只微弱地意識到她的尖叫。暈眩感又再次膨脹,而那就像是我的意識要溜走,需要吐出來的感覺逐漸增強。我方才正要嘔吐,可是戴著面具吐會梗塞住臉。如果我背貼地躺下,甚至會被悶死。
戰慄說了些什麼。沒辦法辨認出他說的話。聽起來很緊急。
有個女人對著我的耳朵尖叫。反覆著咒罵、威脅著她將要對我做的恐怖的事。失去意識的彼岸正召喚著我,誘惑著我的、安全的、毫無痛苦的--毫無威脅。
假使這就是知覺喪失。我可能正在死去,這令人心寒的想法,給了我極短暫的清晰。我用力專注於扭曲影像與聲音結合的混亂、我所處的位置,還有人們對我說的、吼著的話。
那個女人滾到我身旁的地面。當她踢出她的腳,一滴濺出的血弄髒了我面具上的一個,我能看清楚的鏡片。這女人名字叫什麼去了?爆彈。刀子的最尖端依然插在她的腳曾在的人行道磚上。那就是我打中的堅硬物體:磁磚,而不是護甲。地上流了很多血。是她的血。她的靴子上有一點,粉紅色與鮮紅。兩隻較小的腳指頭上塗了指甲油,粉紅色與鮮紅,躺在亂七八糟的血灘之中。
我試了卻又無力把刀子拔出來,可是這只嵌進地面四分之一吋而已。這樣施力讓我大口大口喘氣。每一次呼吸都讓我感覺像吸進了帶刺的纜線,還有熱融金屬壓著我身側。我祈禱著想嘔吐的衝動能消失,但也知道那不會停止。
戰慄。他剛在說什麼?我幾乎無法理解爆彈清楚發音的機械聲調了。瞭解戰慄則有十幾倍難度。就像另一個語言一樣。
流泥達倒?刀?那把刀。他需要刀。
我讓自己正面倒下來,臉正朝地面,好讓自己不會被嘔吐物噎住。握住刀子的手留在那,可是我的手臂彎曲的角度很不妙,引起我一陣刺痛。我手腕和手肘尷尬地扭著,緊緊扯回自然的姿勢。我抵抗著放手的衝動,讓手繼續抓住刀柄。
地面比我先放棄,刀子鬆脫了出來。我伸直手臂,向前伸出去,刀子就被握在我的黑色手套之中。我的眼神從刀子向上看,戰慄模糊的形象掙扎著要掙脫綑綁,是我在黑暗和失去意識的仁慈伏上我之前,看到的最後一個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