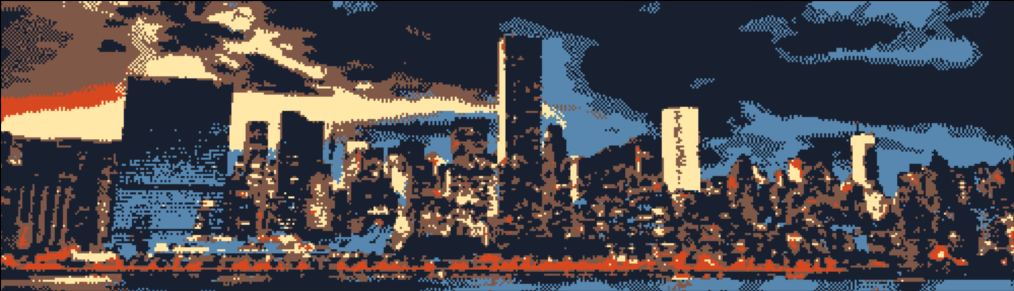 x
x
蛇蜷堅定抱持著,一個人不會太偏執的哲學。每天每刻都是唯妙的平衡,預測從各個可能的角度攻來的任何無形威脅可能,和部下說話時或單純早上起床時都一樣。
在一個現實中,他平安地安頓在地下基地裡,穿了假面服,自己和數組沉重鐵門間,有不下二十位重裝備士兵。他花了整晚閱讀,追蹤新聞和他的股票。他所在位置只有那些為他工作的人知道,他們每個人的薪水都多到,就算他們有理由攻擊他,他們「同事們」也有動機出手阻止。
第二個現實裡:他在一個普通、稍微老舊些的房子位於城市西南端末。穿著浴袍走到室外,拿起報紙和信,停了下來朝鄰居和他們那兩位從家出來的女孩揮手。這裡沒像其他地方一樣受洪水影響,可是學校還沒開始運作,所以母親和父親會在這段短暫時間點中,把他們的女孩們帶去工作。
他回到室內,沖了澡,接著穿上直鈕扣襯衫、卡其褲和一個絲綢領帶。他坐上自己的四年車齡普銳斯【Toyota Prius】開進城裡。在被迫要繞過被摧毀的道路、倒塌的建築,還有工地中,普通的十分鐘車程會花上他四分之三小時,離開房子所在的死巷之後他立刻與其他駕駛在一段恆久塞車潮裡一起移動。表面上,他就是個普通的男人正離家要去工作。他的身分,徹底是捏造出來,他在一家公司裡有真正的職位,健康、稅、牙醫、房貸的記錄都可以追到十年前。
那位遇到他的士兵,是其他人所稱呼的怪胎。沒有隊長會想在他們的戰隊裡有那男人,他的嗜好讓他無法在公眾部門中被雇傭,而蛇蜷只是唯一一個能夠、會提供怪胎渴望的「款項」,這件事使他忠誠到人能忠誠的極限。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鉤餌、惡癖或某種在原始、渴望的等級上所需的事物。某些時候,那東西需要被創造,或培育出來,好讓它之後能被親手餵養。那些被這種事物驅動的人──所抱持的劇烈渴望特別接近表面的人──正是蛇蜷最愛的人們之一,在有用的人之下卻也非常接近了。那些同時有用又極渴望某些蛇蜷能提供的東西的人呢?
那麼他們,就是世界中的行旅人、爬蟲和戰慄等人。
財富對其他任何、所有人就已足夠了。
怪胎一直是唯一一位有機會揭露沒戴面具的蛇蜷的人,就值得買下他的衷心。那男人等在一輛白色箱型車前座,雙眼看向前方,直到他聽見車輛後方車門上的三聲敲響。他按下一個按鈕,開門讓蛇蜷進來。
一當他進入箱型車後座,座位之間有一道帳壁把他隱藏在怪胎視野外,蛇蜷脫去衣服,整齊地摺好。他穿上假面服──他那第二張皮膚。一條拉鍊藏於裹住假面裝的身體繞到頭部的長長白蛇上。他把布料拉到身邊,將金屬垂片塞進腳踝布蓋裡。假面服的布料讓他能透過布視物呼吸,但外面的人在最明亮光線中,仍見到不透明的黑灰色。
這些日子裡,他花費愈來愈少時間在平民的身分上,到他仔細考慮要把它全放下。等到基地徹底建起,他就能全時間當蛇蜷。不過,現在來說,只要有一張床,還有一個可以遠離工程噪音的地方,這種策略就是必要的。他坐在車輛後座一張座椅上。
從外面的人看來,怪胎就是個普通勞動工人開著一輛電工箱型車進入工程地。蛇蜷的地下基地正好落在鬧市區中央的距大湖水寬度之外。若窟窿多延伸四十、五十呎,就可能會造成比內側牆壁裂痕要更嚴重的傷害,耗費蛇蜷數月而非幾天的時間,會花上幾十萬元而不是幾千元完事。
怪胎將車開到斜坡下,進到停車場裡。他在蛇蜷下車時和箱型車留在那裡。
蛇蜷進入車道最低處、停車場最隱蔽的角落,走進一個在金屬籠子後方,有套電線系統的房間。他打開房門走到籠子裡,繞過電箱,穿過進入那隱蔽走道,他走上沉重的庫門──那標誌了他地下基地的入口。
即使在他進入室內後,兩個員工正等待和他打招呼,一個他的戰鬥分遣隊隊長立站待命,他依然很小心翼翼。另一個現實之中,他從電腦前站了起來,走進自己的旁邊房間。他在走廊上停止腳步,凝視那躺在行軍床上的女孩。她穿著白色衣物,除了肋骨胸口起伏之外沒有動作,她雙眼睜著。
「早上了,寵物。妳知道我要問的問題。」
「早上了?」她問道,抬起頭。「我感覺自己才剛吃晚餐。糖果呢?」
「不,寵物。現在太早了。請回答我的問題。」
她躁動地,回答:「這裡之後一小時會有任何問題的機率是百分之零點二五二的機率。午餐前會有任何麻煩的機率是百分之三點七四四一。」
「好女孩。」他說道。
就這樣,他將自己整晚熬夜、研究新聞、跟上國際金融趨勢、追蹤他的戰隊最細微的行動細節的那個現實,塌落下來──他會用自己的能力確保重要任務成功。那個現實迅速褪去,只留下他有整晚睡眠、吃了份豐盛早餐,和怪胎開車進基地的世界。只有記憶和知識殘留。
他站在自己的員工和士兵面前,他再次將現實分裂;在消除一個存在與創造另一個之間,只隔一次心跳。
他時常納悶自己是否真的創造了現實,或那單純是在他的認知裡,預知自己的行動所影響的未來延伸事件。他問過了他的媘蜜,她也沒有答案能給。
他痛恨這種時刻──在他獲得他的寵物與她所提供的保證之前的時間。當他剛開始重新使用能力時,他太過靠近另一個自己,就是他最脆銳的時刻。這很可惜地無法避免,除非他找到方法擴展出第三個世界。不過他理解有危難的機率是微乎其微,他的寵物就算想,也無法對他說謊,他依然費心地盡可能拉開兩個世界。
第一個現實:「隊長們,跟我來。八十八帝國分裂了,我會指引你們開始一系列打擊,在兩個派系能融合為一前,確保我們盡可能造成更多傷害。」
另一個現實:「我希望調查基地。隊長們,待命。」
兩群人馬前往不同方向。他其中一個自己和部隊一起行動,走下金屬階梯到下層,另一隊移動到另一個方向,穿過金屬走道,兩個員工趕緊跟上他的長步幅。
他看了眼正在發展的基地。大量的板條箱和紙盒正被拆開,為執勤士兵們弄的上下舖床,一個完整配備的醫護所,要組成廚房的備料和設備,還有無數把武器。這都正在成形,精妙細節只出現在正確的角度和整齊組織起來的疊疊箱中。
他擁有那家建造布拉克頓灣和周圍城市的地下避難所的公司。將基地的細節隱藏在施工地,就是在正確的時間與地點攔截情報那麼一回事罷了,付他自己的錢而不是用城市的資金,控制被回報的內容和回報對象。他的寵物曾向他保證,近期不會有人注意到不一致處。
「行旅人的房間。」這比起指令更接近疑問,但它仍要求答案。
一個穿汗衫、戴小圓框眼鏡的男人,比特先生【原文Mr. Pitter】,說道:「辦好了。單獨房間,裝好家具、廚具和衣櫃。需要一些細微修改來讓房間對殘疾人也更容易使用,但是他們全都可以在今天搬進去了。」
「還有容納設施?」他問道,不過他已經知道答案了,是從在他整晚待在設施裡時所知道的。他在幾小時前就聽見了工程的噪音,讓他得知正抵達的人們。
「庫門在昨晚才裝好。她很……」比特先生頓了下:「很躁動。我們打給了魔閃師讓他進去和她說話。他現在就在這了。」
「我會和他們談談。」
「是的,長官。」
他不喜歡與人們互動,沒有在假如談話沒照他所想地進行時用能力創造或消除現實的條件,特別像行旅人或暗地黨那樣重要的部下。這裡,他很安全。他的另一個自己正對幾個行動、攻擊目標、要注意的人們下命令,由他耗費整晚追蹤的捍衛者與監護者的部署與巡邏模式情報支援。
他允許比特先生在他們前往行旅人的公寓時,領在前方。那男人很矮小,謙遜,又很普通。他是位註冊在案的護士,又有作為褓姆和一對重病非常的孩子照顧員的八年模範記錄。接著他發現自己妻子出軌,有試圖和她離婚。她決定離婚協議無法接受,那女人便動手拆毀他的人生,毀掉他的生涯、友誼、家族關係和所有一切,放出指控又安設了最糟糕的罪行證據。是那類指控和嫌疑對一個男性褓姆來說,會讓人一直疑神疑鬼。
比特先生是那種,同時很有用又得用比貨幣更強力的東西買下的人之一。他會確保行旅人舒適又妥當裝備。更準確的是,他也會照顧黛娜,確定任何所有用藥都很乾淨且妥當施打,那女孩會被維持在最佳健康狀態。他所有要求就是要他妻子消失,那女人對他造成的混沌與麻煩,在她死去後隱密地被解決掉。他從破碎的男人,變成一個無所畏懼地執行本分的人,連蛇蜷也不禁為之一頓。
比特先生敲了門,等著。在門打開前幾乎過了一分鐘。
魔閃師站在門口,沒戴面具。他皮膚色調較為暗沉,讓他的種族十分模糊,那男孩膚色比高加索人深,雙種族似的,有著中東或東印度群島血統。他深色頭髮很長,落及雙肩,帶著美人尖的鷹勾鼻讓他的臉看起來有些嚴厲。他雙眼,普通地銳利,睡眼矇矓。
「你真的很虐欸,比特先生?因為諾埃爾【原文Noelle】需要,我早上五點就被拖到這裡,但又在三小時之後叫醒我?」
那位「褓姆」並沒有回應,卻站到一旁,讓魔閃師更好看到蛇蜷。魔閃師靠在門口上下打量他的老闆,用指甲撿出眼角眼屎。「媽的。好吧。」
「謝謝你。」蛇蜷回答:「我想要和你樓下的,朋友們聊聊。過往經驗建議最好讓你當中介人。」
「我不知道那會不會是好點子。」
「還請讓我知道。你希望我等你洗好臉、穿好衣服嗎?」
「假如我們只是和她說話,然後假如你有其他事要我做,我之後大概,會直接回去躺平。」
「如你所願。」
魔閃師套上了一件黑浴袍,腰間綁好,走出來到金屬走道。
「有什麼是我可以跟她說的?」魔閃師問道。「有任何鼓舞人心的消息嗎?」
「沒有什麼可靠的。我之前傾向要引介暗地黨的媘蜜到這事上,詢問她的意見。也是說,如果她沒已經有些現在情況的概念的話。不論如何,她的才能都可能挖出一些我們錯過的細節。」
「之前傾向?我認為她現在,是沒辦法了吧,是因為在醫院所發生的事?」
「類似的事情。她有告知我她隊上現今的困境,也請求我別讓她分心或給她任務,直到事情安定下來,『不管結果如何』。就是她說的。」
「那真的不是會帶給諾埃爾希望的事欸。」
「不。那並不是。」
他們回到走廊上,然後走下樓梯。一扇庫門,二十呎寬,鑲進水泥牆壁中。庫門遠高過他們,甚至比蛇蜷高三倍。
蛇蜷站到一旁,朝那庫門左側的小螢幕和鍵盤一指。
魔閃師碰了鍵盤上的一個按鈕:「諾埃爾?妳在嗎?」
螢幕一閃。一個女孩的臉佔滿畫面大部分面積。她的臉旁有著棕髮,髮色油膩,而且雙眼底下也有著黑眼圈。她雙眼在看向她那側的螢幕時動了下,但沒應聲。
「嗨。」魔閃師說。
「嗨。」她的嗓音有些粗糙音質,就好像她剛嘶吼到沙啞。
「蛇蜷想和妳說話。」
一頓。「好吧。」
蛇蜷走向前好讓他和魔閃師一起分享攝影機畫面。「諾埃爾。我很抱歉施工吵到妳。我們不應該在這麼晚的時候工作的。」
「你把我鎖了起來。」諾埃爾指控他。
「是為了妳的安全,還有我們的。」蛇蜷說。
「妳之前有同意。」魔閃師告訴她:「我們談過這事了。妳要求我們這樣做的。」
「我知道。我、我之前不認為裡面會這麼幽閉。或孤獨。我發誓我感覺有了幽閉燒【cabin fever,又稱機艙發燒】,而且才只過幾小時。」
魔閃師張開了口,接著又閉上了嘴。當他總算找到詞語時,他說道:「妳隨時都可以打給我。」
「除了你在工作的時候。」
「妳到時候也能和奧利維說話啊,或者是比特先生。」
「奧利維還是忙著和你們說話啊,而且我很怕比特先生。」
蛇蜷在面具後抬起了一邊眉毛,瞥了比特先生一眼。那男人沒有反應。
魔閃師風度地沒當比特先生的面評論。他沉靜地,說道:「我們正在處理別的事情。」
「你現在已經弄了一個月了!」她開始吼道,那只增加了她嗓音中的沙礫啞聲:「修好這個啊!治好我!是你把我弄成這樣的,克勞斯!」
「諾埃爾。」蛇蜷說道,控制自己的聲音:「魔閃師不該被責怪。只要一有機會,我會邀請一位我的員工和妳,還有其他行旅人談談。她的超能力會提供線索。我也連絡了康奈爾的超亞人類研究總部。那有一位這個領域中的專家。」
她的尖叫透過對講機系統透出:「那只是更多人弄我和打針和理論啊!你答應我們你會治好我!」
像要強調她的論點,有一道使骨頭震顫的衝擊打在庫門上。幾乎每位下層裡的士兵站起來或轉頭面對那扇門,雙手放在槍上,灰塵從水泥牆接觸天花板之處噴灑出來。
這讓人不爽。這段對話不會有任何結果。至少他知道那件他想調查確認的事:她惡化了。他使用能力消除那狂怒女孩所在的現實,留下那個他正在和士兵說話的那一個。
「……地黨正在忙,所以你們會由行旅人間接支援。赫洛斯隊長?你的小隊最快什麼時候會準備好?」
「我們隨時都可以出動。」
「很好。」蛇蜷說。「準備好,我會在一小時之內給你命令。」
「長官。」
蛇蜷轉身,讓隊長們去做他們被分配的任務。他瞥了眼比特先生:「我相信,行旅人的住宿間已經設置好了?」
「是的。我們剛在半夜的時候把重鐵門裝上。諾埃爾焦躁到我們必須打給魔閃師來讓她冷靜。」
「我知道了。」
「如果你想和他說話,他還在這裡。」
「讓那男孩休息吧。他一定累了。」
「是的,長官。」
「確保那女孩這個早上有雙倍份量的口糧。」
「那花費……」
「是我的考量。考慮到她睡覺被打攪,她很可能會……情緒不好。要確保她沒其他事情抱怨。還有比特先生?」他頓了下:「裘馨進來就和她講工程的事。我想強化那扇在下層的門。把牆壁向內擴大,然後如果必要,就加上第二扇門。把任何工程都安排在白天,好讓我們不會再打斷她的睡眠,但我也想要工程盡快完成。」
那男人點了頭,正確地將這道命令解釋為解散,趕緊離開了。
這讓他只有一個助理留下來跟在他身後。克蘭斯頓。「有緊急事嗎?」
「沒有,長官。你買進的產業仍在災後掙扎,但是我們收到了保險金……」
「很好,我們之後再談。」
「遵命,長官。」克蘭斯頓趕緊離開。
蛇蜷回到設施裡距離入口最遠的一端,進到他的艙房。他停在電腦前確認電子郵件還有最新的新聞。沒什麼關鍵的。
他分裂了現實。在一個現實中,他留在電腦上。另一個,他進去那留給他的寵物的房間。「早安,寵物。」
「早上了嗎?」她呻吟了一聲,坐起身。「我以為自己才剛吃完晚餐。糖果?」
「你知道我的早晨問題。」
他已經知道數字了──在她喋喋不休講出數字時,他注意到它幾乎沒有改動──但如果他一直取消掉他詢問任何早晨有無危險的現實,因為再問會多餘而不再詢問時,她就不會記得。就算像她這樣的強力心智也有她自己的限制和界限。
「我的大計畫成功機率,無視使用我的能力?」
「百分之七十二點二零零二一。」
這真令人愉悅。那是他在接下來數天、數個月,用上他的能力,就可以提升的數字。相當有趣,那數字比利魔維坦攻擊之前更好了。
「暗地黨的問題會解決的機率?」
「不懂。」
他皺了眉。又是另一道限制。她需要能視覺化出場景。「暗地黨在我的計畫成功或失敗時,有多可能繼續在我底下工作?到十分位?」
「六十五點六。可是他們不是同樣的暗地黨了。」
「喔?」他摸了摸他的下巴:「這個新隊伍和舊隊伍相比,我的計畫成功機率如何?」
「我不懂。我的頭開始痛了。」
「再多一、兩個,寵物。假如隊伍轉變,我的計畫更可能成功嗎?到十分位。」
「對。百分之四點三對十一,要看誰留下和誰離開。」
「再一個問題。我有多少機率找到行旅人狀況的解決方法?到十分位?」
「九點五。糖果?」
整整比利魔維坦攻擊之前低了百分之七。是關鍵人士死去或離開了這城嗎?或者他正思索的理論是正確的?利魔維坦來這裡,除了攻擊一個已經飽受折磨的城市的機會,還有其他原因?
很難無視,從利魔維坦他抵達時,就逐漸靠近這個地點──也就是那女孩已經被安置的地方──這個現實。行旅人也曉得這件事,相當擔心,便打給他。
也許,當他把她介紹給諾埃爾時,這事可以問問媘蜜。
「感覺好難受。好想吃糖果,我知道自己會想吃糖果,也有看到我會想吃。愈來愈強了。」
更低了百分之七。到那時,他在他們身上所投資的資源不足以賺得他們的忠誠嗎?
「我知道假使自己沒吃的話就會生病,我看得到,知道那是什麼樣子,慢慢生病,然後那也快要發生了,機率愈來愈高,感覺更真實,就算只有九點二……」
「寵物,妳會有些糖來讓妳撐過去。」蛇蜷打斷她,盡他所能地做出可靠的語調。他幾乎不可能藏起自己被想法所引起的惱怒,可是她被自己的困難分心得,她幾乎沒注意到他。
他正在成功,不過計畫稍微被現在的狀況拖延。潛在敵人們被分裂或減少了數量,整座城市都更脆弱而可被奪取。勝利如此靠近,他幾乎可以嚐到勝利的味道。
也許值得慶祝。蛇蜷穩住自己的脾氣。太期待自己的話,他又有這樣獨特的天分,就不公平了。
這確實是個昂貴的天賦。就算依靠他的能力,以一種千里眼和預知能力者也無法偵測的方式玩弄市場,他仍花費了數年時間才賺回來。這是場讓人抓狂、挫折的力爭上游,當他已經構想著自己要啟動的計畫,又得延後,而且就連現在,他還欠了一份人情,也空忙一週。他沒辦法確定自己是否夠強、夠安全,能在他們要求過昂貴的代價,或花上他太多時間而對計畫造成關鍵性損傷時,反擊回去。
他取消自己站在寵物床邊的現實,發現自己還在電腦前。最好留下寵物沒太疲倦的世界,以免他那早晨想問更多問題。
他創造的世界並非真實。它們比一個特別生動、精準的夢境還要真一點點。享受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沒有任何他願意接受的事之外的後果?假使他不沉迷其中就太不合理了。只要有機會,任何人都會想得要吧。
這種自娛讓他專注、徹底冷靜。在處理那個行旅人女孩讓他感到煩躁後,他需要這麼做。
他碰了電話上一個按鈕:「比特先生?到我辦公室。」
「遵命,長官。」應聲如此響出。
他正在完成目標的邊緣之上。靠這麼近,他的能力卻失敗、意外選成錯的現實,或他另一個自己被意外或惡意所殺,強迫他與這些懶散的娛樂活下去,就會成了個可笑的悲劇呢。現在,他不會再碰寵物,也不會接觸他的超能力部下。在他這樣接近目標時不會接觸。
他桌面圖片一閃,讓他最底下抽屜彈了開來。
比特先生進到房間裡了。「長官?」
其中一個現實:「我的寵物需要她的『糖果』,請給她,低分量。」
另一個現實:他電腦滑鼠一點,遙控鎖起了門。比特先生轉身,有些驚懼,試了下門把。
至少現在,就算有他另一個現實的當保險,他也不會做任何他必要的話就無法解釋的事。他不會讓自己抱持,無法取代任何人的這種想法。比特先生?可替換。
再說,並不存在過份懷疑這種事。
#蛇蜷 #黛娜
ns18.224.21.144d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