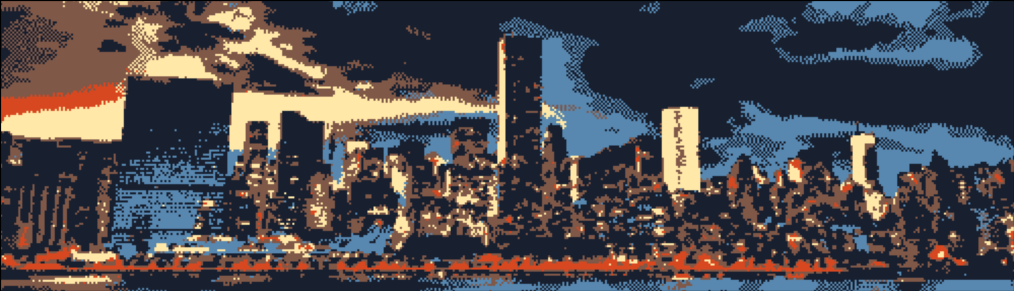 x
x
純潔漂浮在碼頭上方,成了在藍灰色天空的背景之中一團特大號螢火蟲。她停在一棟蓋了一半便被遺棄的房子上空,一台小起重機在那房子正中央外。一棟我認出,是母狗住處的房子。她的即興狗兒收容所。
「布萊恩!」我喊出聲。「你會想來看這個!」
攝影師試著把純潔的鏡頭焦距拉近,卻只讓跟隨她的鏡頭炫光效果增強。
他及時拉回來焦距來看她的動作。
從她手掌中射出的數道光束並非筆直。它們有一點螺旋狀,變形成一個大略的雙股螺旋。射出來的東西比純潔身高更寬,扯裂那棟建築,讓起重機倒塌在牆壁上。她將光束轉到牆壁上,將它徹底摧毀。
她花不到一分鐘推平了整棟房子,把所有比人行道高的建築結構都碾成齎粉。
她頓了下,懸浮在塵埃、微粒和隨她能力而起的光輝中。她轉了方向,射向另一棟最接近的房子,朝建築接觸地面的角落引了一道更小、更緊束的光線。她射中另一個角落,接著將搖擺光束揮穿過地面層,摧毀任何建築裡矗立的柱子。那棟房磚牆脫落、掀起屢屢塵埃,雜亂倒塌。
甚至那房子未落地前,她已經開始對另外兩棟做同樣的事,兩棟各受一道光束。
「那裡面有人嗎?」我問,對這個想法和這女人能做到的事同時感到恐懼。「另外那兩棟房子呢?」
布萊恩站在他的沙發後面,看著。「那裡可能曾經有,可能現在也有。」
我得趕緊推翻自己的矜持了。我站起,把上衣脫掉,上身只穿胸罩,確認自己背對布萊恩。脫掉我綁在自己腰上的長袖運動衫,然後解開假面裝的袖子。
「妳在做什麼?」
「準備好。」我將手臂穿過其中一個袖子,把手指套進手套。
布萊恩繞過沙發,我趕緊拎起假面裝的上半部分,抓到我胸口遮住自己。他將雙手放在我肩上,手中力道足以將我按下、坐好。我僵硬、不願意地,順從了。
他雙手拿開的速度可能比一、兩天前更快一點點,將雙手塞進他的口袋。我有意識地向前駝了背。
布萊恩深深吸一口氣。「那不是妳的工作。」
「他們是因為我們才這麼做。」我換了抓住假面裝上衣的姿勢,空出一隻手好讓自己能指向電視。攝影師正在從那場面撤退,攝影機畫面隨他動作劇晃時模糊。純潔夷平了更多房子,那個光點也正朝他大略的方向移動。
「因為蛇蜷,不是我們。英雄們才是要負責的人。」布萊恩反駁。
「他們可能傷害無辜的人。」
「考量到他們是誰,我很確定他們已經傷害無辜的人很久了。」
我轉頭對布萊恩皺眉:「你知道我指的是什麼。我們……」
「暗地黨。」一個女性嗓音切斷這對話。「捍衛者。給我記好。」
我們頭都轉向電視機螢幕。攝影機展現一道約略能看出是張臉的耀眼光線。畫面一變,我聽見她命令道:「拿著。」
攝影機穩住,從地面向上拍,聚焦在純潔的臉。我猜是攝影師在地上。
「你們將世界上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東西從我身邊奪走。」她的嗓音平坦,毫無情感。「直到她回我身邊前,這都不會停。我會拆毀這座城市,直到我找到你們,或你們來阻止我。我的部下會殺掉任何人--所有人--直到這件事平定。我不在意他們有沒有純粹基因。只要他們不和我們結盟,就已經錯過機會了。」
她彎下腰拿起攝影機。影像同時狂暴搖晃,純潔說:「深夜,迷霧人。展示下。」
攝影機被穩住,畫面固定在穿灰黑假面服的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上,他們服裝各有著頭巾和斗蓬。他們倆身後是一個蒼白到不自然的白髮年輕男子。
那身穿灰衣的男人氣化為一團騰滾灰白霧氣雲朵,朝攝影機移動。純潔飛起,越過攝影畫面,讓攝影機聚焦在攝影師。當攝影機升起,畫面的視野遼闊開來,我能看見在一旁的十字軍,他雙手交叉在胸前、靠著一面牆壁。
當霧氣包裹住攝影師時,深夜向前邁步,消失於霧中。可是事情的時機產生歧異--太快在她進入霧之後發生。迷霧中發出一道殘破不堪的尖叫,接著血液噴出霧氣,在周圍的道路上灑上好幾十條鮮紅污點。
那迷霧像有意識一樣移動,再次凝結成那個男人。他徹底將自己組合起來時,距離屍體倒下的地方差不多有六步距離才有幾灘血。而深夜,站在道路正中央。迷霧通過的地方沒有屍體,沒有衣服,沒有血跡。
「我們不是ABB。」純潔說,毫不費心於轉攝影機回到她自己:「我們在超能力和數量上,都更強。我們有紀律,而多虧你們,我們沒任何東西好失去了。我會把我的女兒奪回來,而且也會得到我們的賠償。
純潔丟下攝影機,畫面在攝影機朝地猛衝時慵懶地轉動。畫面中有極短暫的光痕標誌著她的離去,之後攝影機撞上地面,電視畫面便成全黑。過了一陣子,「BB4新聞」商標出現在藍色背景的畫面上。
「該死。」布萊恩說。
「所以。假使你沒要去追他們,去救人。」我無能將嗓音中的苦澀全藏住。「也許你會為了我們的名譽,在我們被這樣點名之後出動?」
「這不是……泰勒,我也不想要其他人受傷或被殺。我不是一個打算傷害人的反派。我只是比較實際而已。」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們現在聽到這件事,要做什麼?」
「我們會打給莉莎。或者妳來打,我在妳打電話時處理妳的耳朵。」
我點了頭。抓住機會在他拿來急救箱時,把上衣穿回來,拿來我的手機。布萊恩用時鹽水和一個濕棉花擦了我耳朵周圍,我撥了莉莎的號碼。響第一聲她就接起。
「檸檬J。」我對她說。
「大黃蜂S。」她回達。「沒有立即危險,可是情況看起來不怎麼好?」
「對。」我回應。
布萊恩將棉花棒放到一邊。棉花棒上有我的乾血碎片。他準備了另一根,繼續工作。
「妳看到電視上那個了?」我問她:「等等,我要把妳放到免持聽筒上給戰慄聽。」我用代號以示安全。我弄了下鍵盤,讓手機轉到免持聽筒模式。
莉莎的聲音聽過低品質喇叭後很像錫。「純潔?我看到電視了。伊我看來,兒保機構和一個假面分遣隊在她出外工作時到她家裡,帶走了她的寶寶,甚至她是在有機會聽到那個電子郵件新聞之前。媽媽熊抓狂了。」
「媘蜜。」布萊恩說:「妳跟蛇蜷說過了?」
「蛇蜷說他直接告訴凱薩他自己才是負責那封電郵的人。我相信他。假使純潔和凱薩的其他部下不知道,凱薩不是認為不適合告訴他們,就是故意向他們隱瞞。」
「什麼?他幹嘛那樣做?」我把手機拿高到我嘴邊問她。
「以我的扭曲想法來說這很合理。」布萊恩幫莉莎回應。「讓他的人相信我們才是罪魁禍首,用純潔的隊伍追殺我們和捍衛者。鐵血狼牙因為母狗,已經恨透我們了,所以他也會跟風。凱薩讓他們來處理我們,使用那股憤怒和仇恨來無底線地折磨我們,或當方便時機出現時,他才告訴他們真相,將嗜血憤恨轉向蛇蜷。他的人不會變得比現在更可怕或更邪惡。為什麼不將傷害最大化呢?」
「不是在蛇蜷承認,不論是公開或是對八十八帝國承認他才該負責之後,整個行動崩毀嗎?」我問。
「對。」莉莎錫感的嗓音回答:「但是蛇蜷不會那麼做。他願意和凱薩談話,面對面向那男人自己坦承,但要走更公開的路線會讓他走進聚光燈下,把注意力吸引到他身上,風險就太大了。他不會那麼做。我猜凱薩知道,也仰賴這點來行動。」
「所以接下來呢?」我問:「我認為我們應該做點事介入,可是布萊恩在說他認為應該繼續維持低調。至少是,他在純潔發表演說以前是那樣。我不確定他是否改變想法。」我看了他一眼。
「我沒改。」布萊恩說,大聲得足以讓手機接收。他輕拍了些軟膏到我耳朵上,讓我皺眉。「抱歉。」
我不確定那句話是為了他在談話中的立場,還是為了治療傷口。
「根據新聞和我的,呃,內線情報。」莉莎指她的能力,說:「純潔還沒停下來。她在碼頭四處砲轟。她移動速度快得只有無畏或極迅能趕上,而且她的打擊力比他們兩加起來還強。我很確定,我們在這說話時她會擊倒更多建築。她還要多久才會擊毀我們的藏身處?」
布萊恩噘起了嘴。
「她也帶著她自己在八十八帝國的小隊,所以我敢賭迷霧人、深夜、白理石和十字軍都在街上,做著他們的事。我不知你們的想法,但我在街坊鄰居中有朋友。我對此並不贊同。」
「好吧。我們出動。但直到有個行動計畫之前都不能直接衝突,特別不要在我們兩群人會合之前。你們在哪?」
「我們待在火車維修場的另一側,跟狗在一起。」莉莎答道:「這地方不壞。比純潔拆毀的建築還要好。不知道她為什麼從那邊開始而不是這邊。」
我聽到另一邊八成是母狗的聲音,不過我沒辦法聽清楚在說什麼。
「所以。我們會面?」莉莎問。
「我們會面。」布萊恩回應。「我會打給蛇蜷跟他要台車,也要問他幾個問題,我要自己聽聽蛇蜷說他對凱薩說的內容。不管你們搭車過來要多久,我應該有足夠的時間把掠翅傷口縫好。」
我皺了眉。
「傷口縫好?為什麼?」
「跟現在的情況沒有關連。我們之後再解釋。」他說。
「那就等會兒吧。照顧好自己喔,掠翅。」莉莎掛斷。
布萊恩舉起針線:「讓我事先道歉。」
■
「你總是會在電影和電視上看到孩子的耳朵被扭。你不知道的是那他媽的有多痛。」我碰了碰面具蓋住繃帶了的耳垂的部分。我耳朵一陣抽痛,部分是因為布萊恩的援助。
「那樣就好了。止痛藥很快就會起效。」
「好吧。」
我們沈默坐了一會兒。我望出車子後頭的小窗。和我們同向的車子非常少。
蛇蜷為我們取得車子內裝充滿了醫療設備。我所坐的地方,是個輪床,另一張能在需求下拆開和重祖的輪床則被放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車子內部有效率地塞滿醫療補給:一桶氧氣罐放在戰慄坐著的椅子底下,心跳監視器,數件救生衣,各式形狀、大小的軟管,櫥櫃和抽屜裡塞滿了藥丸、夾板和繃帶。
這車--整體看起來--就是輛真正的救護車。我沒辦法說這台車原本就是救護車,然後是蛇蜷為了武器和我的蟲子才加裝額外空格,或是他採用另一個方法從頭組裝整台車,加裝他自己的組件。
我們慢了下來,戰慄靠向救護車的前方:「怎麼塞車了?」
「前面有封路。」駕駛說道。他和副駕駛座的女人是蛇蜷的人,穿著醫護人員制服。「別擔心。」
他按下一個開關,警鈴接著刺耳鳴叫。幾秒後,他轉了幾圈方向盤毫無困難地動了車。我看著後照鏡,見到一條警車和PRT貨車組成的封鎖線在我們後面,將他們剛才打開的空位補回編隊位置。
「嘿,還好吧?」戰慄問我。他正穿著假面服,戴上了安全帽也放下鏡面。
「嗯?」
「我感覺妳好像在生氣。」
「假使我為了那件百貨公司外的事對任何人生氣,會是我自己。我們能永遠放掉那個話題,忘掉那件事嗎?」
「不,不是。我是說,妳不是在我們知道所有東西都在危急關頭上之前,對我沒立刻起身,要和八十八帝國戰鬥生氣嗎?」
「喔。」我臉紅了,我耳朵對羞紅的血流以刺痛回應。我真該踹自己一腳。「我真的不清楚。我沒有期待你會那樣決定。我見過你花費很多力氣照顧你的……家庭成員,我認為你是個滿可敬的人,你懂我嗎?」這話題走向比我喜歡的還更接近不該談論之處。我刻意把那個想法懸在空中。
戰慄摩擦了下後頸:「我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妳所想的那種好人……」
一震衝擊撞上救護車,將戰慄扔出去、沒站不住腳,也差點把我撞得四腳朝天。救護車拖離司機掌控,翻了過來,落在側邊上,戰慄撞上我剛才坐著的擔架下方。備用輪床和抽屜、櫥櫃裡的東西全都噴灑在我們周圍。
「幹!」那個司機罵道。「我肏!」
我把幾條管子抽出,半張輪床也落在我身旁,我便向前爬從兩張前座看出去。
那東西看起來和母狗的狗兒們有著差不多形狀。它可能,比較大一點點,可是真的很難說。它的肢體空洞,四肢比狗兒們更細,我沒辦法看出真正身體的「肉」和不是肉的輪廓,因為那整個東西是個鋸齒刃、鉤子和尖針的旋轉輪,在各金屬之間混動變形、升起又落下,移動速度快得眼睛無法追上。那東西,維持了一個約略有條尾巴和長條口鼻的四腳獸形狀。
有兩個人走在它兩側。一位是有著只會在騙子和健美人的壯碩肌肉身材、蒼白高挑男子。他穿著褲管口緣破爛的黑色垮褲,數條鐵鍊繞著他的前臂、雙手和小腿,戴著一副藍白老虎面具。金屬野獸另一側是個二十幾歲、有著體操選手的女孩,暴露出的肌膚有數道十字疤痕。她的頭髮被剪成漂白金髮狗的啃頭,她臉龐被金屬牢籠遮住。
那個貌似危險攪拌機的金屬部位融解,每根鉤子和刀刃都被收回那物體胸口中央的男人皮膚裡。當那雙前腳收回他雙肩時,他以蹲伏姿勢趴在街上。他戴了一片粗糙彎曲的鋼鐵狼面具,面具周圍由油膩、金色長髮凸顯。鐵血狼牙。
聽說鐵血狼牙,在早年間,曾經是個紐約超亞人類拳擊場的最強鬥士。他變貪心,殺了管拳擊場的人,走進金庫拿走當晚收入,也在過程中樹立不少敵人。曾經有個當地區域的白人志上團體提供他避難所和支援,很高興和他站在同邊,因為他殺了一個「合意的目標」。也許那份意識形態對鐵血狼牙來說一開始就是真的,也許是他假裝後,發現自己享受那些人慶祝他所扮演的最扭曲衝動和高疊屍山,才成為真實。不管是哪樣,我猜他現在只有少數幾件事不會為「帝國」幹的。
嵐虎--就是那身著鐵鍊和老虎面具的男人--還有蟋蟀女--那個女孩--都明顯和鐵血狼牙參加過的超亞人類獎金鬥士圈子有關。我沒辦法猜想他們跟隨他的動機,可是我也認為這根本不重要。鐵血狼牙自己就很危險了。加上他朋友?
「我們跑。」我低語。鐵血狼牙和他的伙伴們轉身背對我們,正朝警察封鎖線走去。嵐虎伸展雙手,周圍的空氣便被模糊,兩隻手各自凍結出五六道蒼白、透明刀刃。
「我們有槍。」駕駛說:「我們從後面射他們。」
「不行。」布萊恩說:「那不會傷到鐵血狼牙,而我也懷疑蟋蟀女和嵐虎可以對付槍,不然他們就不會那麼固執於走向那些警察了。掠翅沒有錯。我們撤退。準備好了?」
戰慄將救護車的後門和外面都蓋上黑暗,消除他砸開門的噪音。我們四人無聲地,從救護車後面走出來。
戰慄把街區注滿黑暗,我也把蟲子從周圍區域和救護車內裝隔間裡散開,覆蓋戰場和周遭物品,給了我一種周遭的蟲群感知。我抓起那個醫護員女人的手,把她從街道正中央拉開來,走向人行道。布萊恩把那個駕駛也帶往差不多方向。
我的蟲子感到有人,迅速快追向我們。我沒時間閃開來也把蛇蜷的偽醫護員帶到安全位置,所以我把她塞向一方然後跳向另一邊。那男人跳進我們空出的空間,我感到一陣風猛衝過,令我頭髮鞭打我的臉邊。
一陣類似爆炸的東西,產生足夠強力的疾風將我從地面提起,也推開戰慄一部分黑暗。嵐虎站在空出處中央,他舉起的左手周圍重構了透明「爪子」。
他轉身俯視我時,用手上其中一道透明刀刃輕碰了下老虎面具的鼻子。當他說話時,他的嗓音比布萊恩更低沈:「甜心,我不需要看見妳。」
我真的,真的開始痛恨強化感知了。
ns18.117.157.139da2




















